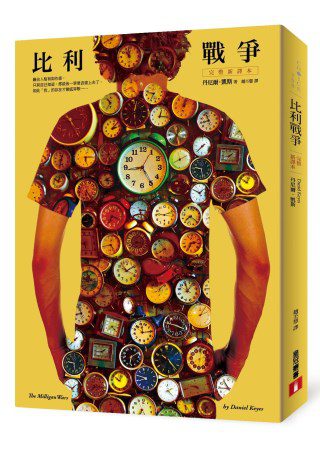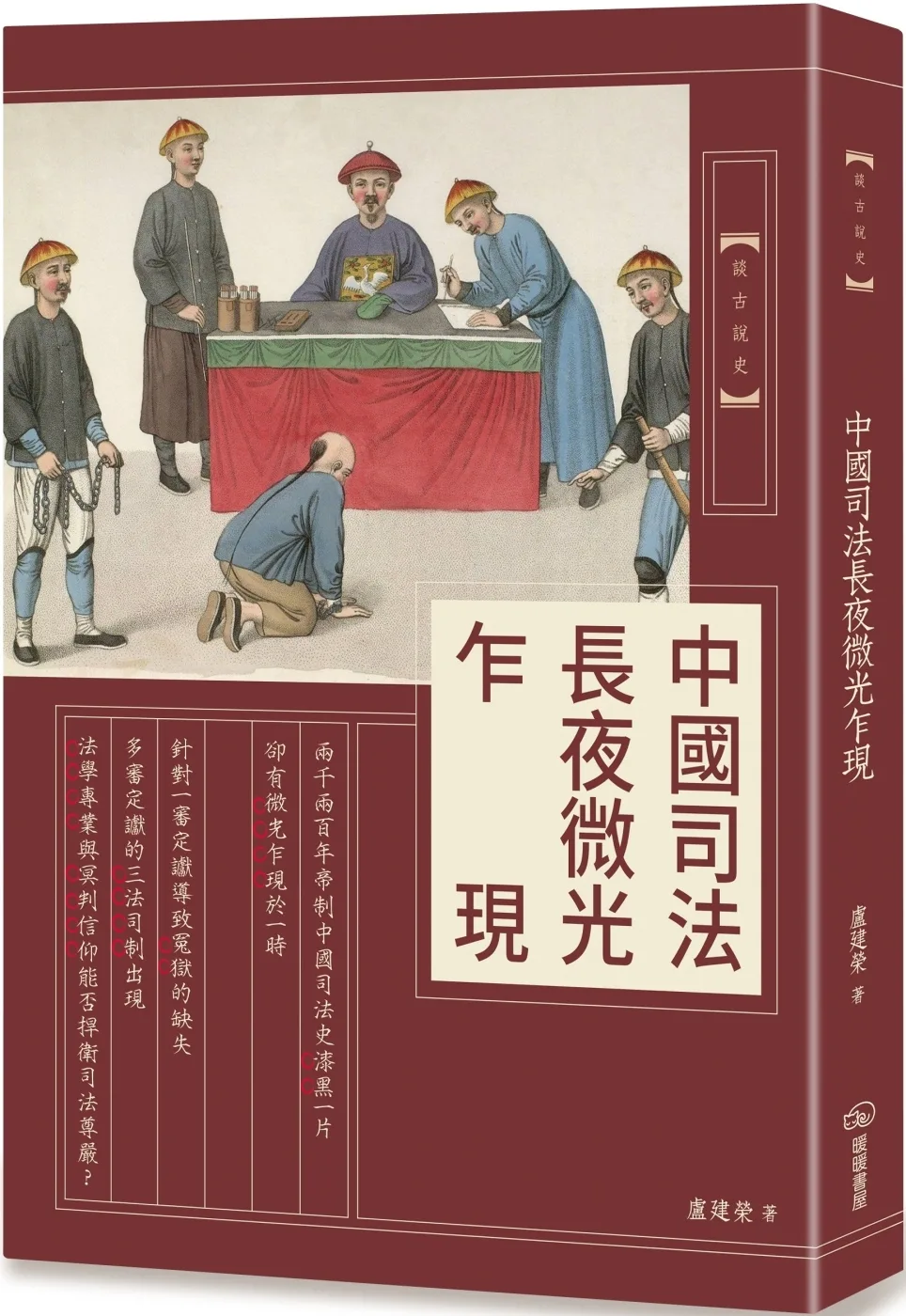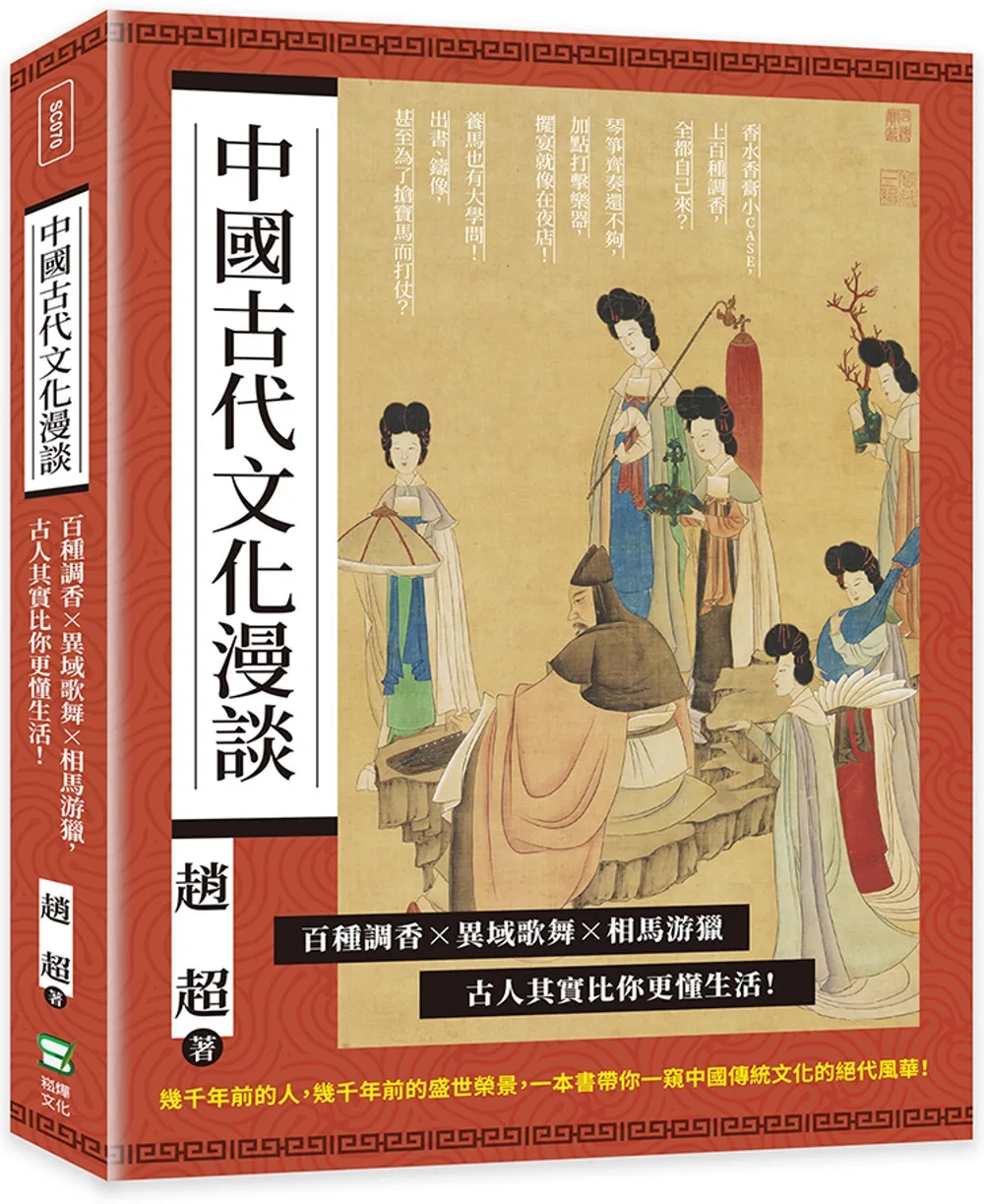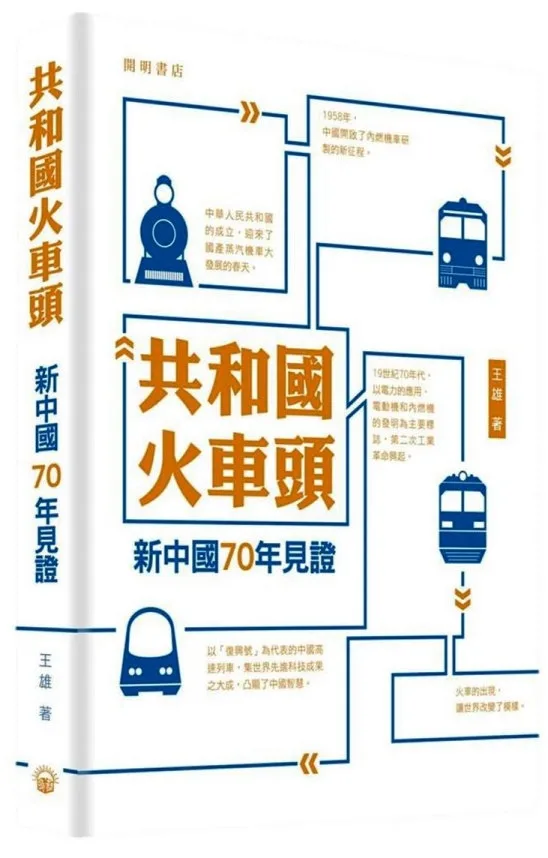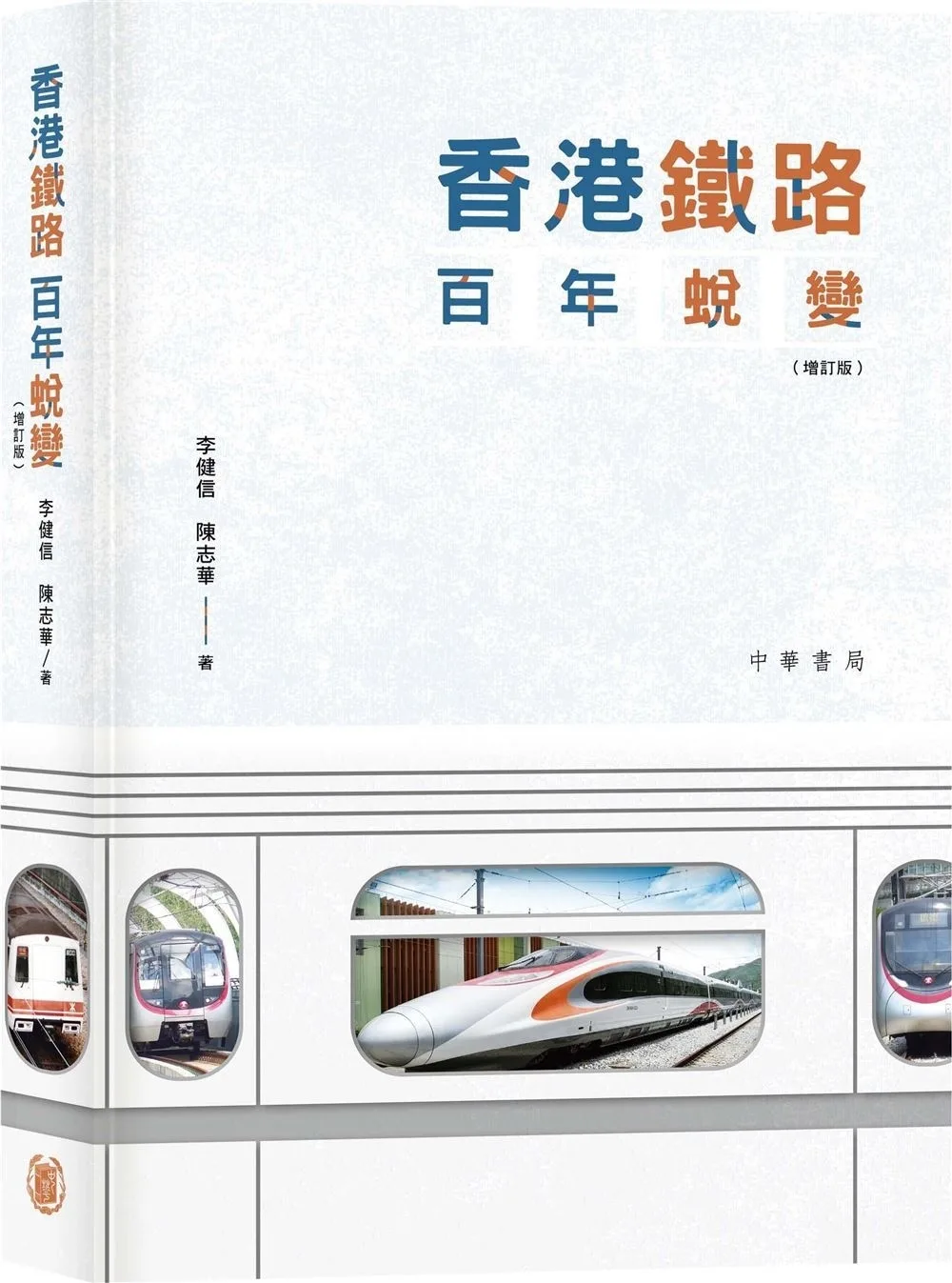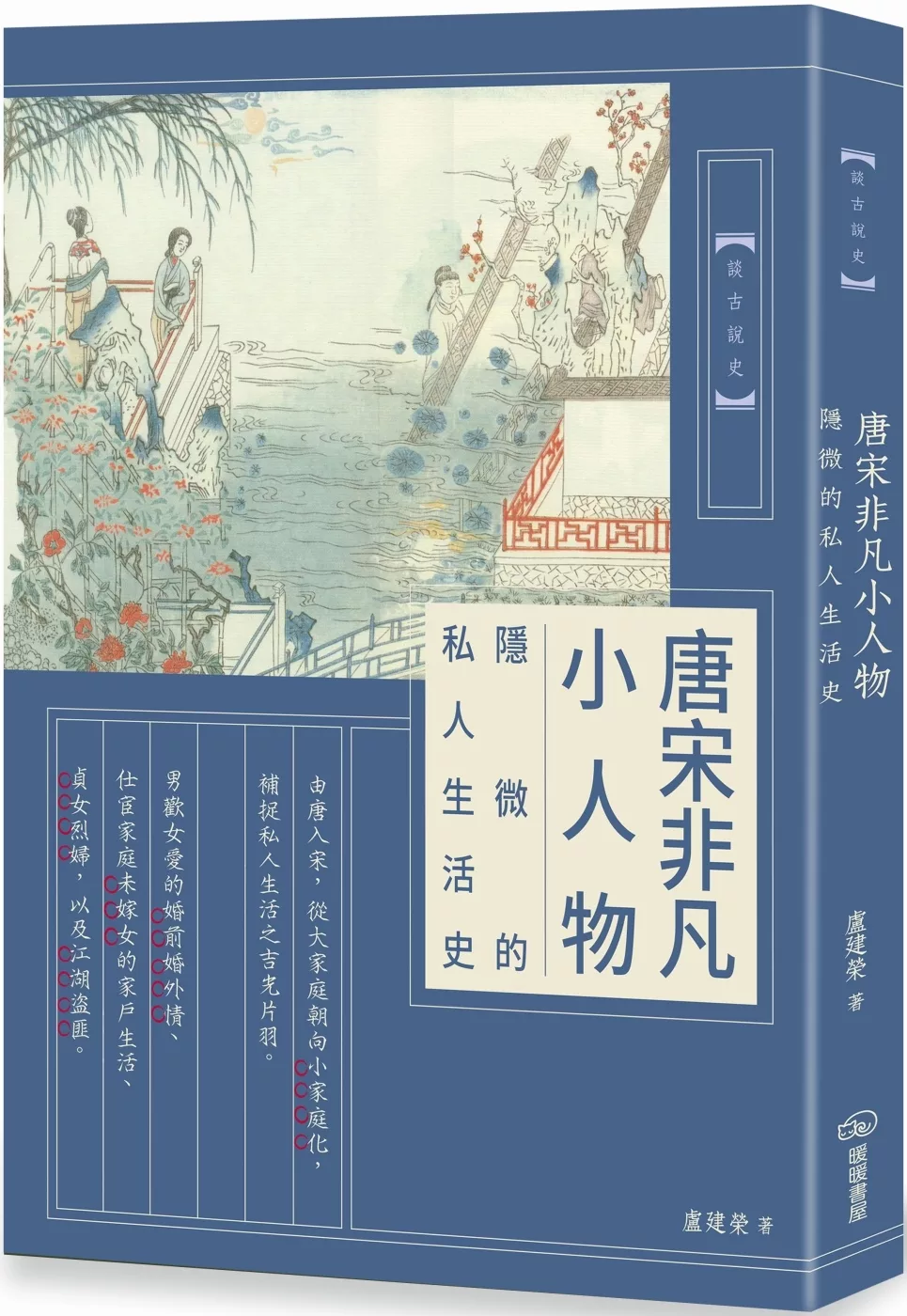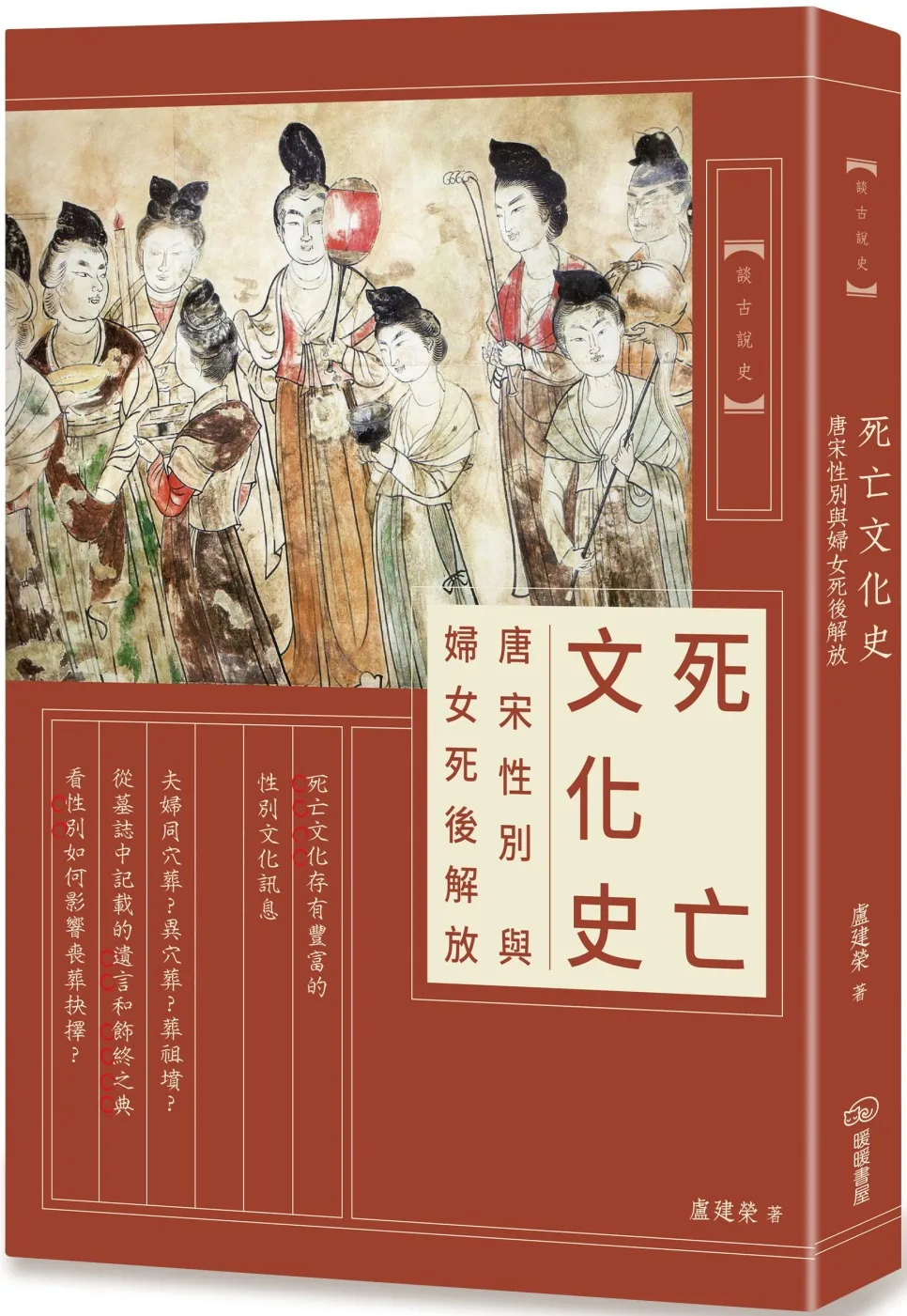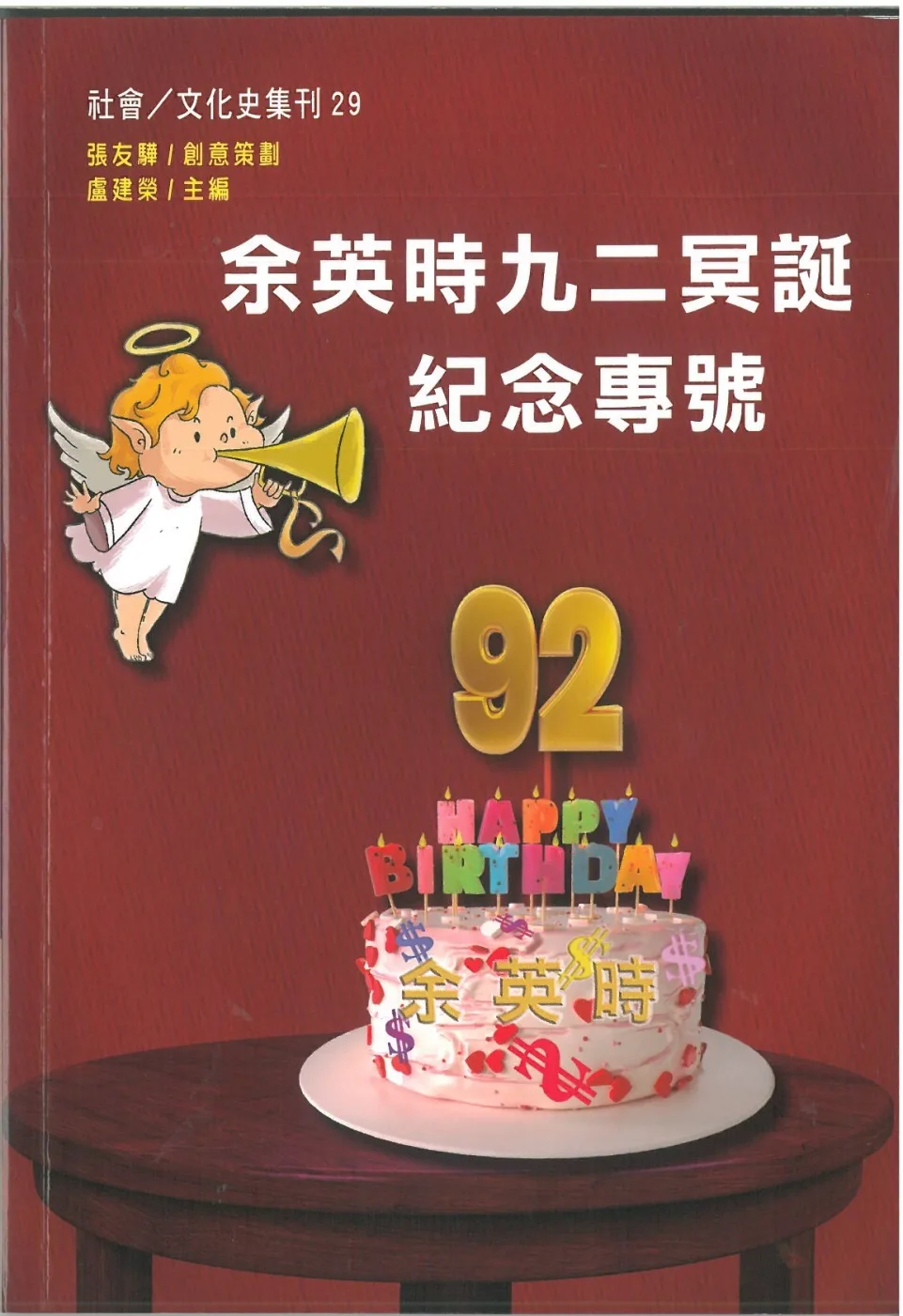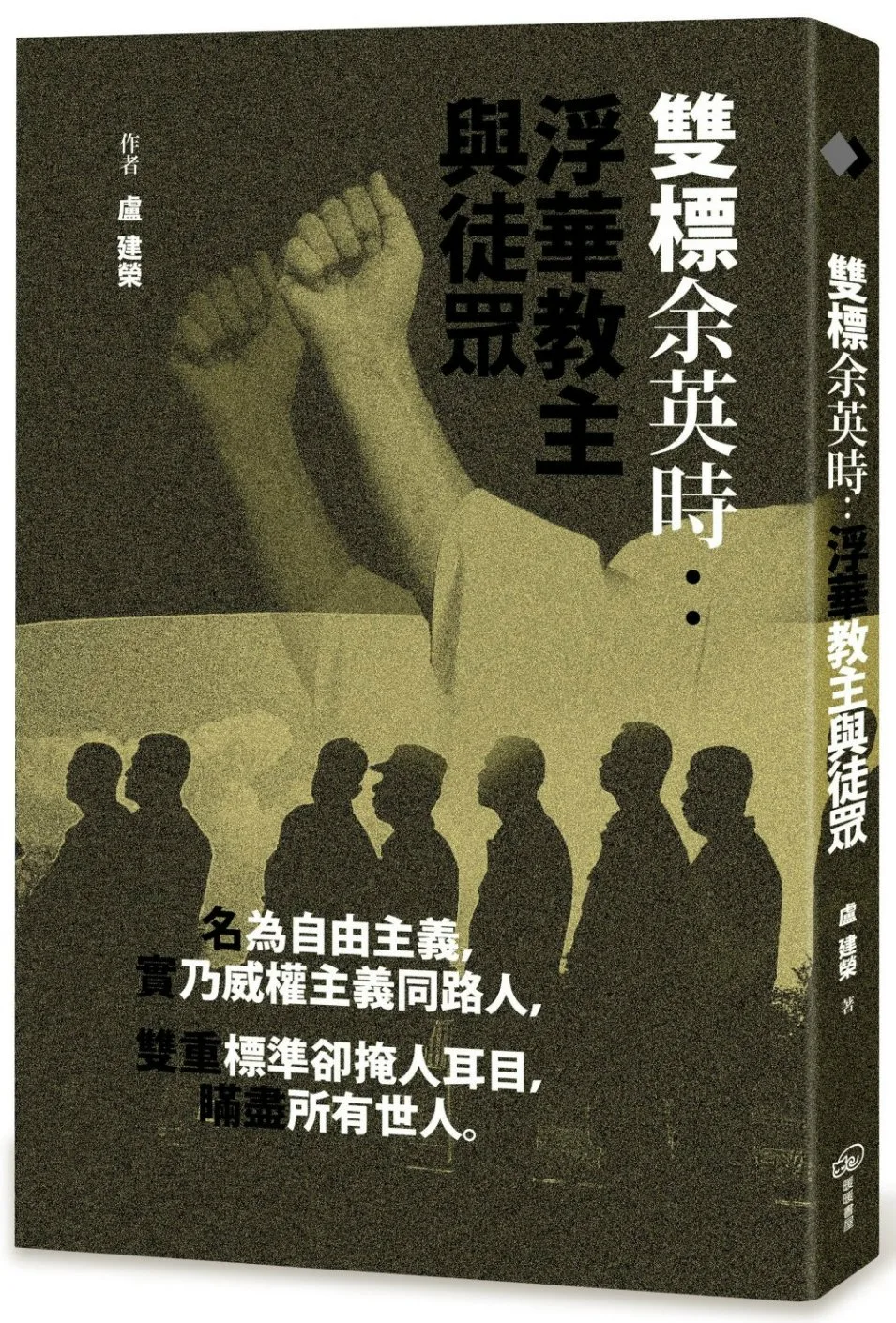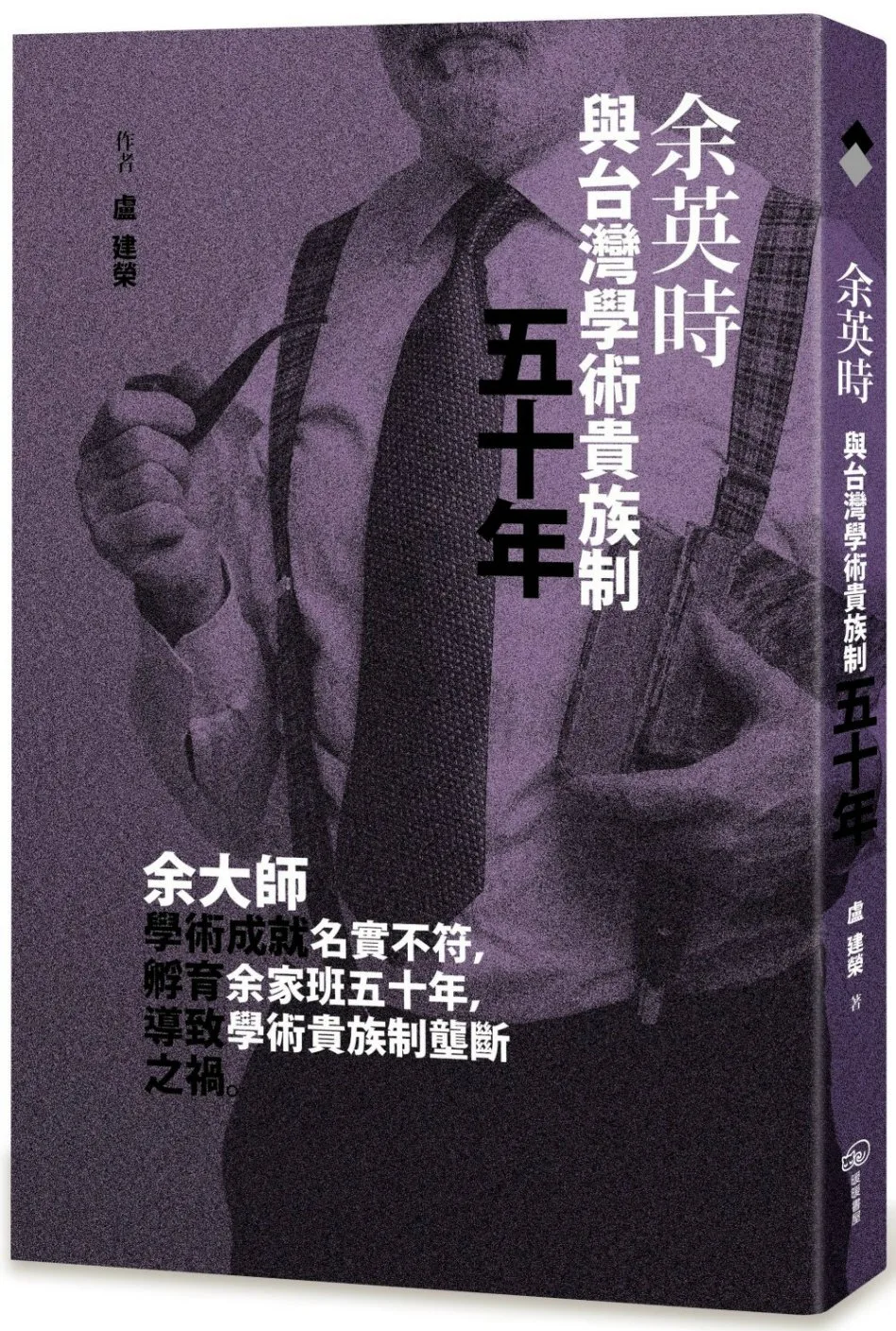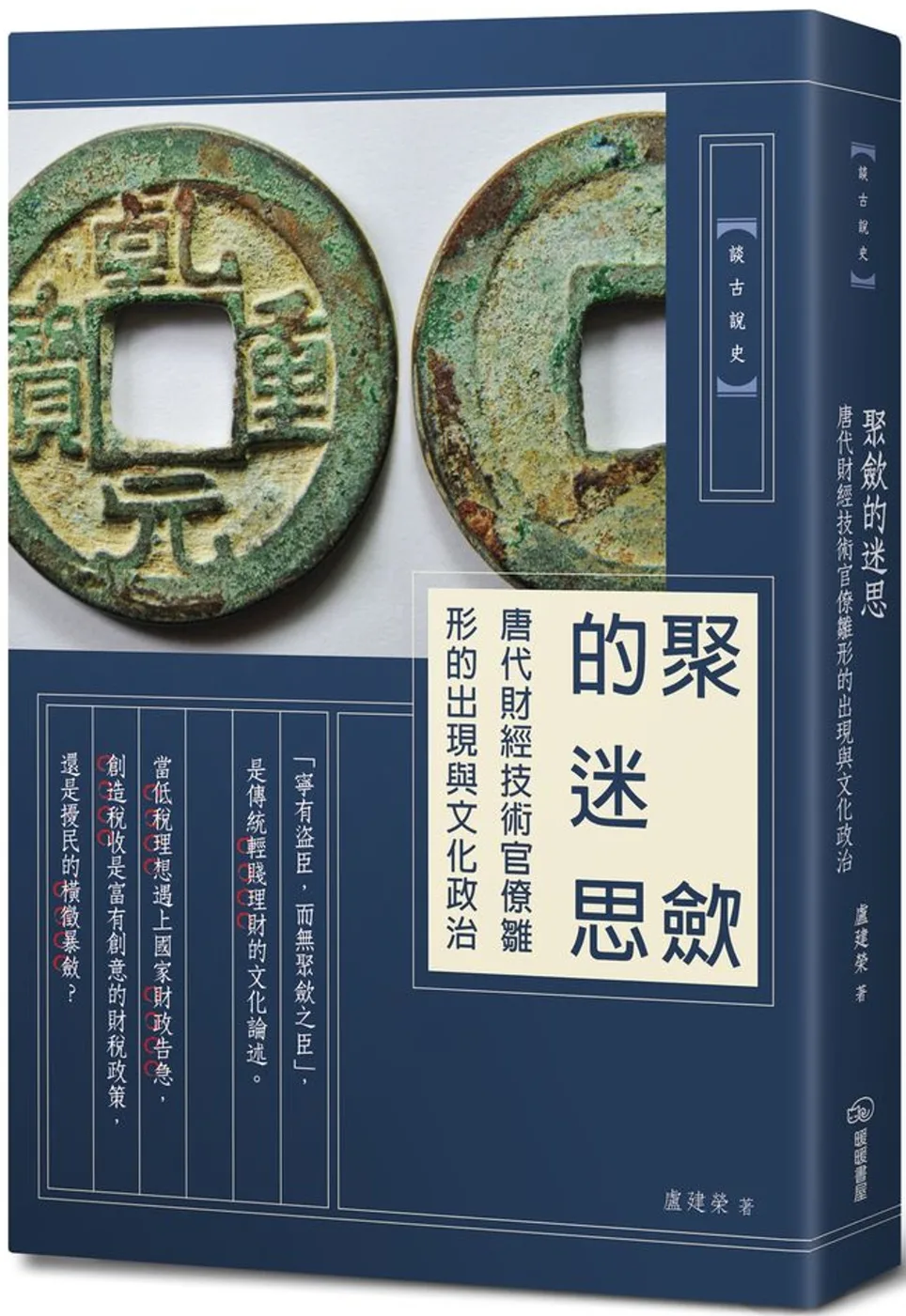自序
論文一篇考績甲等 專書一本考績乙等
一
關於本書製作過程,我且從頭講起。
本書第二章初稿完成於一九八六年二月。稿成後先後請史語所法制專家張偉仁和近史所近現代思想史家黃克武兩位先生寓目,並乞賜卓見,他們兩位都很客氣,並未提供任何修正建議。之後半年不到,我便負笈美國,本稿置於筴中隨我飄洋過海。一九九六年初,那時,我已返國六年了,一次偶然與史語所同事李貞德交談機會裡,談到北魏駙馬毆(公)主傷胎案的一件司法案件,我告以曾有稿論及此案,她表示有興趣索閱。這份稿件就這樣保存在李小姐處,達一年多之久。等到她交還後,我趁機向她徵求修正意見,她亦謙辭所託。以上三位友人可能都因我的愚魯而不忍賜教吧?
時序進入二○○○年初,我動念修改初稿,並投稿《台灣師大歷史學報》,獲蒙審查通過。以上過程中,有一次機會我巧遇明代法制史家邱澎生先生,他也是史語所同事,承告文化大學史學系的桂齊遜有類似博論,並蒙他借予桂著。我讀畢桂作,發現彼此在寫法、觀點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便放心了。我決定,不必在導論處增寫一段有關學術史的回顧,特別是針對桂氏的研究,我改而在正文相關處,指出桂作所為,異於本章之處。說起來有點有趣。就是說,即令我從事這種司法文化課題的研究起步很早,但因故晚了十五年才發表,不曾想這十五年來這方面的研究迄未突破,是以還敢厚顏發表源於十五年前的一項構想。最後,感謝兩位秘密審查人的審查意見,也感謝邱先生告以最新研究行情。另外邱先生還提供修改題目的意見,更是感念不已。事情還沒完,更神奇地,前述二○○○年論文發表事,又經過快二十二年,老天待我不薄,又賜予我有據文改寫成專書的機會,我又從頭修補、潤飾一遍,提煉成今天讀者看到的模樣。
本書第三章安排有三節,第一節談北齊司法人才出頭的政治因素。第二節共三款,第一和第三這兩款,談有關北齊、與周隋之際,筆者考察這前後兩時代河北司法人才出仕機率之大小。以上兩部分,我草成於一九八四年,到了二○○一年我加以增補並改寫。在增補方面,我多了第三節,談國家法學教育體系和司法官專業官職的出現,以及第二節中第二款,在講河北文教事業特性、法律知識的開展,以及家傳律學這三樣東西。也就是說,本書第三章,我在一九八四年側重政治�社會史,但到了二○○一年,我補充了文化視角與政治�社會相連動的東西。此章觸及歷史複雜性中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等三個維度。此章完整的初始版發表於二○○一年的《台灣師大歷史學報》上,二十一年後今天視之,仍是先驅研究。
本書第四章處理了唐臨這位《冥報記》這一宣教文本的作者,他是《法華經》中冥判信仰的宣揚大家,這是本書強調一些「不群不黨」法官,敢於對抗皇權的信仰來源。唐臨的家世、生平,及其在司法史上的表現,都讓我給率先發表於二○○○年。二○○一年、或二○○二年,有位陳姓同行(就職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到史語所參加法制史會議,主辦單位邀我擔任陳文的評論人,他恰好處理唐臨這個課題。按說我是這方面研究的先行者,而且他也知我在史語所工作,他到史語所大談唐臨,不可能秘不讓我知道。會議前我從主辦單位先獲讀此文,驚訝發現,他談的唐臨,都經我處理過不說,而陳文中又有蓄意略我所詳的部分,按說他應該有所交代才對,哪知他卻裝著我研究唐臨在前的事實一副不存在似的。這是對前人研究不尊重不說,也對學術研究建立在學術傳承這項原則,竟然毫不遵守。原來他研究唐代法制史經由拜碼頭的文化機制,隸屬台大教授高明士所收容的外門弟子(按:陳君原是文化大學史學所王吉林教授的碩士生,師大史研所邱添生教授的博士生)。我呢,乃反拜碼頭主義的獨立知識人,既非高某跟班,更不在高門麾下。以上派性機制使得身為高門長隨的陳君,便決定既不引證、也不批判我的唐臨研究。他寧可重複勞動,也不提拙作,以示他裝不知我的存在。這是派性主義作祟、違逆了現代科學研究的精神,是在於對前輩學者研究成果的尊重。這是當代台灣學術腐敗所自來的一端,竟然被我逮個正著。
我當天的批評是直言不諱,完全不理會主辦人邱澎生教授事先明告,要我手下留情。這又是台灣學術腐敗另一端,即會議前先行關說。我通常都不會答應這種關說。更何況論文發表人在治學態度上,完全犯了不理學術倫理這一套行規。試問是可忍,孰不可忍?
今天我出版此書,一口氣講出與本書內容相關其背後的兩件學術不端行為。本書內容就只有三章,頭一章與次一章的幾部分,我草成於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之間,一直等到二○○二年,我草成末章,這才完成本研究的事先全部構想。想來這個系列研究斷斷續續了二十年之久,其間,我的治史方式也經歷了兩次重大變化。我將十六、十七年前初搞,經增補後正式發表時,已然對八○年代的原始構想多所改易,這主要是從單一法律社會學視角,再多加法律文化史這一視角,而在這社會�文化兩視角交叉觀照之下,才有從二○○○年至二○○二年連續三年的論文發表。再過二十年,我決定從新彙整,以成本書如今這模樣。這樣一本書,從一九八○年代草創,中經二○○○年代正式以論文形式刊出,以迄今天二○二○年代易以專書形式應市,前後歷經四十寒暑,我已從青春煥發的青年變成斑白老翁。學問的經營如此耗時又艱難,如果定力不夠,很難等到以專書形式問世的一天!
二
本書前一版本築基於二○○○年之後兩年的三篇論文。這三文經我運用藝術手法,於二○○四年寫成《鐵面急先鋒》這一敘述史學文本,在問世之後,從台灣到大陸都獲好評。同一個歷史課題的研究發現,我可以用三種不同表達方式呈現世人面前。無論二○○○年代的一連三篇論文,還是今天本書模樣,採用的是第三人稱全知觀點,而二○○四年敘述史學文本這一專書,採用的是第三人稱受限觀點。因此,歷史書寫表達形式有異,閱讀效果自是有別。在此,有個小故事。話說《鐵面急先鋒》在市面上推出,史語所同事兼好友蒲慕州教授到書店看我新作。蒲先生於觀後,告訴我,很驚訝書的呈現方式,與論文呈現方式,可以做到判若兩人。我原想告訴他,二○○四年史語所年度考績評定會議上,我在「年度工作報告書」上,明列完成專書一本,可是與會行政主管望著書名而浮想聯翩,並據以判定不予接受。他們咸認這是一本小說創作(按:在研究機構工作,如何可能用小說創作混充專題研究?如此判斷力竟號稱學術菁英,有權操人生死),而非嚴格意義的史學專著。在評定完成後,我以此向所長王汎森抗議,說開會諸公不依事實,而依一己想像作判定。王某則一再低聲致歉。(可能只是故作姿態吧?)我還說,大家同在一棟大樓上班,開會時眾人若有所疑義,只消以電話向本人查詢,便可解消疑慮。但這些權勢者非常厭惡查證,而性喜自以為是地當場給予評定等第。這是享受權力滋味的悍然作風,不是在作科學認證工作。總之,我在史語所工作,向來每年以發表一文,即獲考績甲等,而我在該所服務最後一年的二○○四年,我卻因出版專書一本,而獲考績乙等,這是我在史語所二十三年最糟的一次成績,全拜王汎森高明領導之賜。
我在一九八一年進史語所,到一九八五年,四年不到,完成唐代理財術與文化衝突一系列文五篇、唐代司法制度與法律文化變動一系列文五篇,以及唐代禮文化與官僚政治一文。以上諸文,我只發表其中五文,便匆忙負笈美國念書。直到一九九○年回國,又因展開其他新研究,便把一九八○年代研究成果給擱置了。如今想來,當年決定從魏晉南北朝史轉行,改做唐史,是大膽了一點。但一開局便氣吞山河,有關唐代的禮文化、法律文化,以及財經與文化價值衝突等三大區塊,便一體冶之,而想從中建構一個龐大的學術王國。我當時並不因年輕而畏首畏尾氣量變窄,反而大開大闔,做起異於俗流的細枝末節、且彼此關連不大的研究風潮。如今想來不寒而慄。
三
再講到運用法庭文書材料去從事歷史研究這件事。衡諸當代西方史界於上世紀七○、八○年代,有過一場饒富方法論的論戰。話說義大利史家卡洛.金茨伯格(Carlo Ginzburg, 1939-)於一九七六出版《乳酪與蛆蟲》(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一書,這是一本利用審判異端法庭材料寫成的書。引起西方史壇廣泛注意,一時之間聲名大噪。這時,美國史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出而與作者辯論說,彼時被告磨坊主於法庭所用語言是俗民口語,而法庭書記官用菁英階層書面語,將之譯成如今看到的案件檔案所現文字,其實是一種翻譯,而其中不乏偷斤減兩、或加油添醋的不實情報混入其中,已非復被告當時陳述的原滋原味。拉卡普卡還進一步指出,今之史家倘用這種已被扭曲的文字,說是在復原被告思想,不免有欺人之嫌云云。由於使用法庭檔案難免失真的疑慮被挑起,一時之間,西方史家面對使用法庭檔案的態度,就變得轉趨低調且慎重。不久,美國史家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Davis)於一九八七年推出《檔案中的虛構》(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一書,即用十六世紀法國赦罪書史料,從事歷史研究的力作。這次,赦罪書中凶手行凶的陳述,戴維斯採取不信姿態,完全不理白紙黑字中的所說行凶經過。她不是在探究行凶的真相,而是究詰古人用何法原諒凶手犯行的說故事文化。行凶敘述背後蘊藏人們如何演繹引人原諒故事的文化。易言之,戴維斯利用法庭檔案,做的是行為人所使用的說故事文化,而不是犯案的真相。
同樣,筆者在本書所用官司的第三者於事後敘述,其所涉的冤假錯案,既已清楚可見,研究的重心便不再是法官如何聽政治力調遣、去做黑心事,而是極少數法官如何不屈從政治權力,甘願承負壓力、甚至即令因此犧牲,亦在所不惜這背後抗壓力量從何而來。筆者當時面對排山倒海諸多冤假錯案的文獻時,一時之間難以找到下手之處。幸而古代極權專制所使用刑獄手法的本質,是政治,而非司法這點,異常明晰,眾多法官乃依(政)令而行,而非依法辦案。在此,爭辯官司的是非曲直,甚至犯案真相,早就沒有意義。就像台灣當代在威權政治時期所施行的白色恐怖,全是藉司法來羅織人入罪,那些司法檔案其白紙黑字全是被告自證己罪的記錄,今之研究者想替被告挖掘「案情」真相,又何其荒謬!這是何以台灣今天從事轉型正義依舊反挫的主要原因所在。且回到本書題旨。本書所處理的案件本身,是政治打壓下炮製出的產物,而猶有少數法官明知「起訴」是奉命辦案,本是沒有其事、硬被虛構出的,卻願意以身對抗惡勢力,這樣行為本身才應比為做法制史而做法制史之類案情研究,更值得揭開其面紗。原來官司材料可有別的用途,有比做法制史更值得開發的題目,來試煉史家的能耐。
四
最後,我還要談一點本書所用材料的性質。法律文化課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官公文書,墓誌碑銘在這方面所能蒐集到的訊息則相當欠缺。講到官公文書,最有用的,是法律文化事件發生百年後,由唐人杜佑所編《通典.刑七.守正篇》所抄錄事發時的政府檔案,還有就是他的評論意見。另外,事發當時當事人的宣教文本,諸如唐臨《冥報記》,郎餘令《冥報拾遺記》留下了當時法官職涯生活點滴記錄。還有,唐.元和年間(807)江南一位縣主簿劉肅,寫了本有關從初唐到大曆年間(766-779)大人物的言行事蹟,書名叫《大唐世說新語》,其中卷四《持法篇》,記錄了二十位司法官辦案事蹟。這是一種回溯性記錄,比起當下遺蹟遺物之類史料,其史料價值稍低,但以其距事發最後時間點的玄宗朝末年(755),五十幾年前到一百多年前,還是相當珍貴。這是一件比較偏私人性質的史料。
以上四件史料是本書比較倚重的資訊取得來源。其他後世所編的正史人物傳記文本,以其大量蒐羅法曹人物生平作為,這相對於當時刑案檔案遺失情形之下,其史料價值也相對水漲船高。這是一筆豐富的政府人事檔案,如果以其非第一手資料而棄置不用,未免過於矯枉過正了。當然,我會用新文化史研究矩矱的手法,即文本分析法,去看待以上史料。這點是我與時下同行不同的行事操作手法,不待深論。
關於本書,我說到這裡,就當成我出版生平第二十五本作品的感言吧。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台北寓所
時俄侵烏之戰如火如荼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