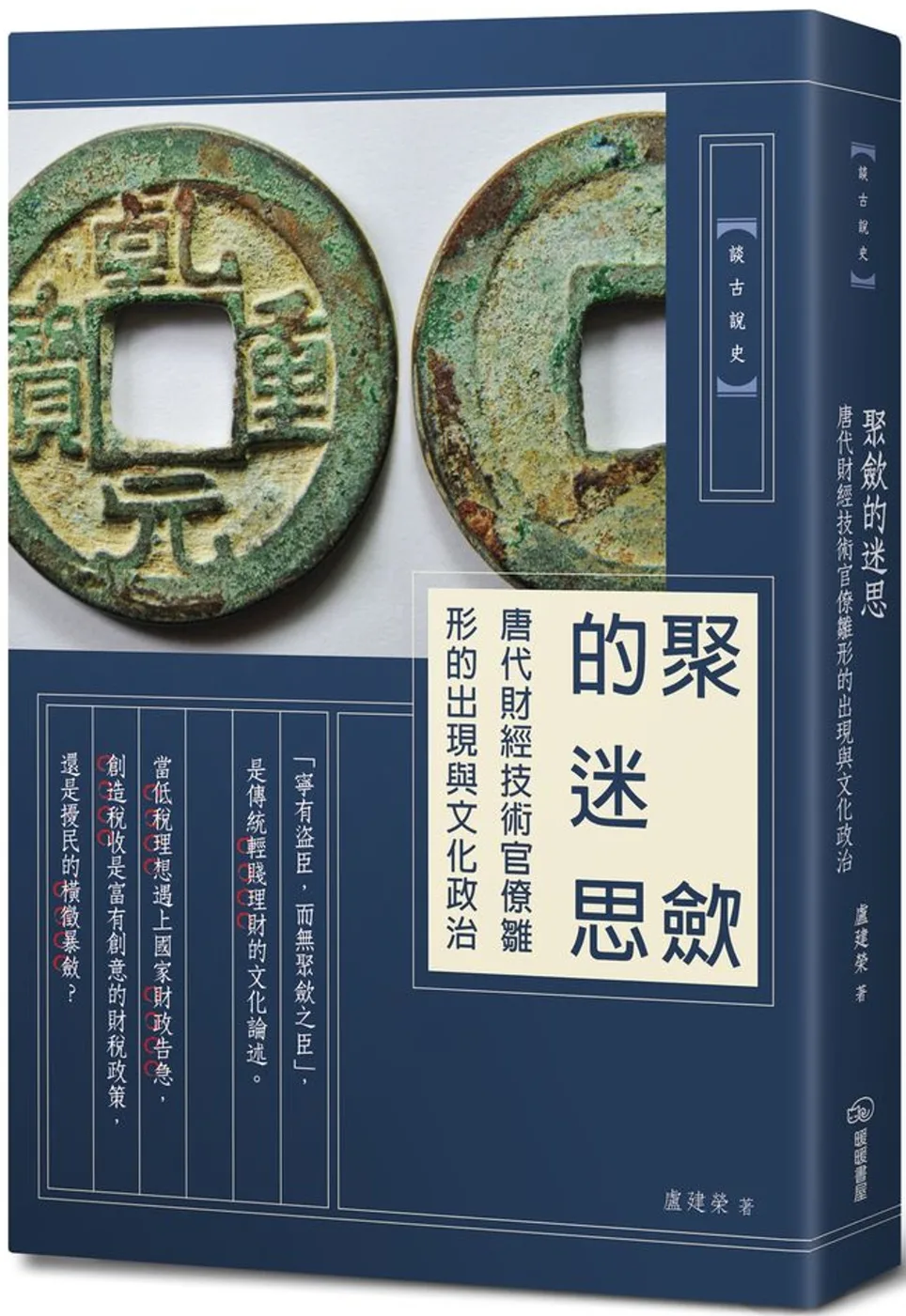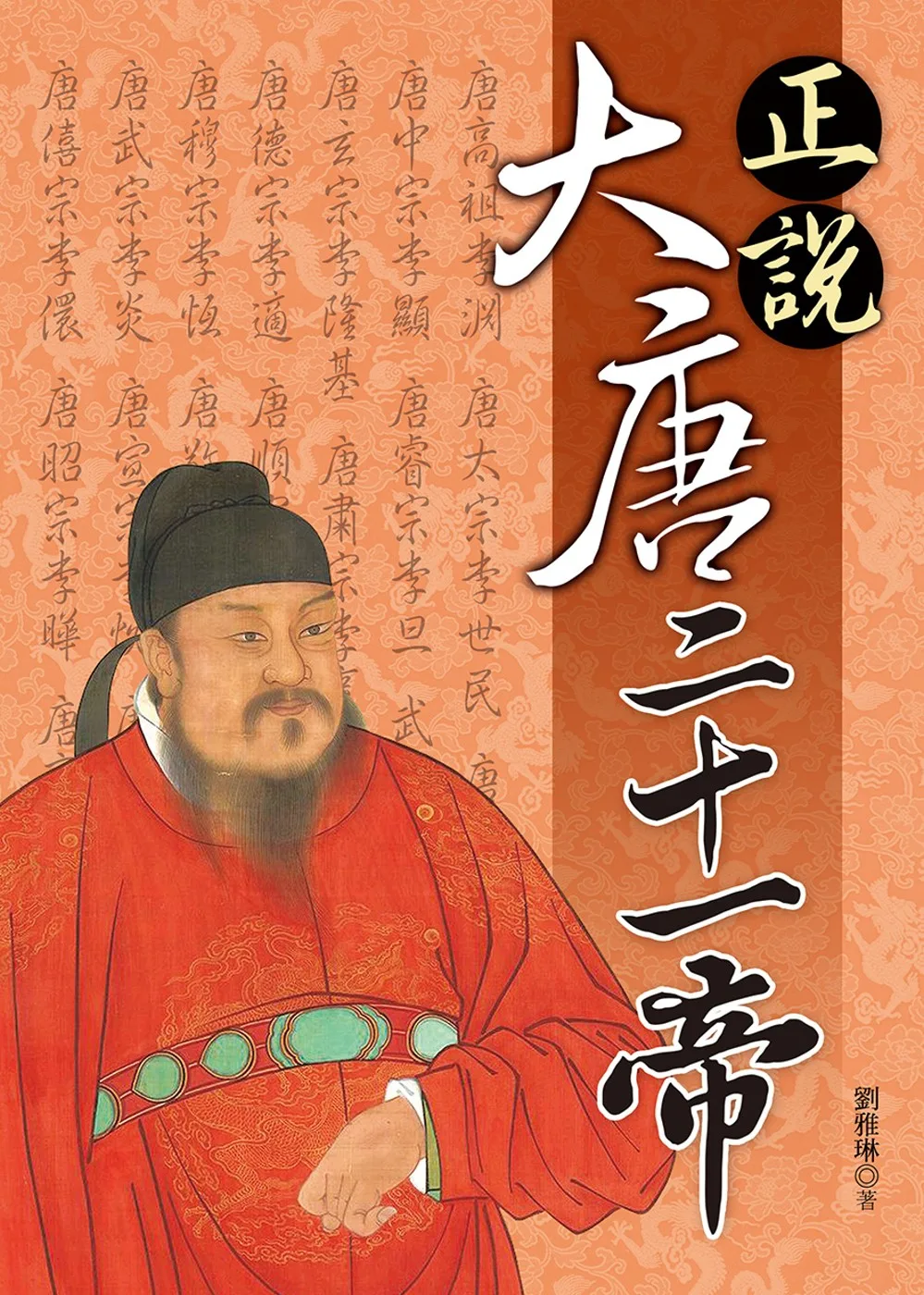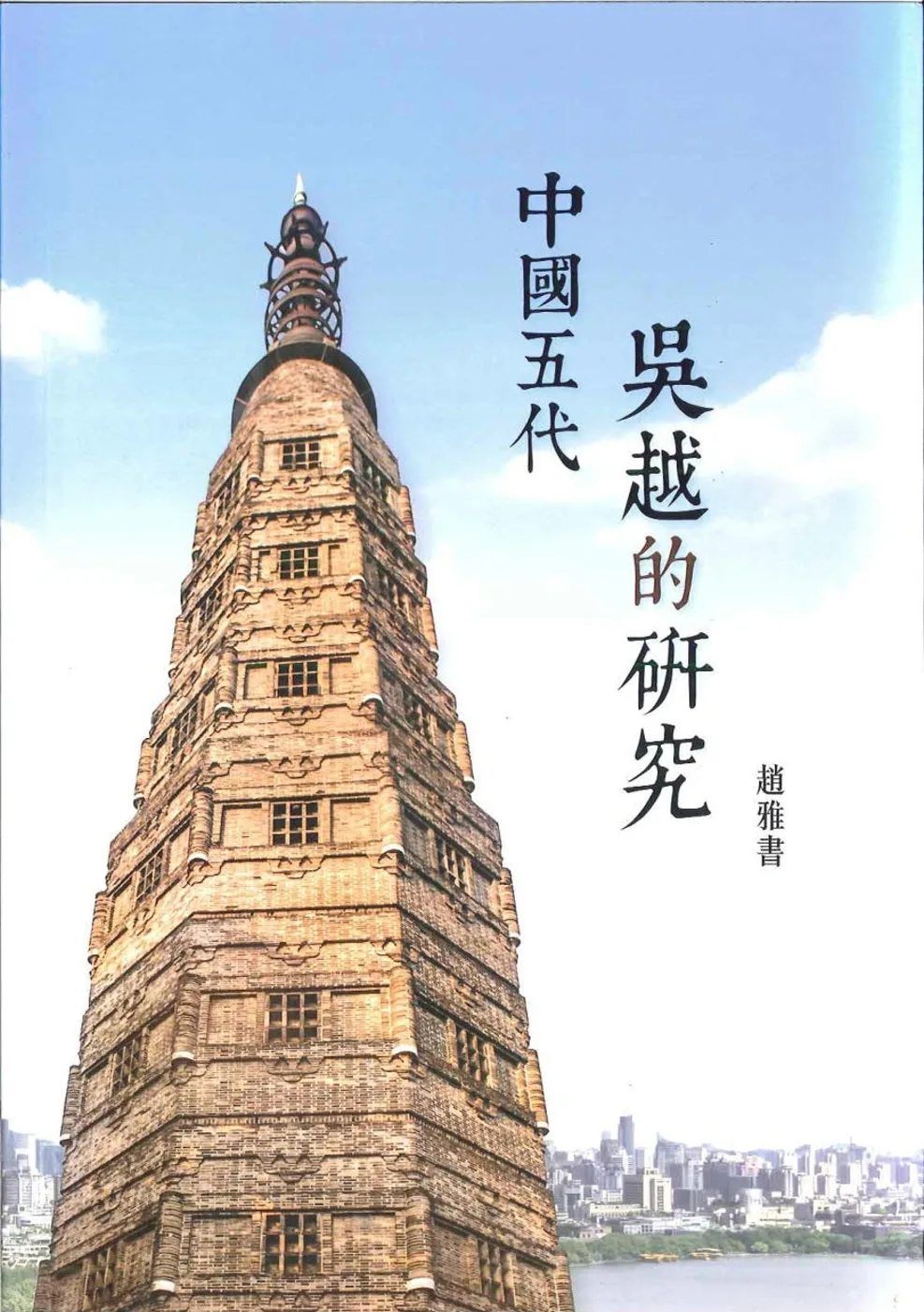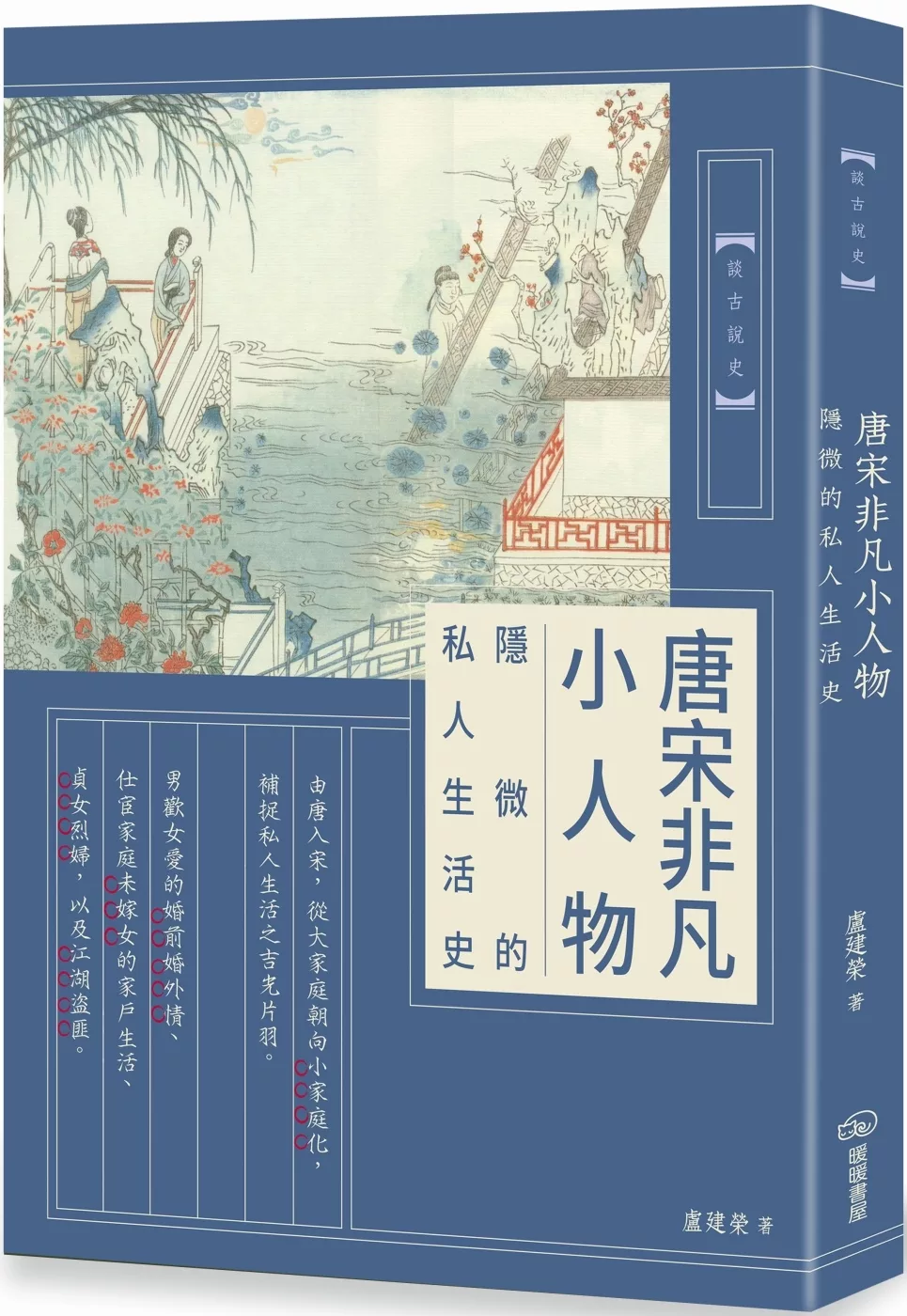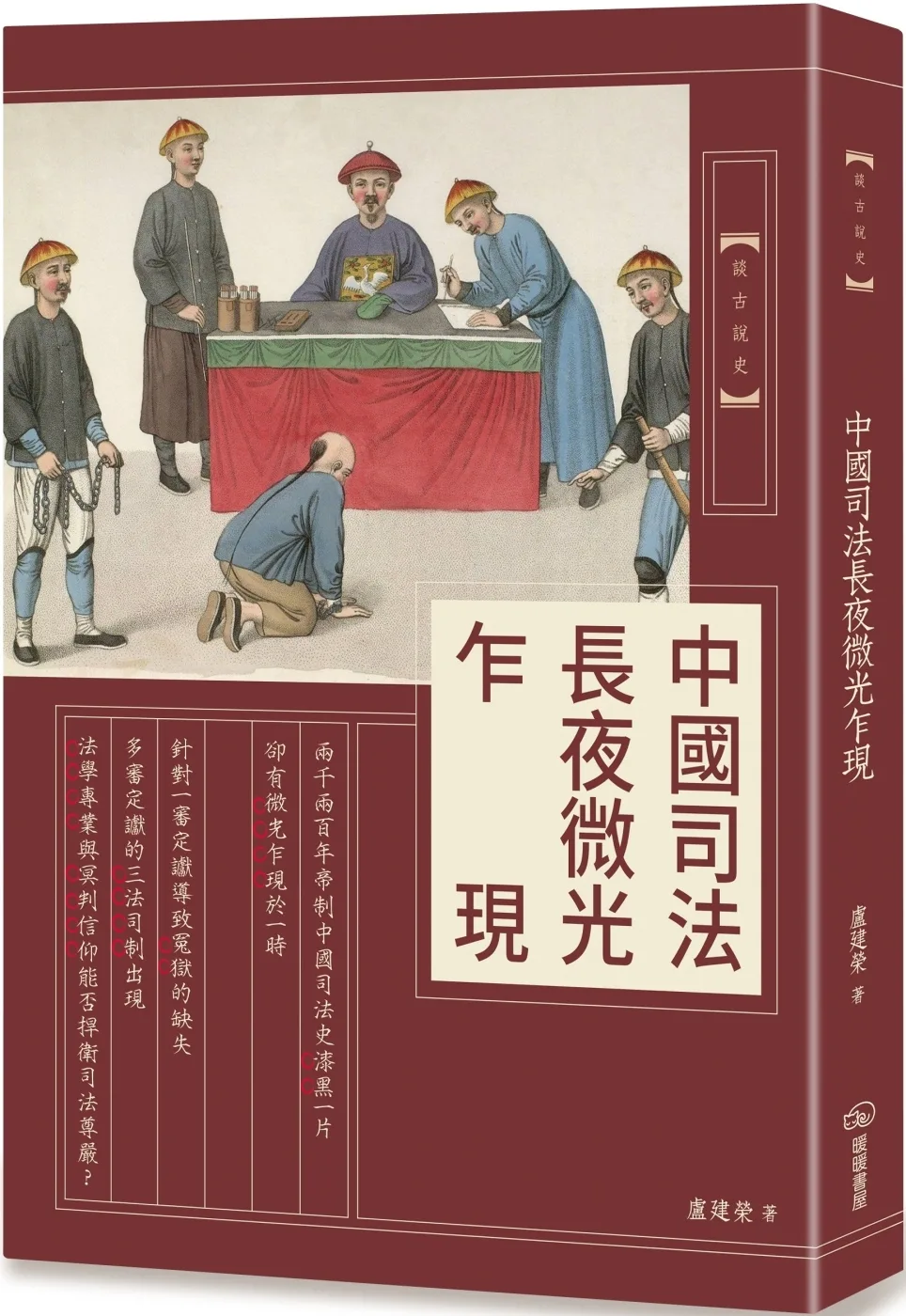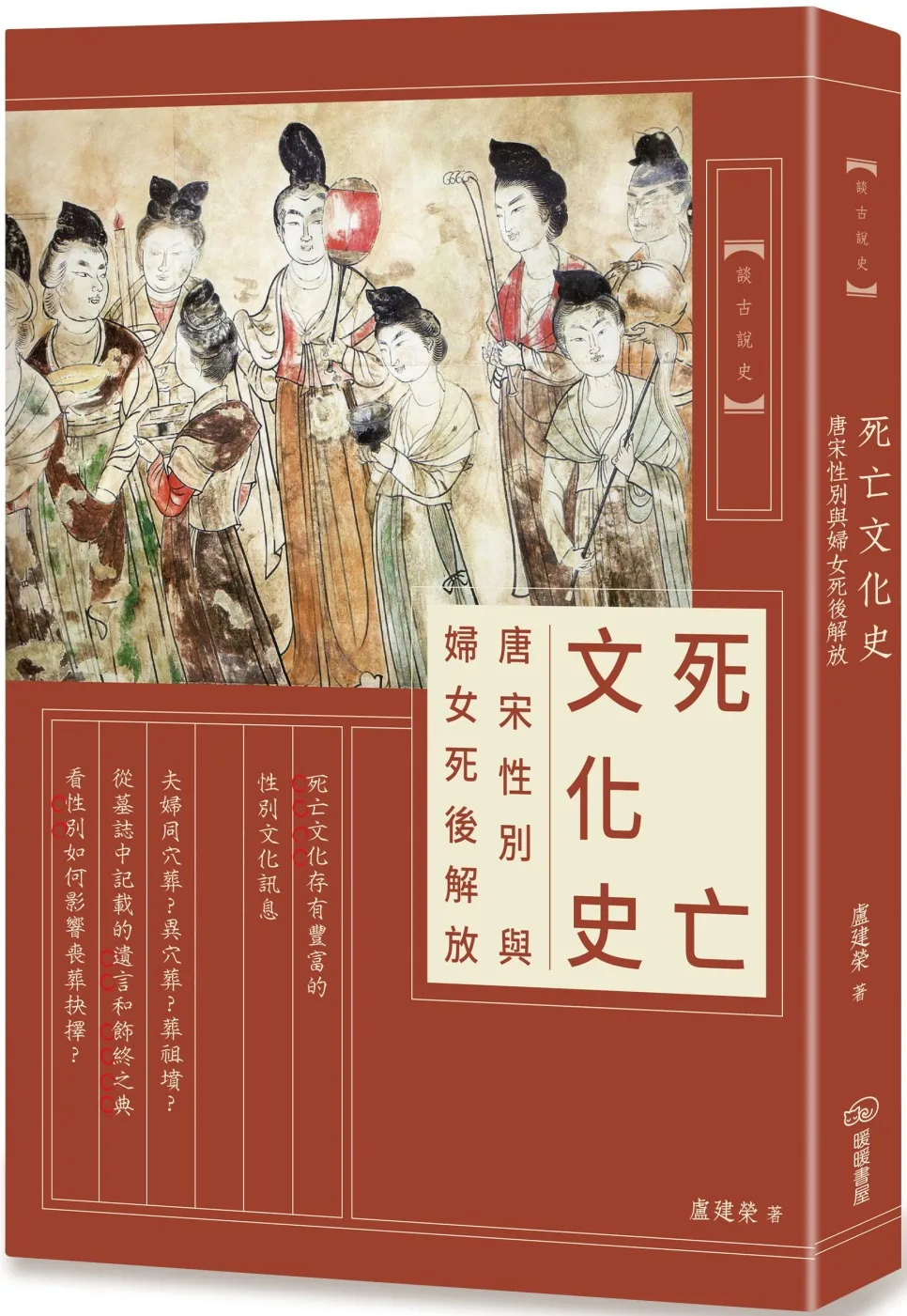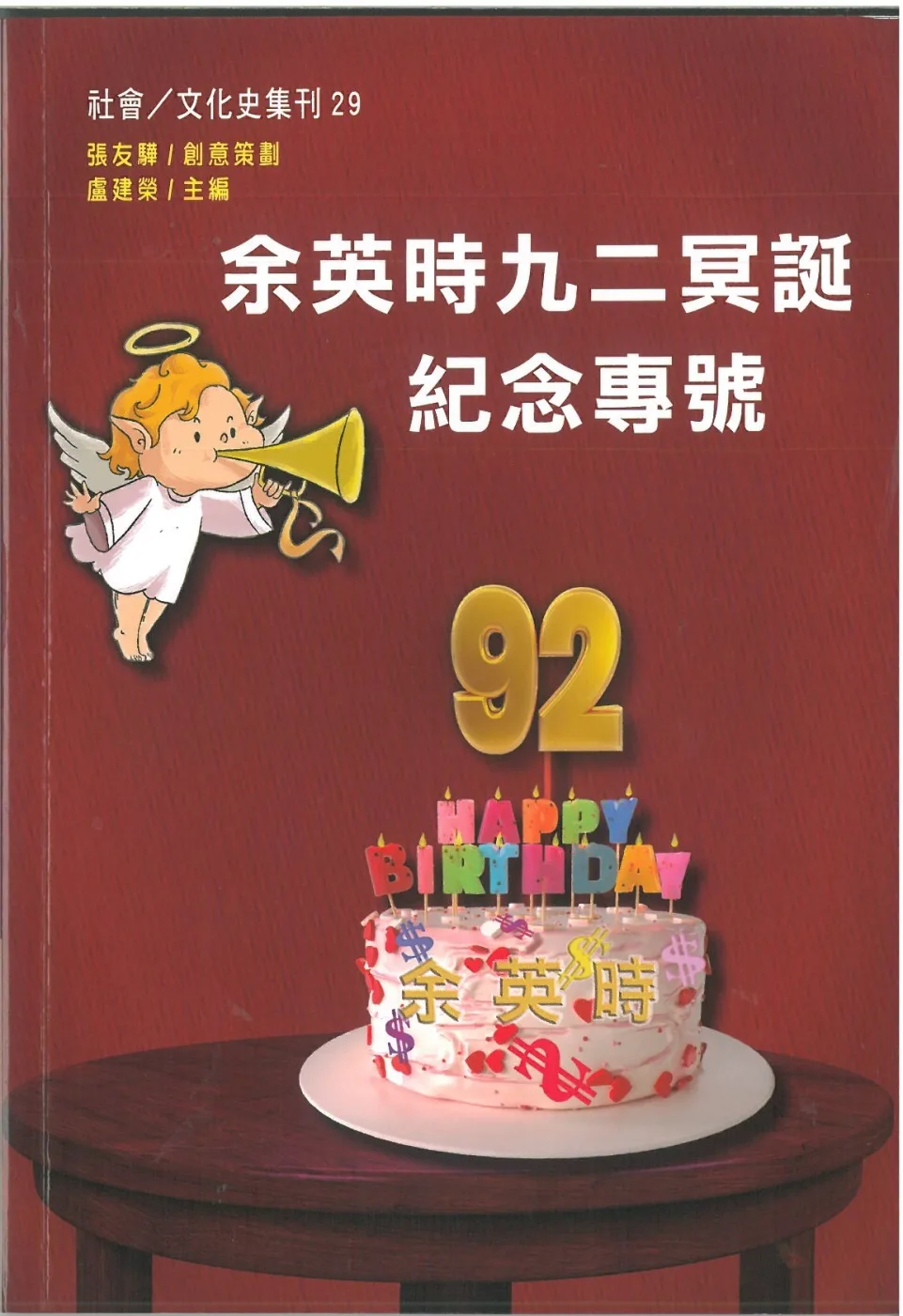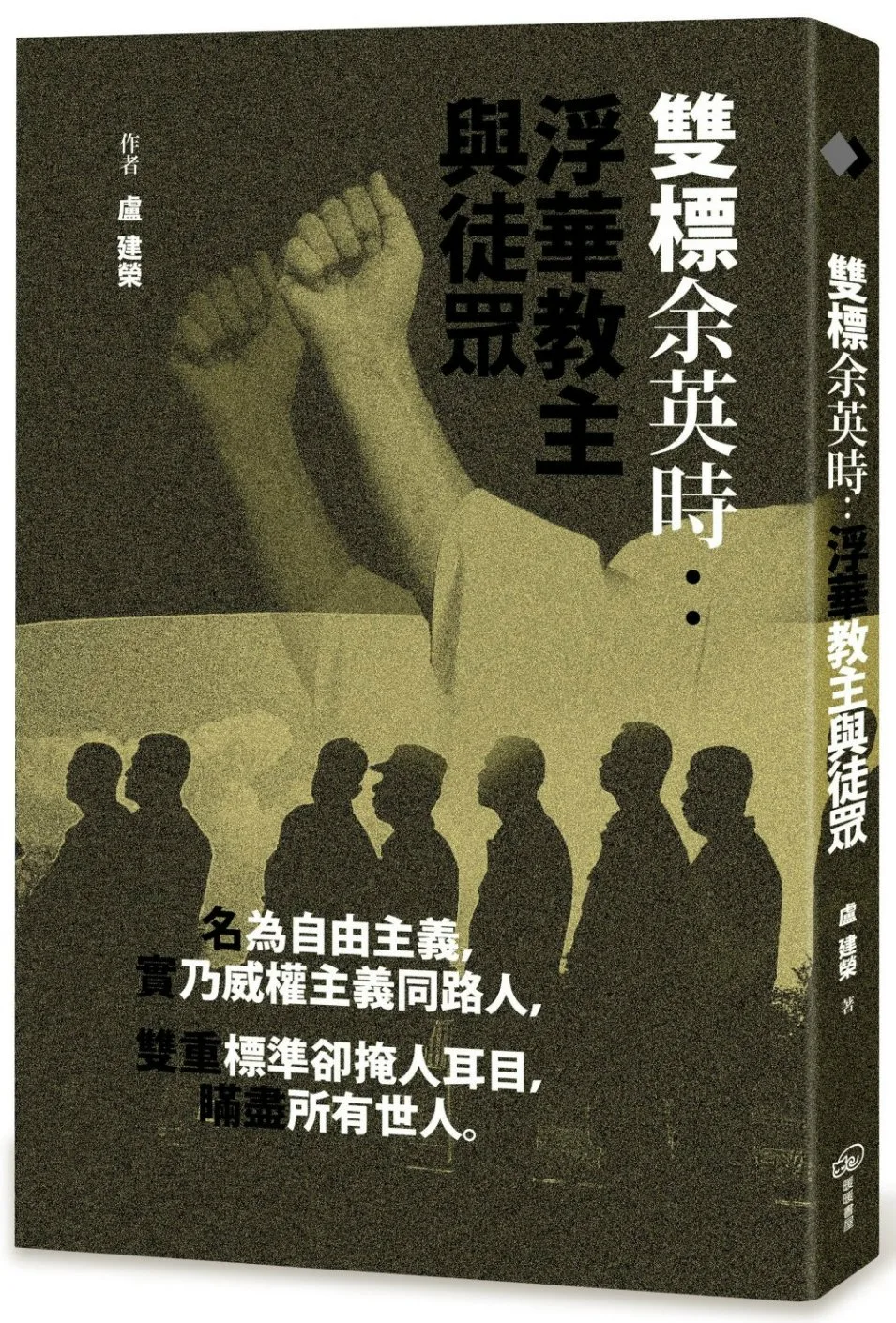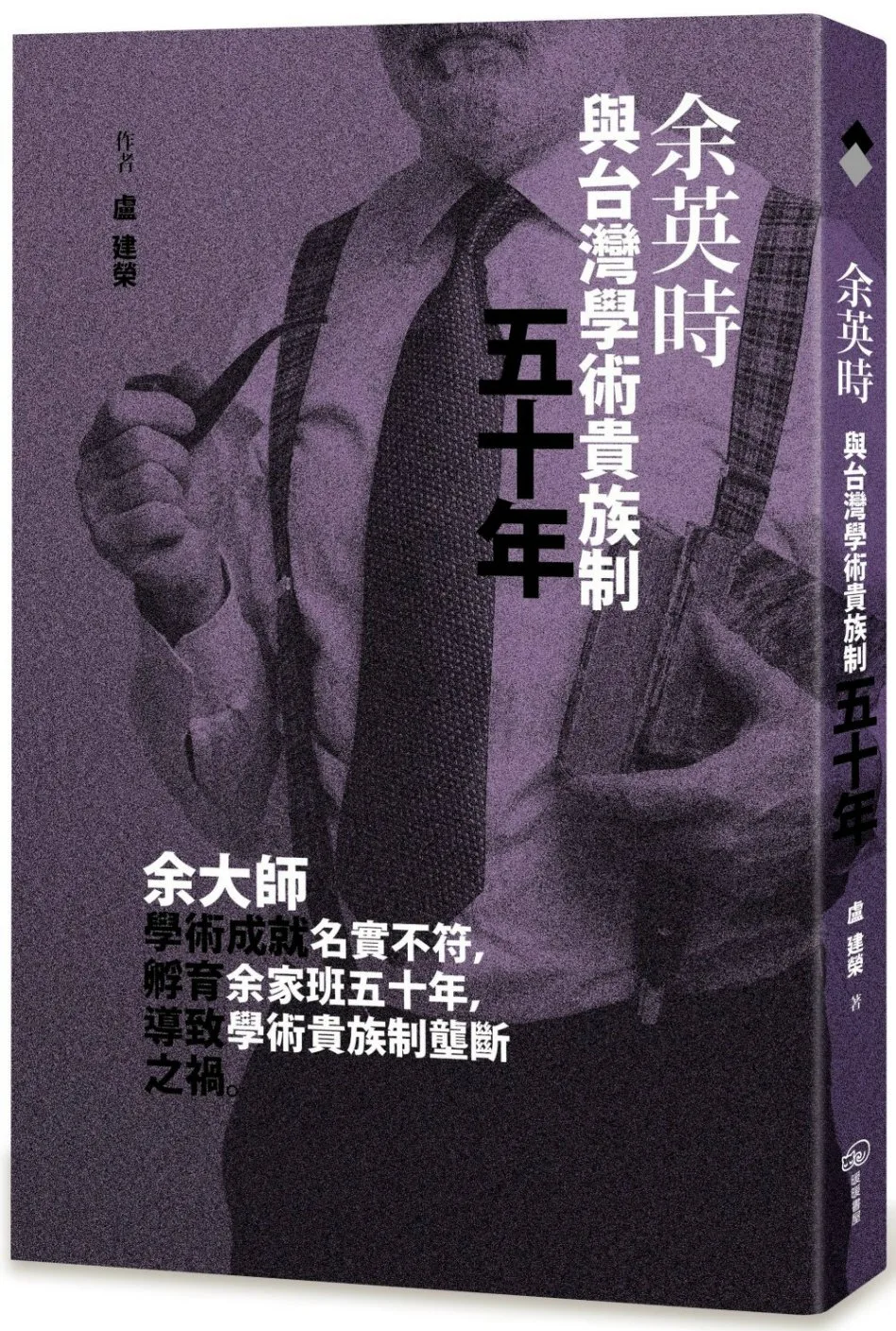代自序
唯將剩勇追殘寇
一
我的職涯軌跡上,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做了一次大膽的戰略大轉進。那年夏天之前十二年,我從本科生,中經碩士生,到即將前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我定位自己投入魏晉南北朝思想史這個研究領域中。這表示我的專長領域有二,一是魏晉南北朝史這個斷代,二是思想史這個史學領域。此時,我的學術成果是專書三本,論文數篇。這時史語所是不興思想史這一套路數的,該機構主要做政治史,社會史是它剛起步新的學術工作領域,投身其間的還只是少數。我那時在思量,若搞思想史恐會與該所學風有所扞格,不利發展,改走政治�社會史路線,方是明智之舉。若然,還要拘泥在投身十年的魏晉南北朝史範圍嗎?想來往下做隋唐史,局面會比較寬闊。思慮至此,就要決定一個大題目來當攻克的目標。我那時想做的是唐朝官僚體系這個大題目。接下來便是蒐集資料,那無非是兩《唐書》和《全唐文》這三部大套書了。就這樣,從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短短二年中,完成三文,先後針對太常卿、少官員,戶部尚書、侍郎官員,以及理財與文化核心衝撞等三個題目,且一一予以發表。我這個行動立刻驚動我的同輩同事,以及所外唐史同行。要知我從魏晉斷代跨到隋唐斷代,這已是一大跨界,遑論從思想史改作政治�社會史,更是另一跨界。所中同仁中,有同年黃寬重(南宋史專業,台大歷史碩、博士)、還有大兩歲的何大安(語言學專業,台大中文碩、博士),都先後給我善意的警告。他們的好意,我很是心領,但他們不知我的學術野心,我又不能說破。當時大家都是助理研究員,但他倆眼前目標是趕緊拿到博士、便升成副研究員,我的則是發表一系列研究,刊在所內《集刊》上、以利升等。這筆帳屬於眼前生計,無關學術鴻圖遠謀。我的學術鴻圖是跨朝代研究、且跳脫斷代思維,這在當時講來太過驚世駭俗,只能待我日後達成目標後再明說了。中國史上許多跨代重大問題無由發掘,便與史家畫地自限、以耽溺斷代為已足,有絕大關係。跳脫斷代思維陷阱,何其重要!
二
我在所內討論會,報告我的第三文——即理財術與文化核心的衝突——時,我的唐史同行張榮芳(台大歷史碩士畢,東海大學歷史系講師)以行道先行者自許,公然向我叫板。他話中大意是說,他從事歷史七、八年,才發表關於唐國史館制碩論,外加論文二、三篇,而你短短兩年便刊文兩篇,現在還準備刊第三篇,無乃太超過乎?由於他不是針對論文內容發言,而是質疑我的治學態度。我就不加理會,冷冷地看著他,不發一語。之後,我唐史系列研究第三文刊出,其中有條註,談及杜佑出身,指出張榮芳的杜佑史學研究一文(按:發表於台大《史原》雜誌上),是抄鄭鶴聲文,且將鄭的錯解照樣給抄了。拙文刊出後,我還特別邀張某到我研究室小坐片刻,並給他看我寫他抄鄭文那條註文,請他指正。這回輪到張某無言以對。這應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他後來來所發表關於唐朝開始徵茶稅一文,我向主辦討論會的黃寬重指控,張某文乃抄大陸學者文。這引起軒然大波,但無疾而終,但至少張知東窗事發,就不敢發表了。張君在一九八七年發表唐京兆尹遷轉一文(按:由學生書局出版),升成副教授,再之後就停產至今,垂三十多年。
三
我的跨界之舉引起的業內漣漪大體如上,不詳遍舉。這是在說台灣史界保守的一個側面。我再回到我的系列研究事上。一九八四年我又完成另三文,次年刊登其中兩文在史語所集刊上。我還來不及處理第三文(即系列研究的第六文)便出國念書去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將之改寫、並投刊在台大《文史哲》學報上。我這個系研究花了三年(1981-1984)時光,算是告一段落。我的唐代官僚體系這個大題,原先規畫做學術官、財經官,以及司法官等三個區塊,分別就太常卿少,戶部正副首長,以及大理寺卿少等三類官進行試探的。其中,大理卿少一文很長,因出國也沒空去發表。回國後我發現,王吉林的一位碩士生以大理卿少寫成碩論。此君叫陳登武。我於八○年代發表的五文都送給王吉林,想來陳君從王氏處看到拙文吧。陳君之後向高明士拜碼頭,變成高門的侍從者之一,那是後話。要之,我一起手就處理了理財與文化衝突,司法如何不獨立,以及禮知識的建構與傳播等三重大問題。這在我同僚而言,是不可想像的事。後來司法這塊,我於二○○○至二○○二年,一連發表三,更在二○○四年給予改寫並出版《鐵面急先鋒》(台北:麥田)。
四
二○○九年,我將唐財經官五文改寫成專書:《聚斂的迷思》,交五南出版社出版。原以為我從魏晉跨足隋唐事就此結案。但竟然沒完,仍有後續。二○一二年夏秋之交,好友張仲民教授(復旦大學歷史系任職)寄來由余欣主編的中古史研究系列六書,其中有仇鹿鳴:《魏晉之降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絡》(上海古籍,2012)一書。我稍事翻讀,驚為天人,始知後生可畏。二○一八年末我趁上海師範大學開會之便,請張仲民為我約見仇氏。這是我與仇先生訂交之始。二○一九年初,仇鹿鳴寄贈新著:《長安與河北之間》,我讀過一遍,確信是本重要著述,便寫一書評(刊於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二十三期二○一九年一月,頁159-163。)以酬雅意。仇鹿鳴此書,便是一次跨界演出。他已是魏晉政治�社會史陣地儼然一大家了,不以此為已足,約莫二○○八年之後轉換跑道降及隋唐史,才數年光景,便在唐史領域立下無數斬將搴旗之功。仇氏的職涯軌跡竟與我的暗合:從二、三十歲的魏晉政治�社會史的一位尖兵,成功轉型為隋唐政治�社會史名家!我暗中將仇先生許為跨界同道,並引以為樂。
五
二○○九年《聚斂的迷思》(台北:五南)出版後,因讀了英國大史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書,又對人類財政學知識有所擴充。我在寫《唐宋新聞傳播史》(新高地,2013),就引用到弗格森的看法。這三、四年我對《聚斂的迷思》增補出版事,益覺迫切。既然北京三聯出版計畫受阻,乃試圖改而在台出版。就在此時,天降神兵,虧得老友吳宏哲兄(屏榮食品公司董事長)仗義疏財,聞知上情,便贊助我出版以圓我夢,真是隆情高誼、古道熱腸啊!
六
北京三聯如何從中殺出呢?容我細說從頭。二○一五年,我赴天津開開會,會議中,侯杰兄引介下認識了北京三聯的主編張龍先生。在相談之下,敲定了《聚斂的迷思》等五部書,交由三聯出簡體字版。之後出版合約也簽了,預計二○一七年推出兩本,其中之一即《聚斂的迷思》,且通過審查,內容無失,惟書名必須改成:《唐代的財經官們》。原本張龍是備感挫折的,我還勸他說,審批可出版,已經贏了,就不必糾結書名。張龍聽了才釋懷。就在該年三月,張龍正準備開雕付印,竟傳來港台學者即使審查通過,也要重新送審。結果這一拖,三年就過去了,任憑書局如何催請審查單位盡快放行,就是遲遲沒回音。
七
此期間,北京史界流傳王汎森為阻我大陸出書,給我下套,因而被查禁的消息。這個消息最後也傳回了台灣,連旅台陸生都言之鑿鑿了。王汎森會這樣做嗎?我且替他辯護一番。沒錯,他為了我掀底中研院史語所三人抄李敖事,大動干戈,不惜出錢要邱仲麟(明史專家)、李建民(秦漢史專家)兩位細漢興訟告我誹謗。再如王汎森借審查教育部傑出獎案、選中文化大學文學院長林冠群授以五十萬大獎,用以收買林某發動其投票部隊將我逐出文大。這是他展開對我的絕戶之計,諸如用官司令我傾家蕩產、讓我沒了文大教職以致生活無著等。又如,王汎森威脅利誘時英出版社不要代為發行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這是封我嘴、消我音。以上我都可以理解不循正途,但王之奸謀終究未能得逞。
如今,王會用密告北京方式阻我在大陸出書嗎?我不信的理由有一點。他是研究清初文字獄的專家,深悉專制荼毒文化其為害之烈,是沒有人能原諒的犯行。他在所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台北:聯經,2013)中,在第四、第七、第八等三章,大談清初禁書,在第十二章,大談道咸以降禁書復出意義。可見他知曉禁書乃反文化惡行,禁書只能禁其一時無法持久。在這裡,王汎森會運用現行禁書機制,以形同告密形式間接做成禁書的目的嗎?這樣的反學術實踐之理,只會讓王汎森拿研究專制暴政作為增益其心術血滴子的樣態。我不信,他利令智昏到做出超出底線的事。
最近我合理懷疑王汎森更膽大到繼續實踐其罪及我妻孥的謀略,欲羅織拙荊公務員不法的罪名,動員中研院政風處調查。更在調查期間有《週刊王》(市面八卦雜誌之一)連登兩期在網路上,數落拙荊苛扣助理和公私不分兩條罪名。倘無中研院高層故意洩密給中時系統,《週刊王》如何取得中研院內部調查資訊?如所周知,其旗下《週刊王》是《中國時報》(按:下稱《中時》)的搖尾巴系統,而王汎森又是《中國時報》力捧的傑出員工,位居該報筆陣之一。王在二十幾歲時,在《中時》聽差辦事,他的同期如今貴為《中時》高層,常邀他主筆、評論五四運動、民國學術、教育等事,並出以做成「社論」刊出。所以,《中時》是王汎森手中的大殺器。他要污名化誰,一通電話搞定。就像他致電時英老闆吳某(按:與王汎森在《中時》共事過),切勿代為發行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者然。《週刊王》沒事、會出動政治組主任撰文欲置拙荊於死地,想來都與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二十七期專號:「中研院『毀』人不倦」,揭露王汎森乃阻擋拙荊升等的兩藏鏡人之一,脫不了關係。再加上,今年二月好友廖伯源去世,我特別揀出廖生前於一九九五年所撰揭發史語所黑暗的腐敗一文,刊在大陸「中古史研究」公眾號上。由事後可能王的嘍囉大跳其腳,跑去騷擾上述公眾號、要逼人下架廖文來看,這些打手所為不正曲折反映其主子王汎森氣急敗壞的「聖人氣象」嗎?更有趣的,從時間軸看,從拙編第二十七期揭密王汎森「奇」行,中經廖文刊載大陸公眾號,以迄四月初,《週刊王》連登兩期中研院還在內部調查、且不確定(按:之後證明為子虛烏有的假消息)的「不法案子」。這不正是王汎森最常慣用的手法:未審先判的大謀略嗎?
八
三聯要出我「唐代五部曲」事,我是到處宣揚,深恐王汎森不壞我好事。之後似乎應驗王煞不住出手的誘惑,他還是對我下套了。姑不論主管單位是否聽信有人密告我是「台獨」所以查禁我書,這後果是兩面刃。一方面我不能在大陸出書,只是少賺銀兩的枝微末節,另一方面,大陸出海外學者書,那是造福大陸讀者,使其可用廉價購得海外之書,如今此路竟為王汎森所阻嗎?若然,這不是大陸千千萬萬讀者的損失嗎!故爾大陸查禁我書,於我小損固有之,但對大陸讀者則大失其利,這才是外傳這件王密告之舉一事之大者啊。台灣影藝界出了黃安、為向北京表忠,密告台灣藝人使之喪失大陸舞台。如今出了位史界黃安,向北京告密說某人是「台獨」便阻其書在陸出版。這兩位黃安允文允諜,鬥爭手法高邁古今呀!黃安所為為自絕於鄉親,王汎森乃聰明人,諒他不致昏聵至此。
再說王汎森能在台灣隻手遮天阻我出書嗎?當然不能。我自費都可以了,遑論如今由吳董事長宏哲先生出面玉成我在台再版了。我誠心鼓勵王汎森你繼續跳腳,放膽玩密告、搞禁書啊。你有本事說動民進黨政府查禁我書,我這才佩服你呀。這位少年院士在台灣玩法弄權久矣,如今假定真有跨足大陸去殘害我在大陸的讀友,那可真敬佩他為害文化事業可做大了。倘如是,他老兄研究清代文字獄之餘,學以致用大搞乾隆帝禁書案,如今效起乾隆大玩特玩文字獄來還蠻帶勁的。拙荊多承教導,感激不盡。我們後會有期。
以上環繞在本書背後,相關的時代學風、學術生態環境上的欺良霸弱,以及學術自由與禁書、告密等事,應比本書內容還要精采,提供我寫本大書都不止。但序文是客,不能壓主,就此打住。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一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