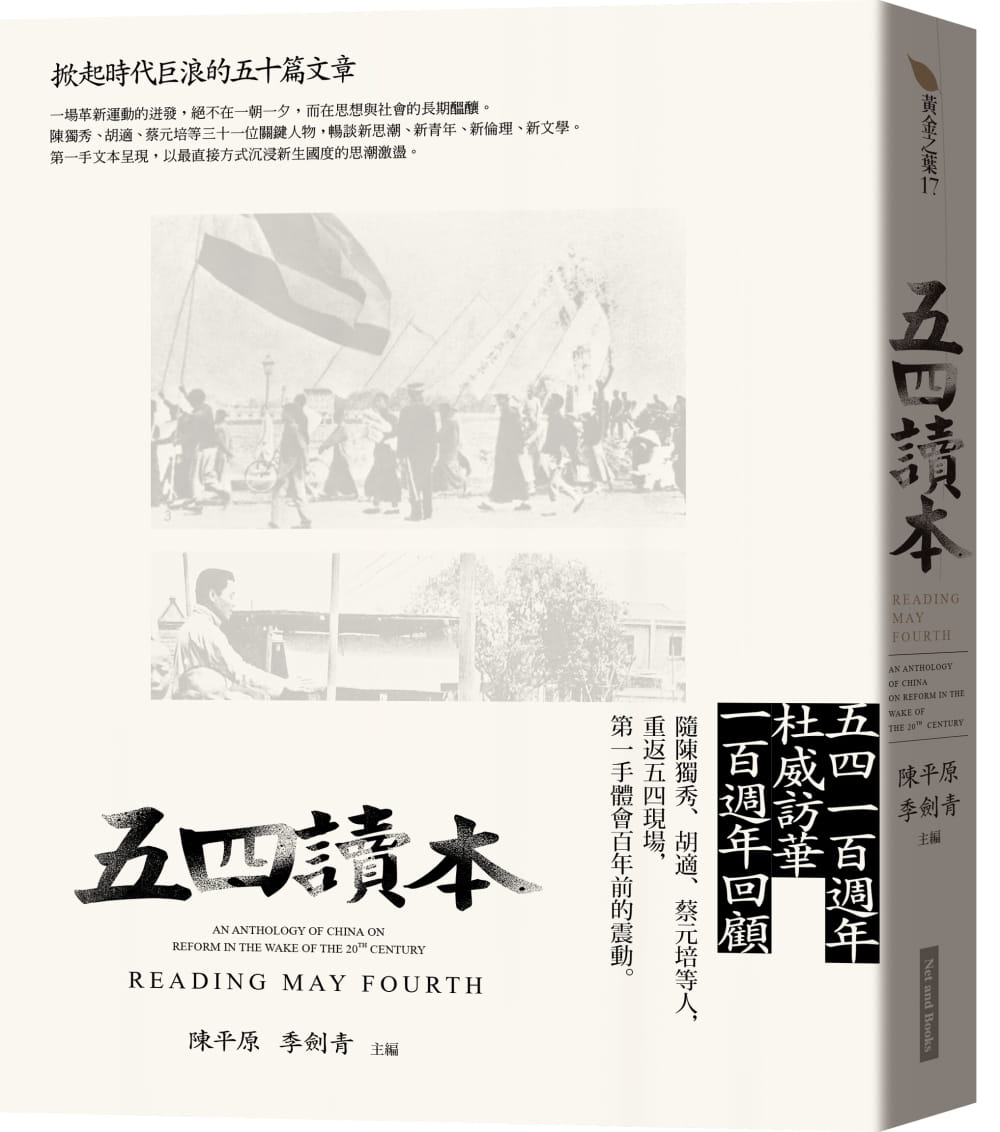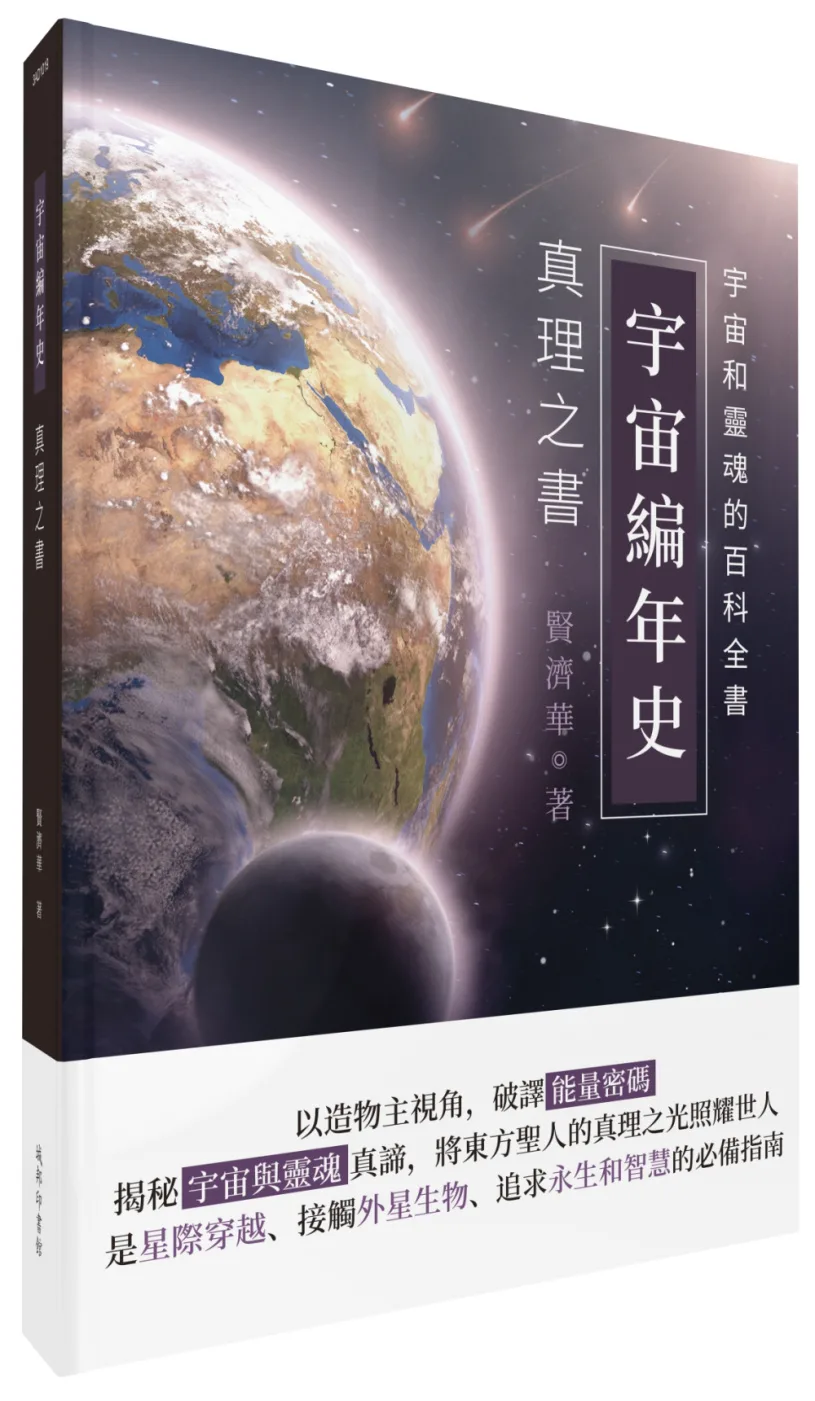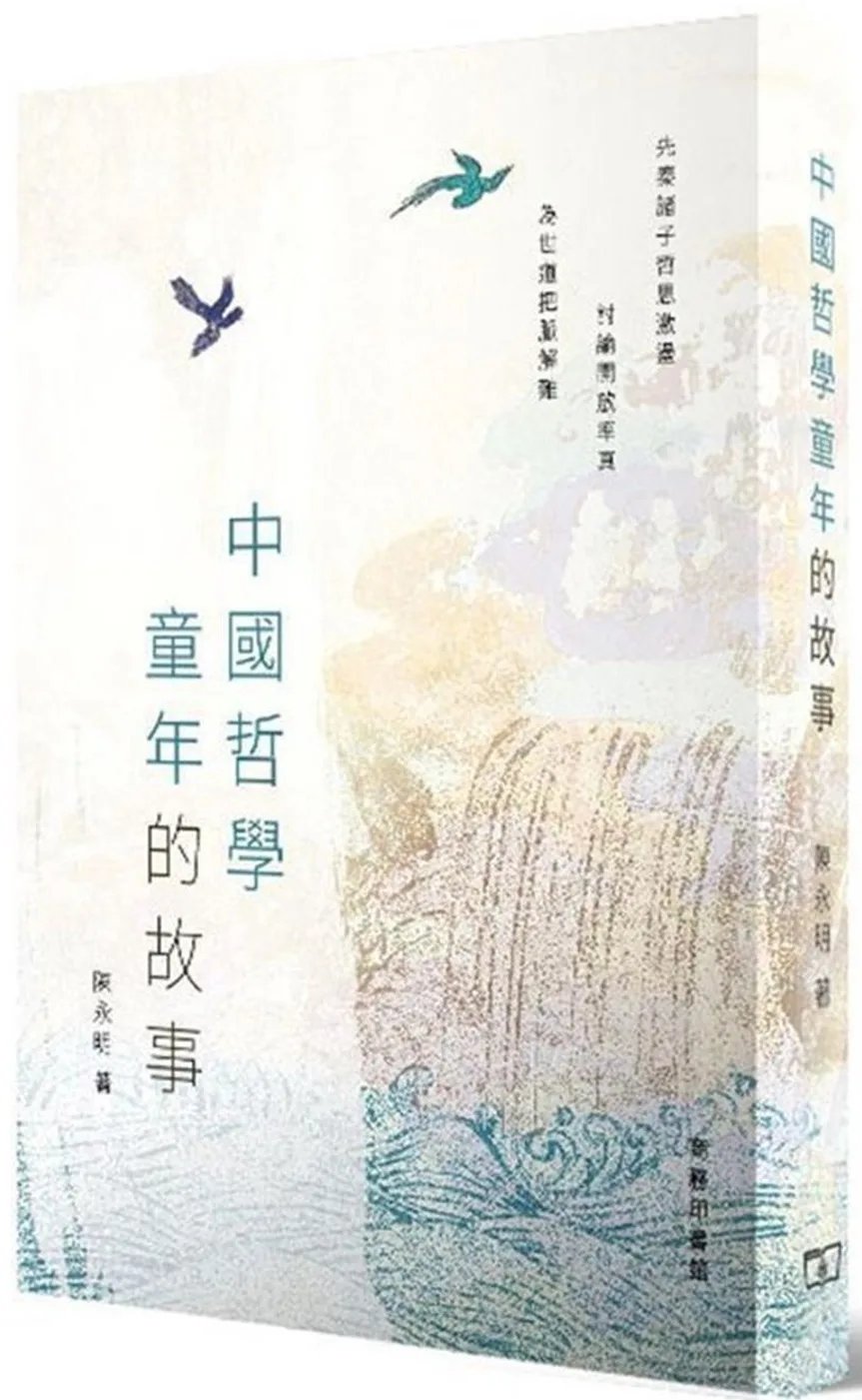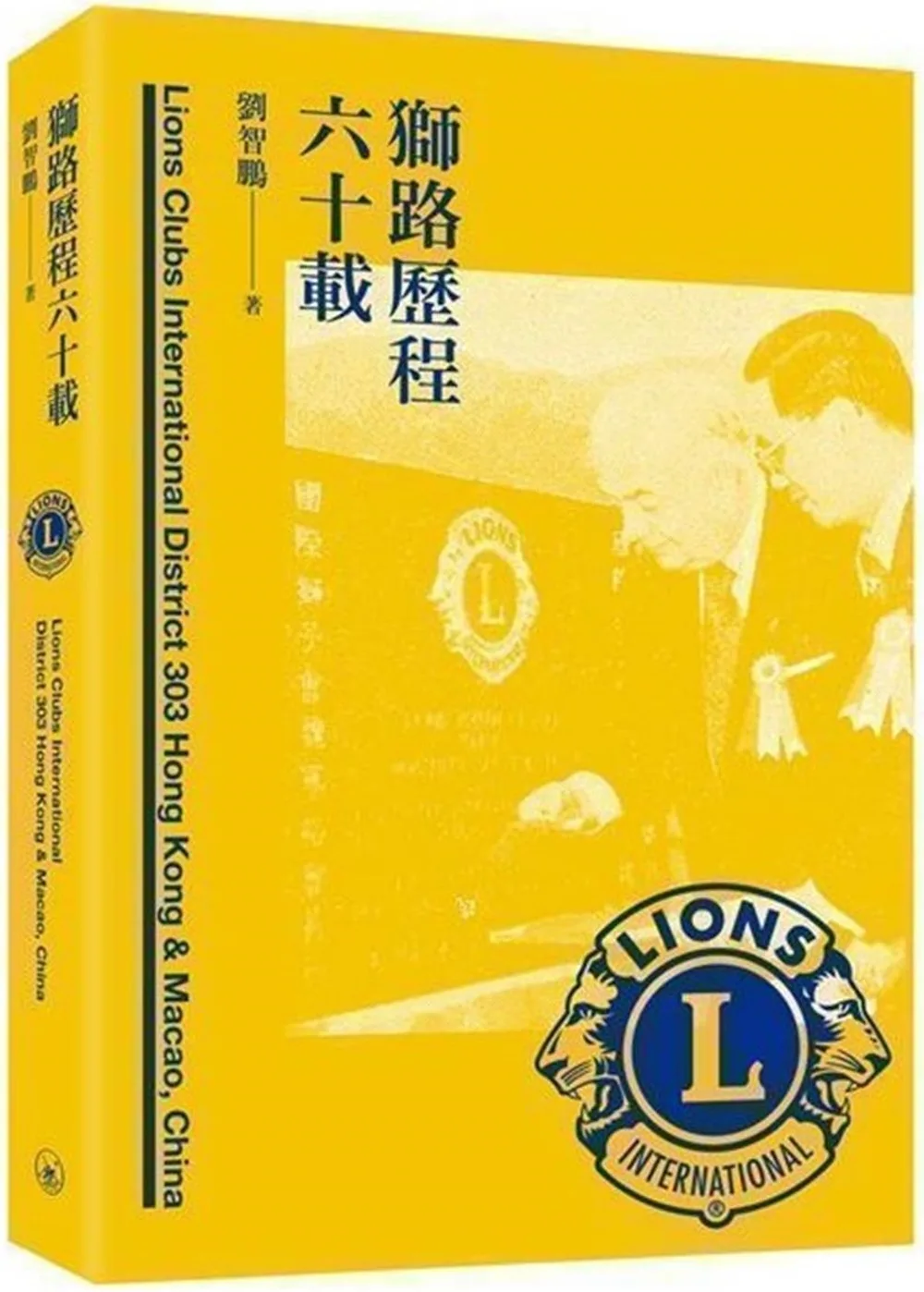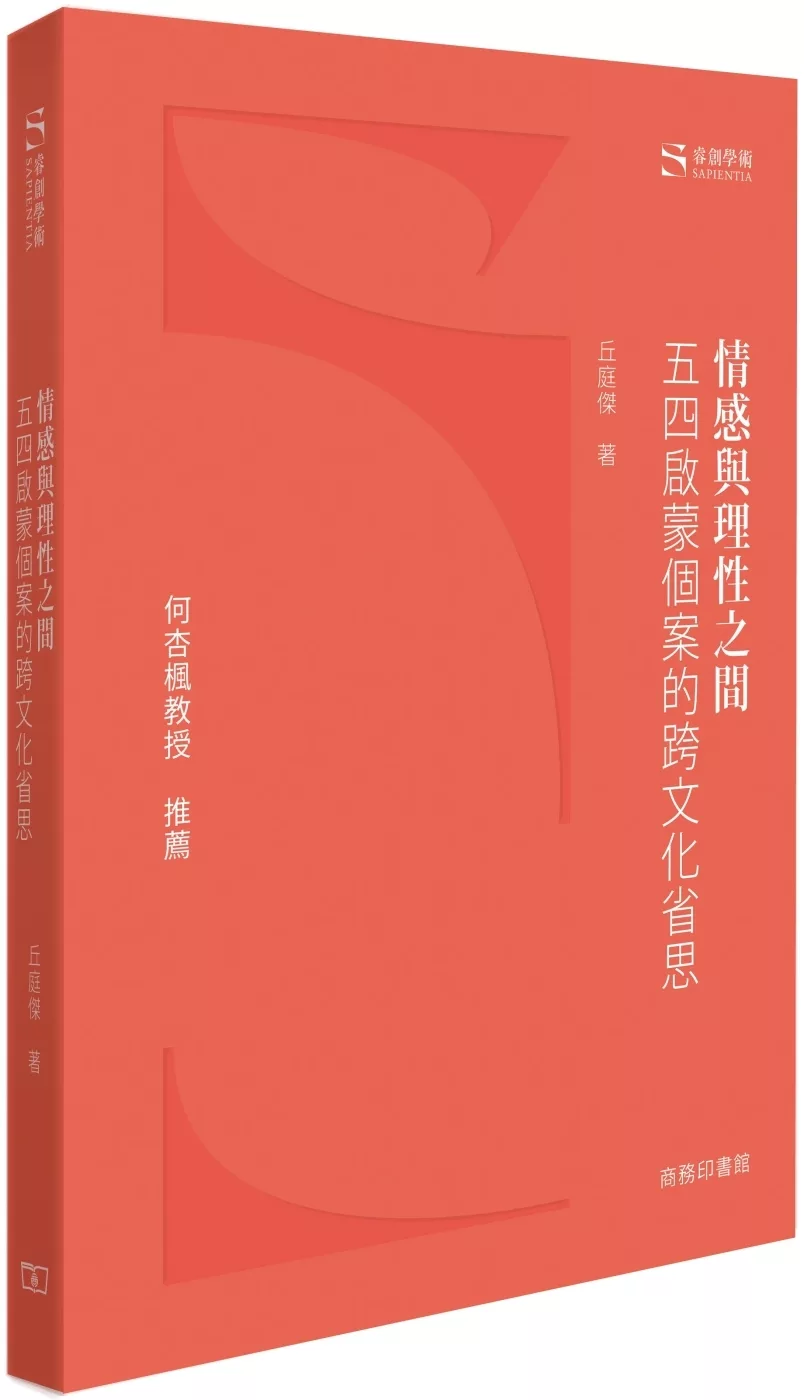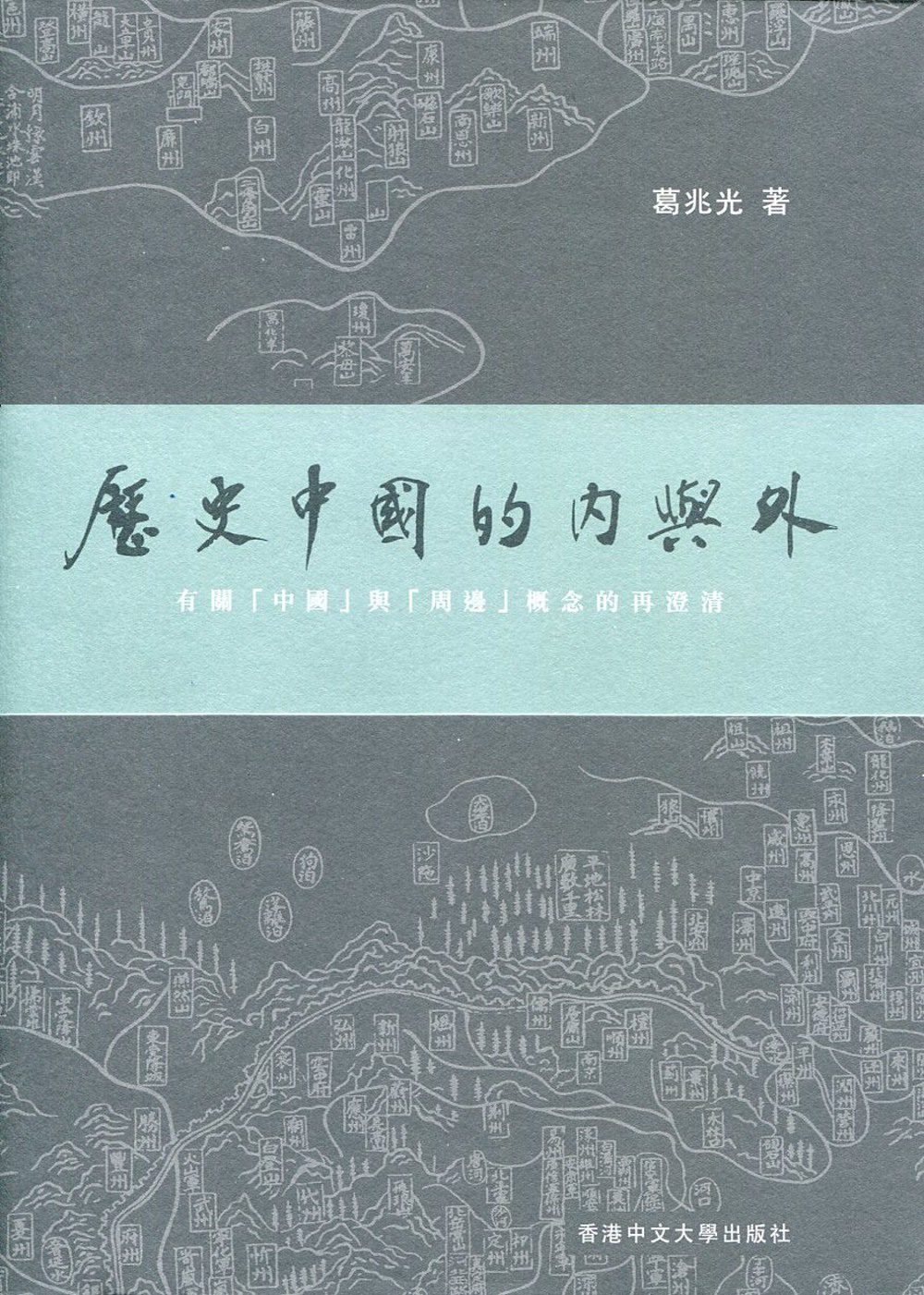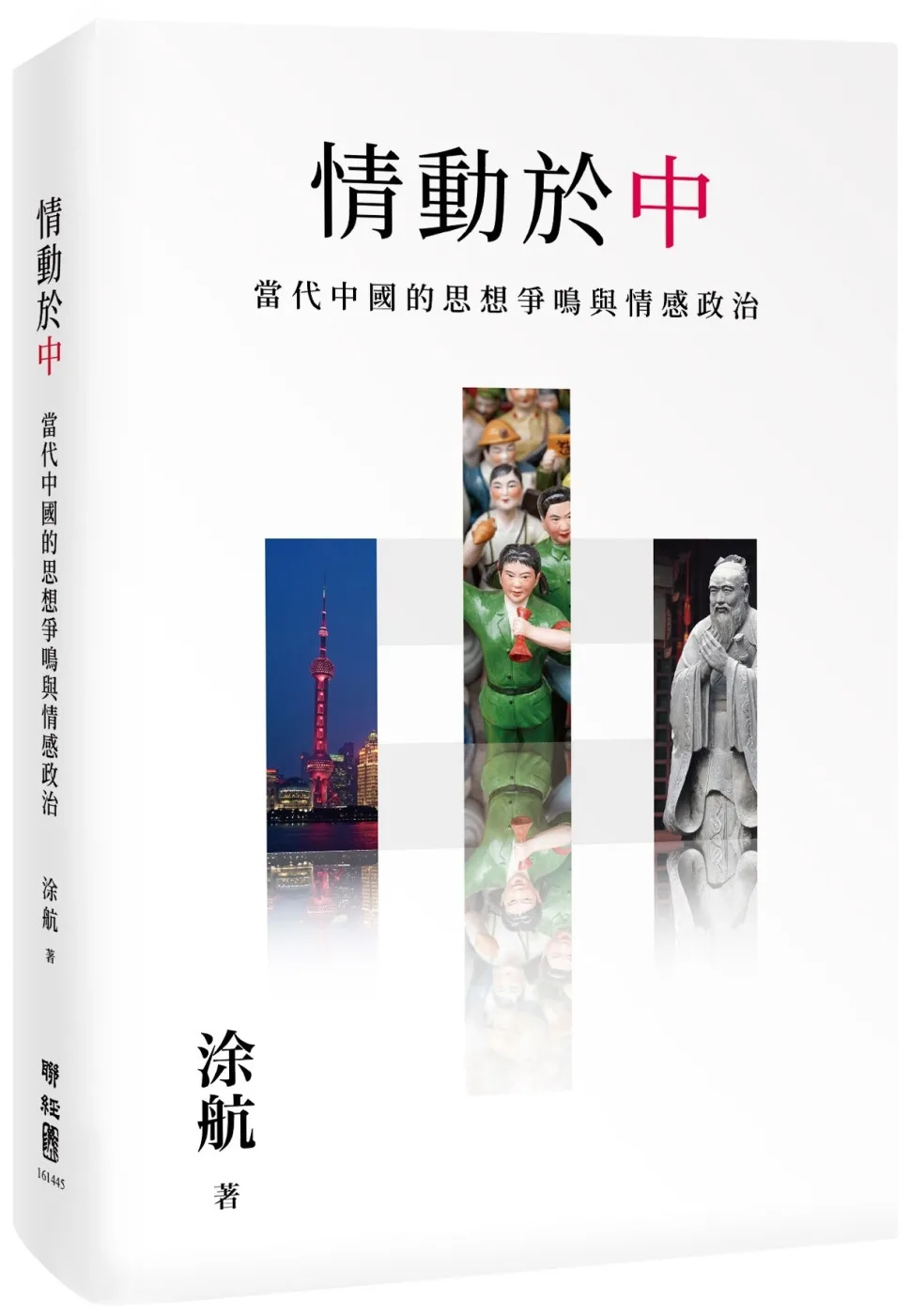序言
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五)的「導言」中,我寫下這麼一段話,今天看來依然適用: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後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係。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三千大學生天安門前集會遊行,那只是冰山一角。這次學潮最值得注意的,不在其規模或激烈程度,而在於「有備而來」。這裡指的不是有綱領、有組織、有領導(恰好相反,此次學潮的參與者有大致相同的精神傾向,但無統一立場與領導),而是制度基礎以及精神氛圍已經釀成,「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巴黎和會不過是一個觸媒,或者說一陣不期而至的「東風」,使得啟蒙思潮下逐漸成長起來的大、中學生們的「愛國心」與「新思想」噴薄而出。而由此樹立的一種外爭主權、內爭民主的反叛形象,召喚著此後一代代年輕人。
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喜歡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百年前的「五四」,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政治運作或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讓我等怦然心動,歆羨不已。
關於五四運動的時間跨度,歷來眾說紛紜。本讀本不做仔細考辨,而是取目前學界的主流意見,即從《新青年》創辦的一九一五年說起,到一九二二年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為止。選擇此雲蒸霞蔚的八年中五十篇有代表性的文獻,讓非專業的讀者能直接觸摸那段早已塵封的歷史,與一個世紀前的先賢對話,並做出自己的獨立判斷。比起簡單明瞭的教科書或愛恨分明的小冊子來,由若干基本文獻構成的「讀本」,雖也受編者立場的制約,但相對接近原始狀態,路徑縱橫交叉,聲音抑揚起伏,讀者經由仔細的辨析,可以建立屬於自己的歷史地圖。
經由一百年反覆的紀念、陳述與闡釋,「五四」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巨大無比的儲藏室,只要你闖進去,隨時都能找到自認為合適的食物或武器—可這不等於就是五四那代人的真實面貌。一次次帶有儀式感的五四紀念,自有其社會動員與文化建設的意義。但我以為更重要的,還是閱讀當年那些核心文本,經由自己的獨立判斷,與歷史展開深入對話;而不是人云亦云,記得某些標準答案。當然,這裡有個假設,那就是,五四不以「密室商談」見長,絕大部分立場與思考都落在紙面上,且當初曾公之於世。也就是說,本讀本呈現的,主要是「思想的五四」,而不是「行動的五四」—後者需要歷史學家借助各種公私檔案勾稽與重建。
本讀本中,直接談論作為學潮的五四運動的,主要是以下幾篇—梁漱溟的〈論學生事件〉、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許德珩的〈五四運動與青年的覺悟〉、孫中山的〈致海外國民黨同志書〉,以及梁啟超的〈「五四紀念日」感言〉。相對來說,涉及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的,更值得關注。以下略為摘引。
關於新思潮—胡適曾引述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價值」,來為五四新文化人眼中的「新思潮」定義:「我以為現在所謂『新思潮』,無論怎樣不一致,根本上同有這公共的一點—評判的態度。孔教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價值。文學的評論只是要重新估定舊文學的價值……這種評判的態度是新思潮運動的共同精神。」(〈新思潮的意義〉)杜亞泉不喜歡將「新思想」歸結為「推倒一切舊習慣」,認定那只是一種情緒,「僅有感性的衝動,而無理性的作用」,其作用近似「英國當十九世紀初期,勞動者以生活困難之要求,闖入工廠,摧毀機器」(〈何謂新思想〉)。蔡元培則意識到中國人受數千年專制思想影響,習慣排斥乃至消滅異己,故大學傾向於 「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具體說來就是:「無論為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
關於新青年—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陳獨秀給「新青年」定了六個指標: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敬告青年〉)。那位日後因任教育總長而備受魯迅等譏諷的章士釗,也曾這樣談論青年的職責:「總之,一國之文化,能保其所固有;一國之良政治,為國民力爭經營而來,斯其國有第一等存立之價值。此種責任,即在青年諸君。」(〈新時代之青年〉)至於學生領袖羅家倫,則在紀念五四運動一週年時,做了如下簡明扼要的表述:「總之五四以前的中國是氣息奄奄的靜的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是天機活潑的動的中國。『五四運動』的功勞就在使中國『動』!」(〈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底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
關於新倫理—陳獨秀在〈本誌罪案之答辯書〉中稱:「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則說:「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為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凡是不作工吃乾飯的人,都是強盜。強盜和強盜奪不正的資產,也是一種的強盜,沒有什麼差異。」接下來,該輪到魯迅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上陣了:「總而言之,覺醒的父母,完全應該是義務的,利他的,犧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國尤不易做。中國覺醒的人,為想隨順長者解放幼者,便須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就是開首所說的『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一件極偉大的要緊的事,也是一件極困苦艱難的事。」
關於新文學—胡適高舉「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大旗衝鋒陷陣,取得了突出的業績:「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才可算得真正國語。國語沒有文學,便沒有生命,便沒有價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發達。這是我這一篇文字的大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錢玄同藉為胡適的《嘗試集》作序,與之遙相呼應:「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裡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裡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嘗試集序〉)周作人則希望將工具的變革與思想的進步合而為一,創造一種「人的文學」:「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於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其中又可以分作兩項,(一)是正面的,寫這理想生活,或人間上達的可能性;(二)是側面的,寫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人的文學〉)
以提倡白話文為突破口,是個精彩的戰略選擇,這也是五四新文化人眾多探索中,文學革命功績最為顯著、也最為堅挺的緣故。談論兼及思想啟蒙、文學革命與政治抗爭的五四運動,可以突出政治與社會,也可以專注思想與文化,本讀本明顯傾向於後者。翻閱此讀本,有三點提醒讀者注意:
第一,作者絕少純粹的政治人物(只有一位孫中山,但不是當權派),基本上都是大學師生或媒體人,他們的發言不代表黨派,更多體現為讀書人對於中國命運的深沉思考。正因亂世英雄起四方,沒有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政府權威尚未建立),各種思潮、學說、政治立場都得到了很好的發聲機會,這也是五四時期言論格外活躍的緣故。在野諸君,「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大膽立論,橫衝直撞,雖說論戰時不免意氣用事,但絕無告密或以言入罪的可能。
第二,論戰各方立場差異很大,但所謂新舊之爭,只是相對而言。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被判為守舊的反面人物,在我看來,只是「不當令」而已—他們可能是上一幕的英雄(如林紓、章士釗),或下一幕的先知(如《學衡》諸君)。本讀本所收錄的,沒有絕對的反派。大家都在尋求救國救民的路徑,只是方向不同,策略有異,而「新文化」正是在各種力量相互對峙與衝撞中展開其神奇的「運動」的。其實,晚清開啟的西學東漸大潮,早已積蓄了足夠的能量,使得大多數讀書人明白,變革在所難免,復古沒有出路,爭論的癥結僅僅在於,是快跑還是慢走,是激進還是穩妥,是調和還是偏執。
第三,既然是報刊文章,基本上都是面對當下,絕少書齋裡的玄思。諸多評論、隨筆與雜感,表達直白且急切,單篇看不怎麼樣,合起來,方才明白那代人的思考及努力方向。「正因身處危機時刻,來不及深思熟慮,往往脫口而出,不夠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堅其說,各種主義與學說都提到了,但都沒能說透,留下了很多的縫隙,使得後來者有很大的對話、糾偏以及引申發揮的空間。這種既豐富多彩、又意猶未盡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陳平原〈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二十一世紀》二○一九年四月號)。
比起寫給專家的鴻篇巨制,編一冊面向公眾的讀本,很有必要,但並不容易。以十幾萬字的篇幅,呈現百年前那場以思想啟蒙為主體的運動,需認真謀篇佈局。本讀本的特點是:首先,以人帶文,基於我們對五四運動的理解,選擇三十一位重要人物,每人最多不超過三篇文章,以便呈現多種聲音,避免一家獨大;其次,所謂多元,並不排斥主導因素,新文化運動與北京大學關係極為密切,故北大人占了十九位(含兼課的錢玄同、魯迅,以及早退的林紓、沈雁冰);第三,不僅按慣例選錄論戰中截然對立的雙方,更考慮運動的各相關方,力圖呈現歷史的側面與背面;第四,這是一個以報章為中心的時代,當事人大都「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陳獨秀語),《新青年》入選文章最多,共十七篇,其次《東方雜誌》六篇,再次《每週評論》四篇、《新潮》及《晨報》各三篇,《學衡》及《新社會》各二篇;第五,全書不以人物或主題分類,所選文章一律按發表時間排列,以便呈現犬牙交錯的對話狀態;第六,以立論為主,不選文學作品(小說、詩歌、戲劇),文章篇幅實在太長的,採取節錄方式;第七,既不刪改,也不做注,*只是提供作者簡介,這對普通讀者是個挑戰—但我以為這種艱辛的閱讀是值得的。
陳平原
二○一九年三月十七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