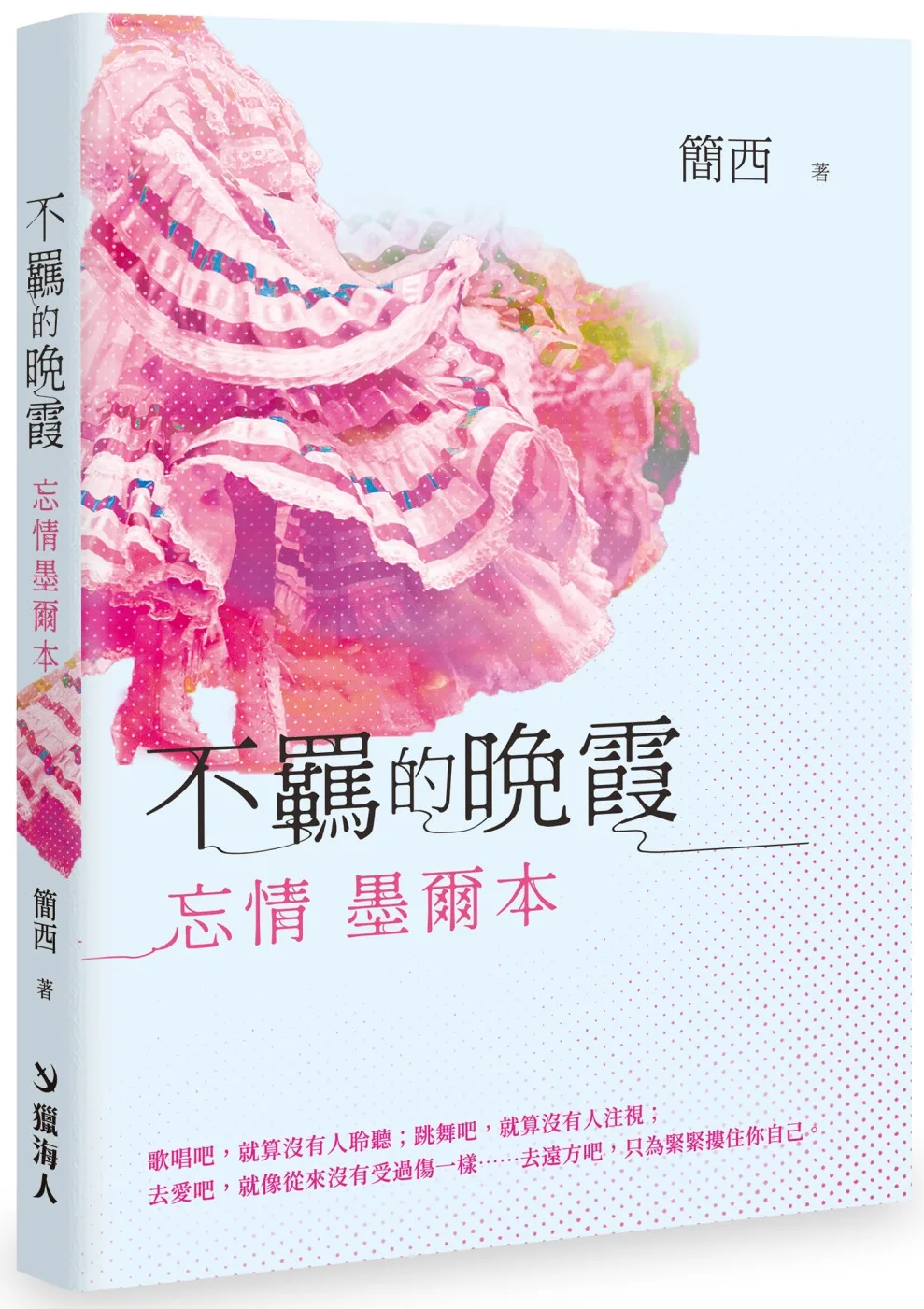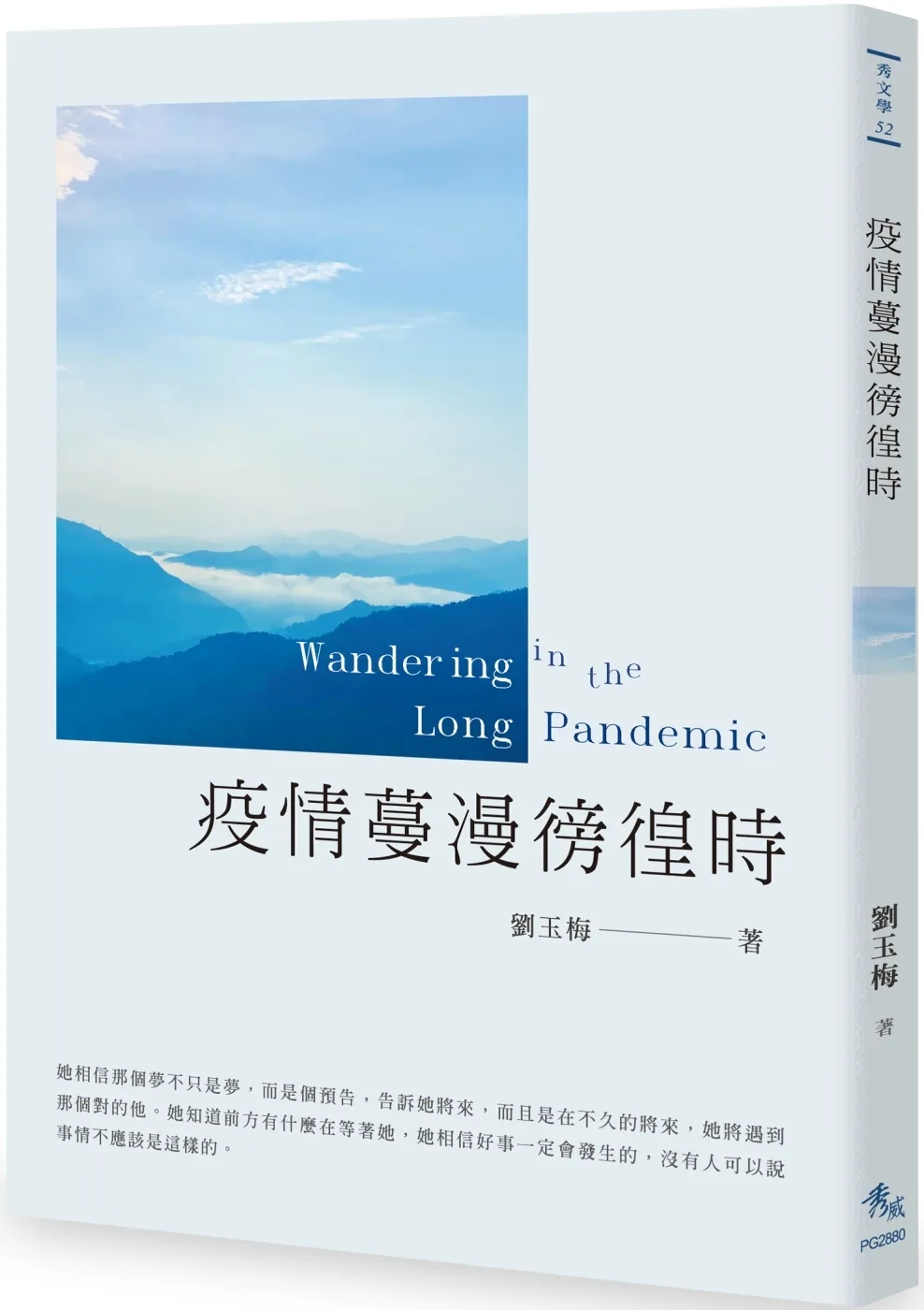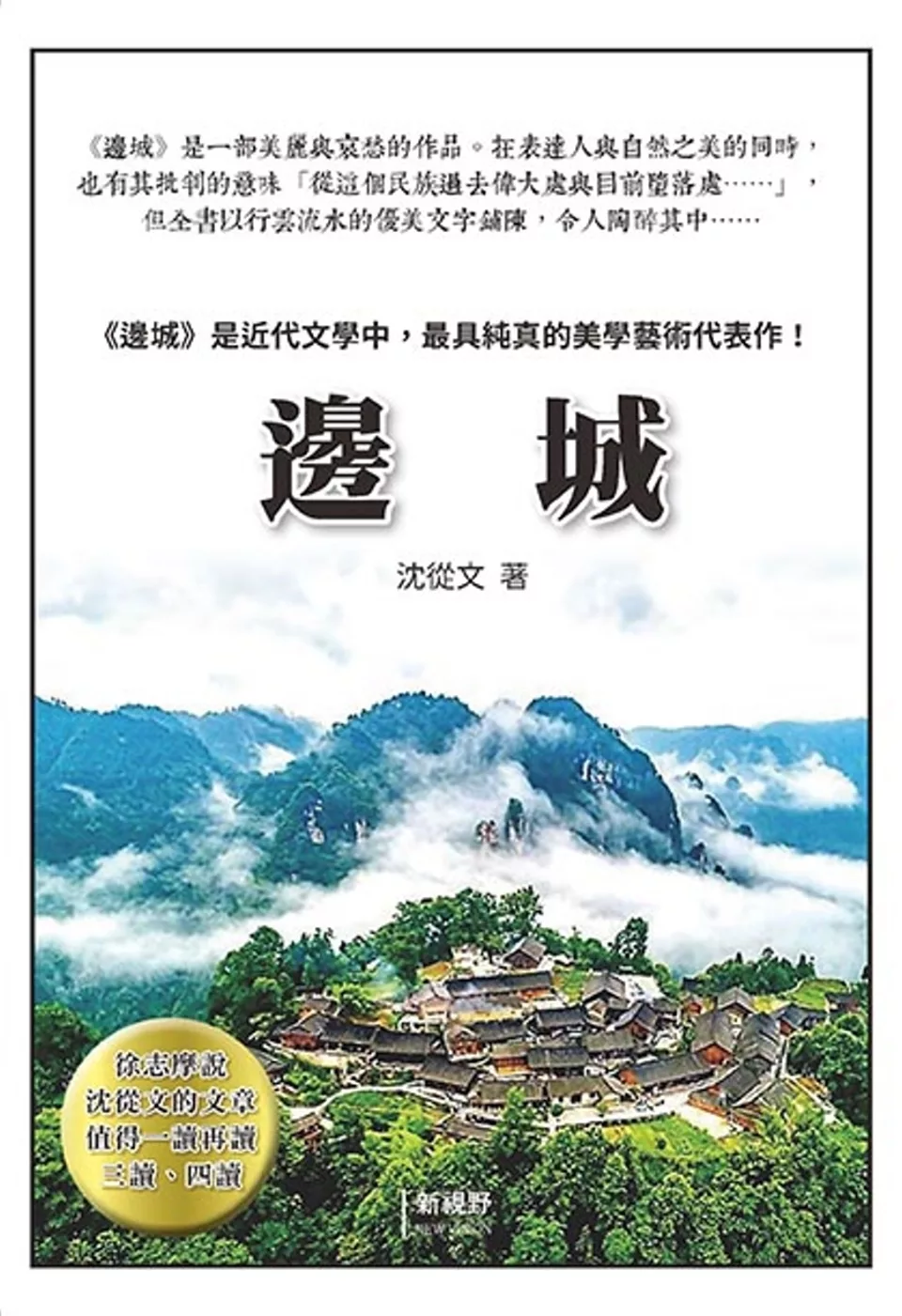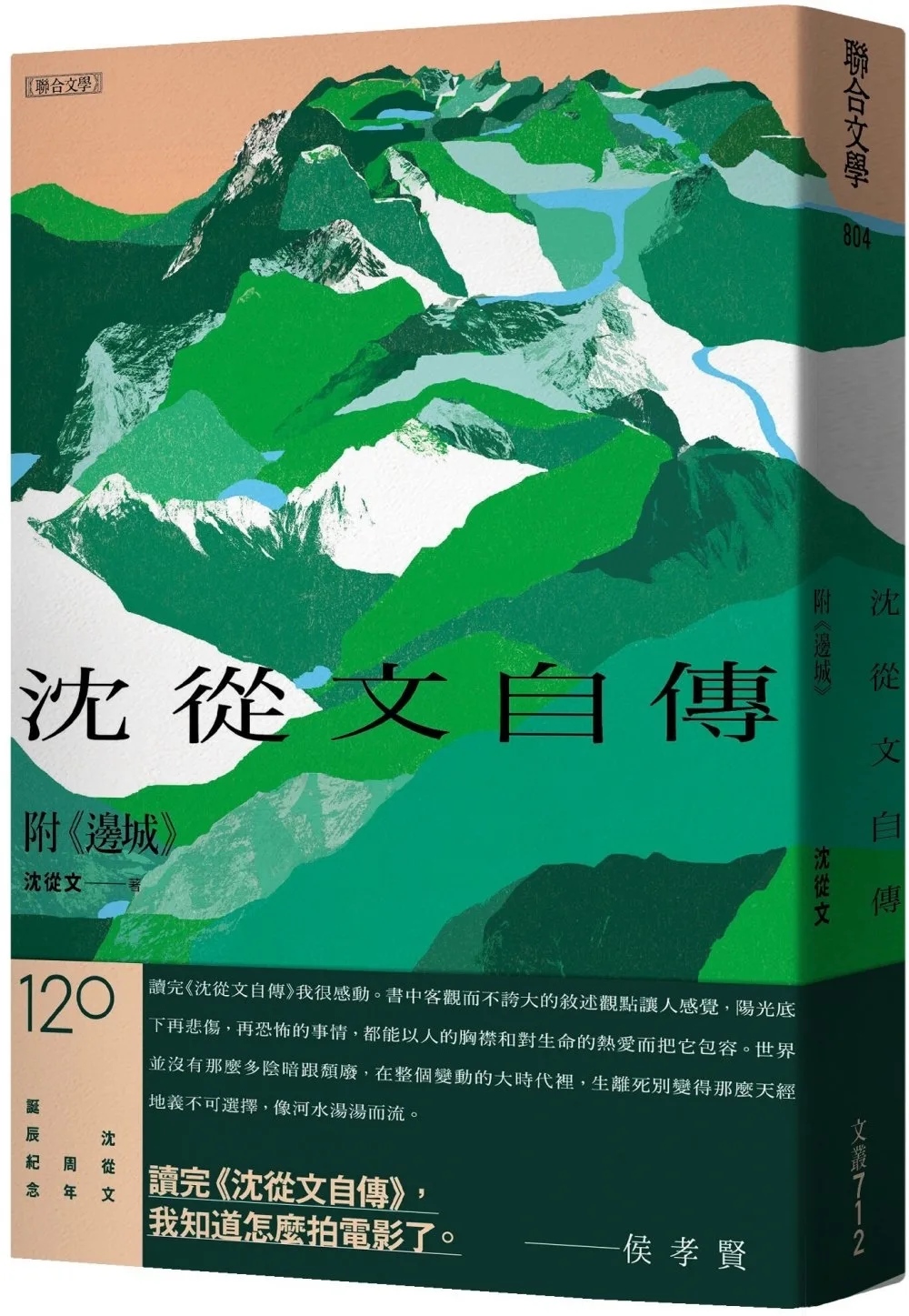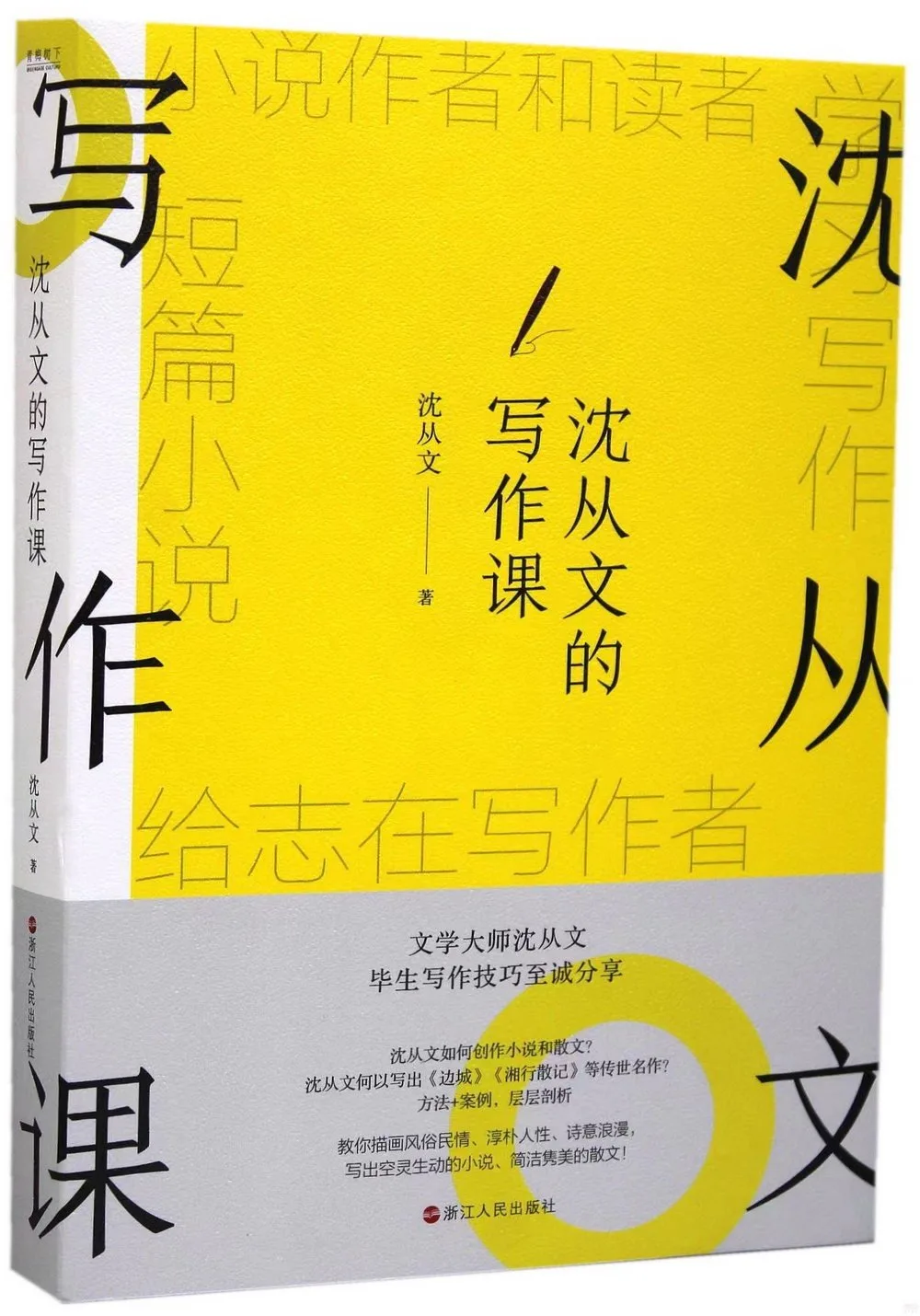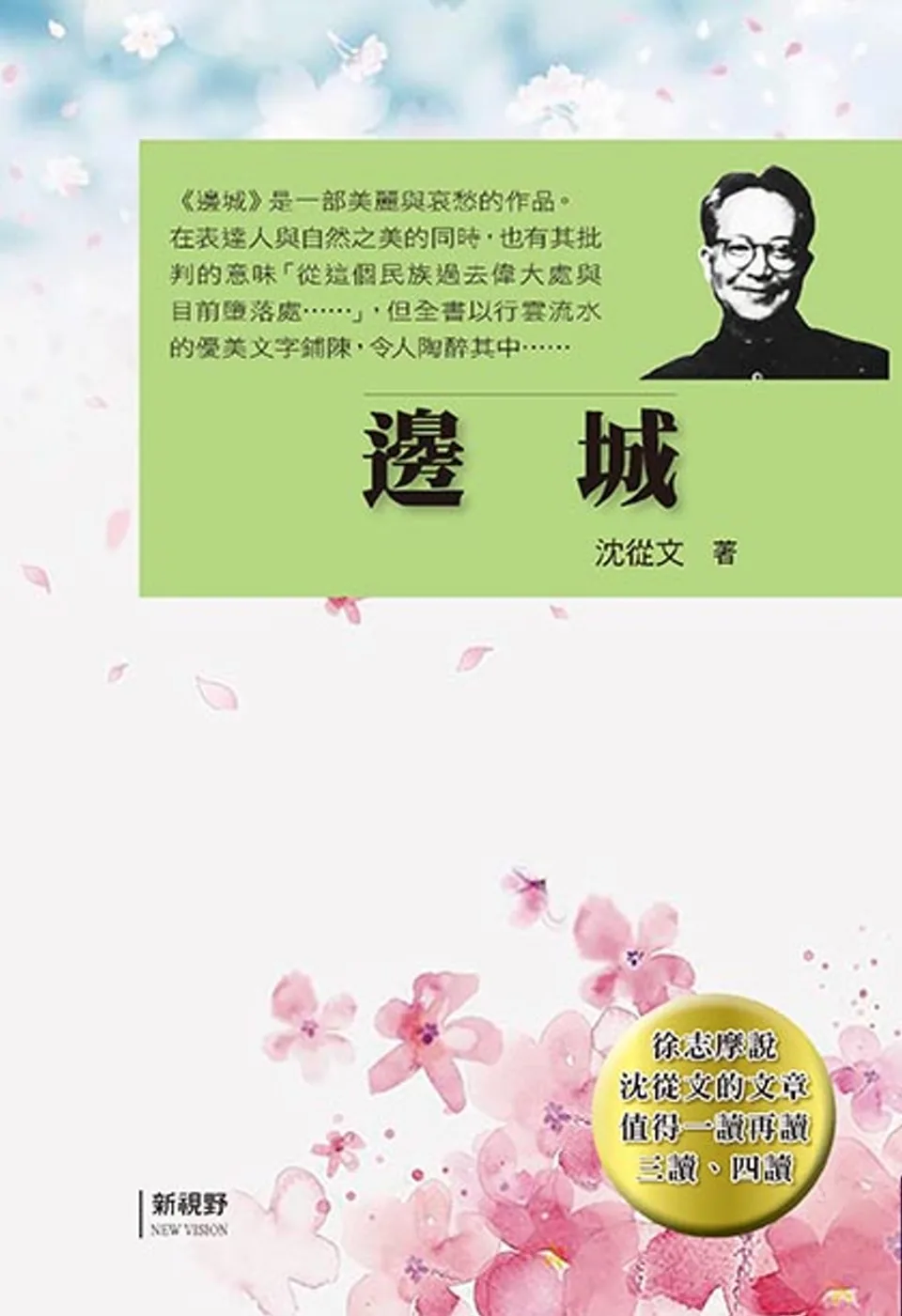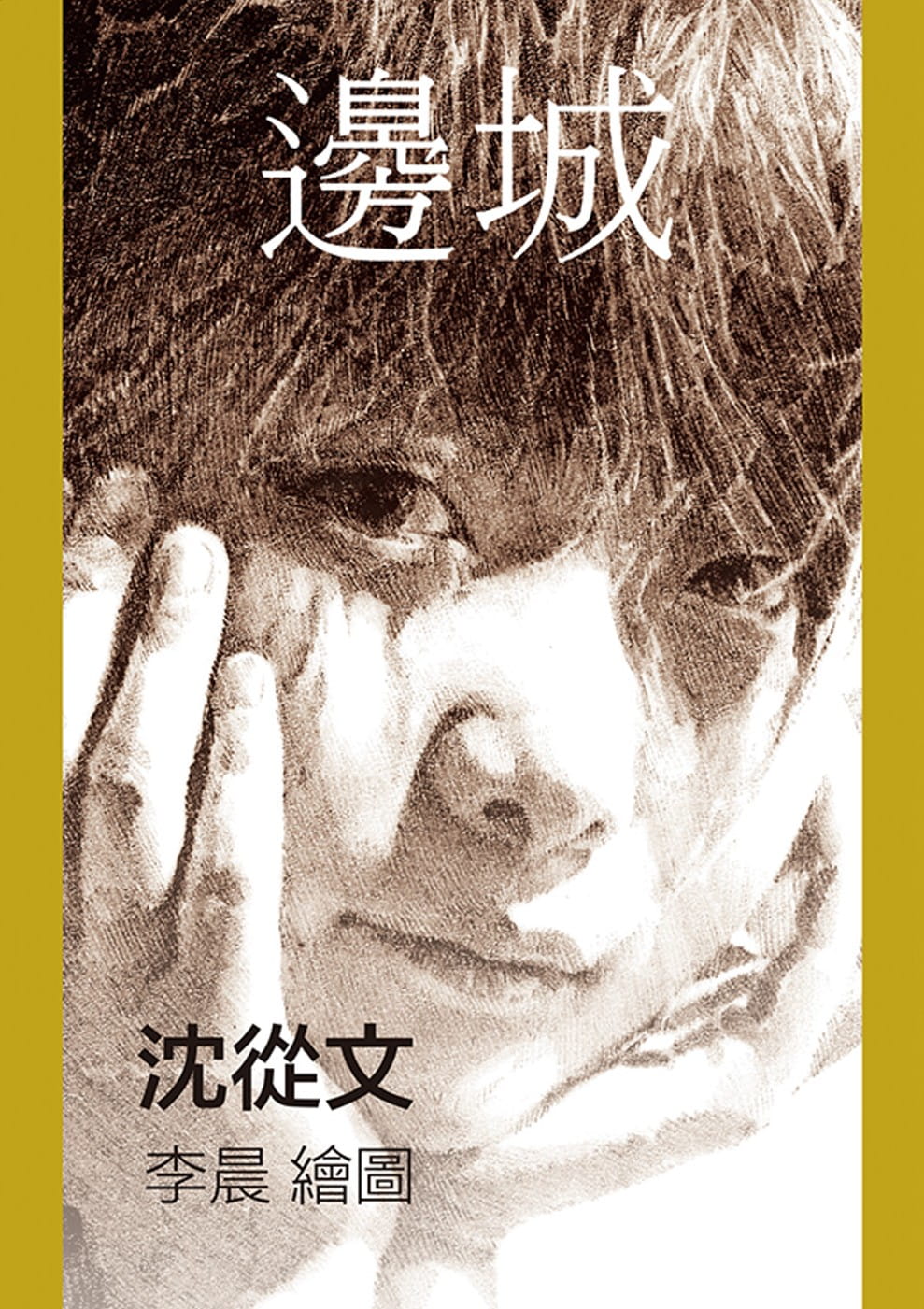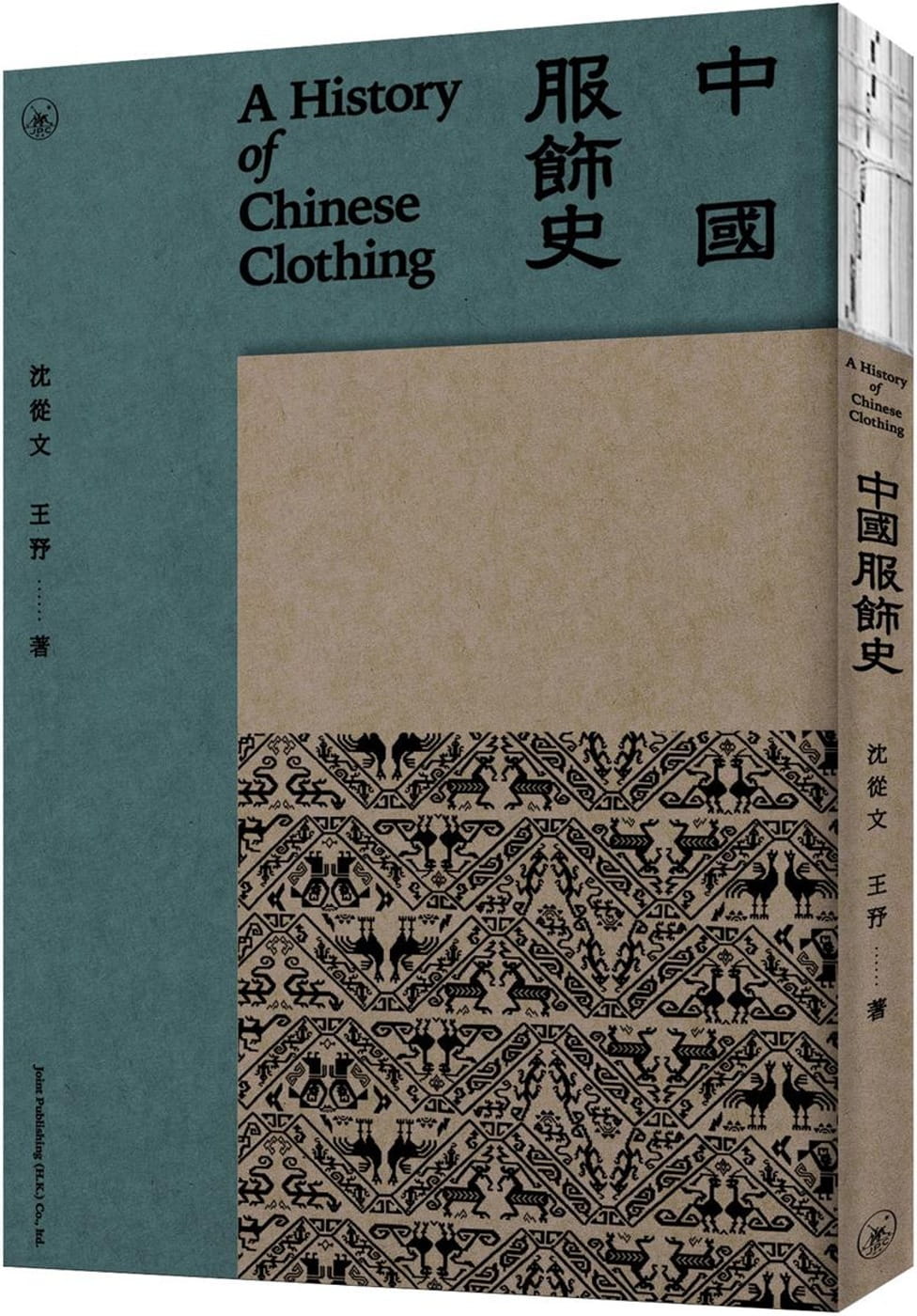題記
沈從文
對於農人與兵士,懷了不可言說的溫愛,這點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隨處皆可以看出。我從不隱諱這點感情。我生長於作品中所寫到的那類小鄉城,我的祖父、父親,以及兄弟全列身軍籍;死去的莫不皆在職務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將在職務上終其一生。就我所接觸的世界一面,來敘述他們的愛憎與哀樂,即或這枝筆如何笨拙,或尚不至於離題太遠。因為他們是正直的、誠實的,生活有些方面極其偉大,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極其美麗,有些方面又極其瑣碎,──我動手寫他們時,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實實的寫下去。但因此一來,這作品或者便不免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
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於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前者表示「不落伍」,告給人中國不需要這類作品,後者「太擔心落伍」,目前也不願意讀這類作品。這自然是真事。「落伍」是什麼?一個有點理性的人,也許就永遠無法明白,但多數人誰不害怕「落伍」?我有句話想說:「我這本書不是為這種多數人而寫的。」念了三五本關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問題的洋裝書籍,或同時還念過一大堆古典與近代世界名作的人,他們生活的經驗,卻常常不許可他們在「博學」之外,還知道一點點中國事情。因此這個作品即或與某種文學理論相符合,批評家便加以各種讚美,這種批評其實仍然不免成為作者的侮辱。他們既並不想明白這個民族真正的愛憎與哀樂,便無法說明這個作品的得失,──這本書不是為他們而寫的。關於文藝愛好者呢,他們或是大學生,或是中學生,分布於國內人口較密的都市中,常常很誠實天真的,把一部分極可寶貴的時間,來閱讀國內新近出版的文學書籍。他們為一些理論家、批評家、聰明出版家,以及習慣於說謊造謠的文壇消息家,同力協作造成一種習氣所控制,所支配,他們的生活,同時又實在與這個作品所提到的世界相去太遠了。──他們不需要這種作品,這本書也就並不希望得到他們。理論家有各國出版物中的文學理論可以參證,不愁無話可說,批評家有他們欠了點兒小恩小怨的作家與作品,夠他們去毀譽一世。大多數的讀者,不問趣味如何,信仰如何,皆有作品可讀;正因為關心讀者大眾,不是便有許多人,據說為讀者大眾,永遠如陀螺在那裡轉變嗎?這本書的出版,即或並不為領導多數的理論家與批評家所棄,被領導的多數讀者又並不完全放棄它,但本書作者,卻早已存心把這個「多數」放棄了。
我這本書只預備給一些「本身已離開了學校,或始終就無從接近學校,還認識些中國文字,置身於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說謊造謠消息所達不到的那種職務上,在那個社會裡生活,而且極關心全國民族在空間與時間下所有的好處與壞處」的人去看。他們真知道農村是什麼,他們必也願意從這本書上同時還知道點世界一小角隅的農村與軍人。我所寫到的世界,即或在他們全然是一個陌生的世界,然而他們的寬容,他們向本書去求取安慰與知識的熱忱,卻一定使他們能夠把這本書很從容讀下去的。我並不即此而止,還預備給他們一種對照的機會,將在另外一個作品裡,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原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成了一個什麼樣子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徵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於營養不足所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我的讀者應是有理性,而這點理性便基於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各在那裡很寂寞的從事與民族復興大業的人。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
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