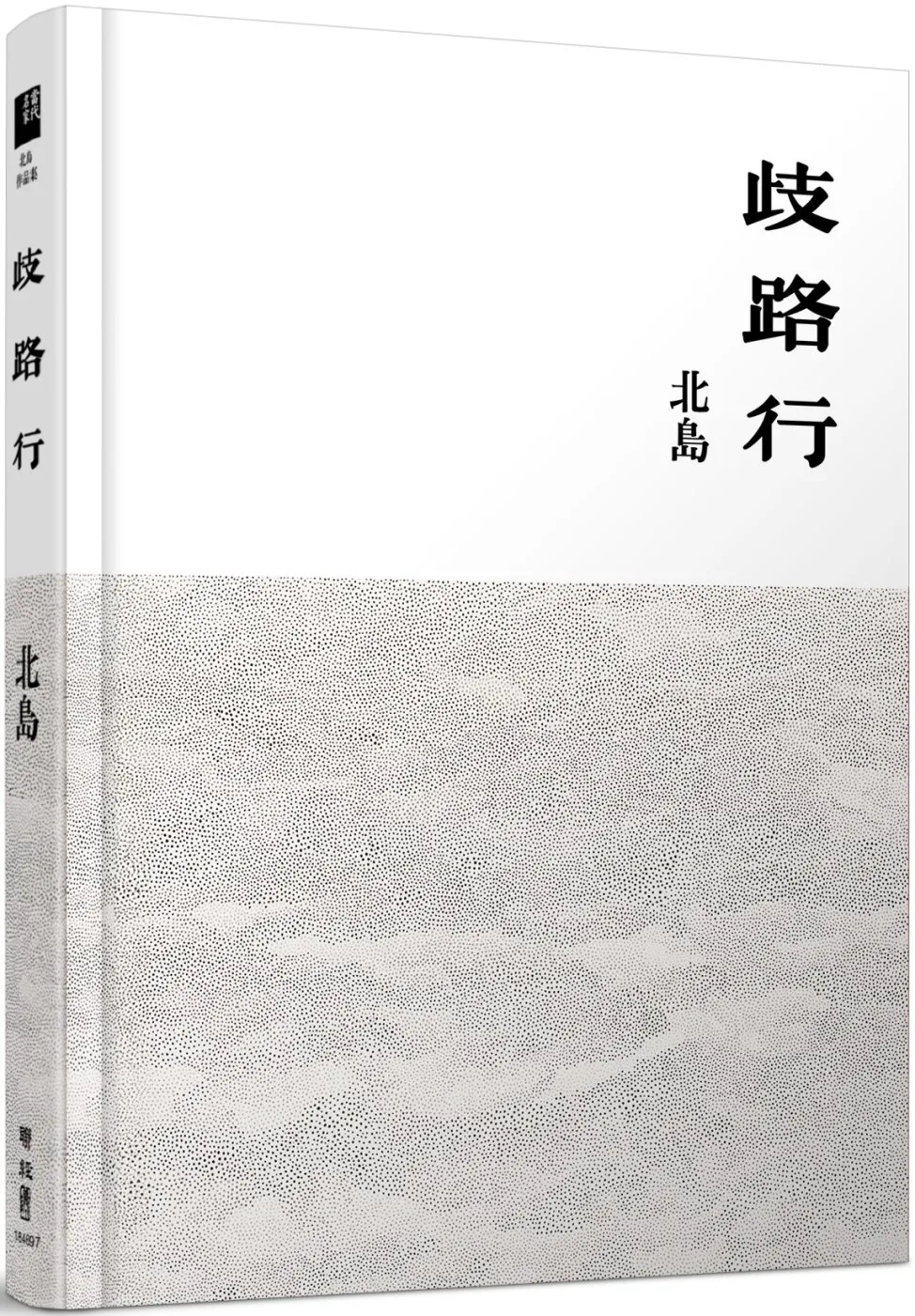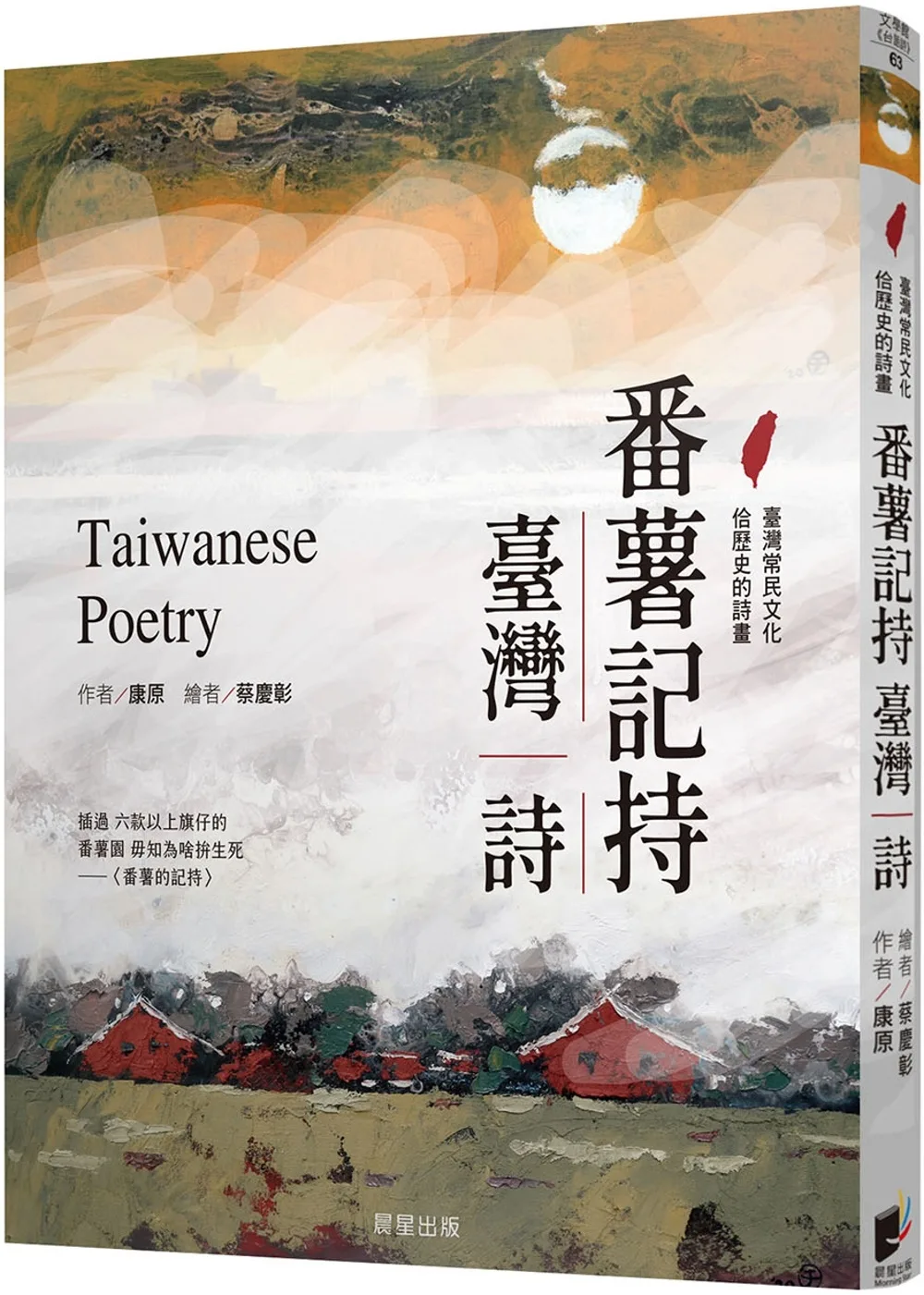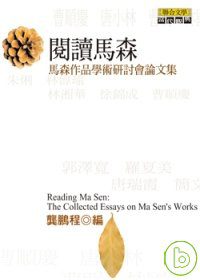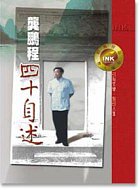我喜歡詩,也喜說詩、喜作詩。偶塗鴉,輒欣然,以為能自道其情。是不是真寫得好,或寫出能不能得到別人的讚美,實在無從計較。因為除了少數幾首抄給同懷諸友看看外,這些東西大概寫完就扔進什物堆裡去了。久而久之,便亦散佚不知去向。
稽延到今年春間,簡錦松詩稿已印出,前言並談及我要刊行詩集事,說他那篇前言就算是彼此共同的詩集序罷。文中娓娓敘少年習詩論學事,把我的記憶又拉回淡水和日月潭的水雲深處。因念年華可紀,流光可傷,昔時歌哭吟哦之陳跡、墨痕凌亂之詩篇,仍是生命中仍不可磨滅的。故若把詩集印出來,當成是一種心情的記錄,也沒什麼不好。待藝不佳,亦正好趁機求教於並世方家大雅,反而別有收獲,亦未可知。
詩稿終於付印,禍災棗梨,其原委如此。補誌卷末,用旌吾過,並借此謝謝教我學詩的師友。
此中凡收詩二○三首。少年學詩之概況,另詳我(用情)一篇,此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