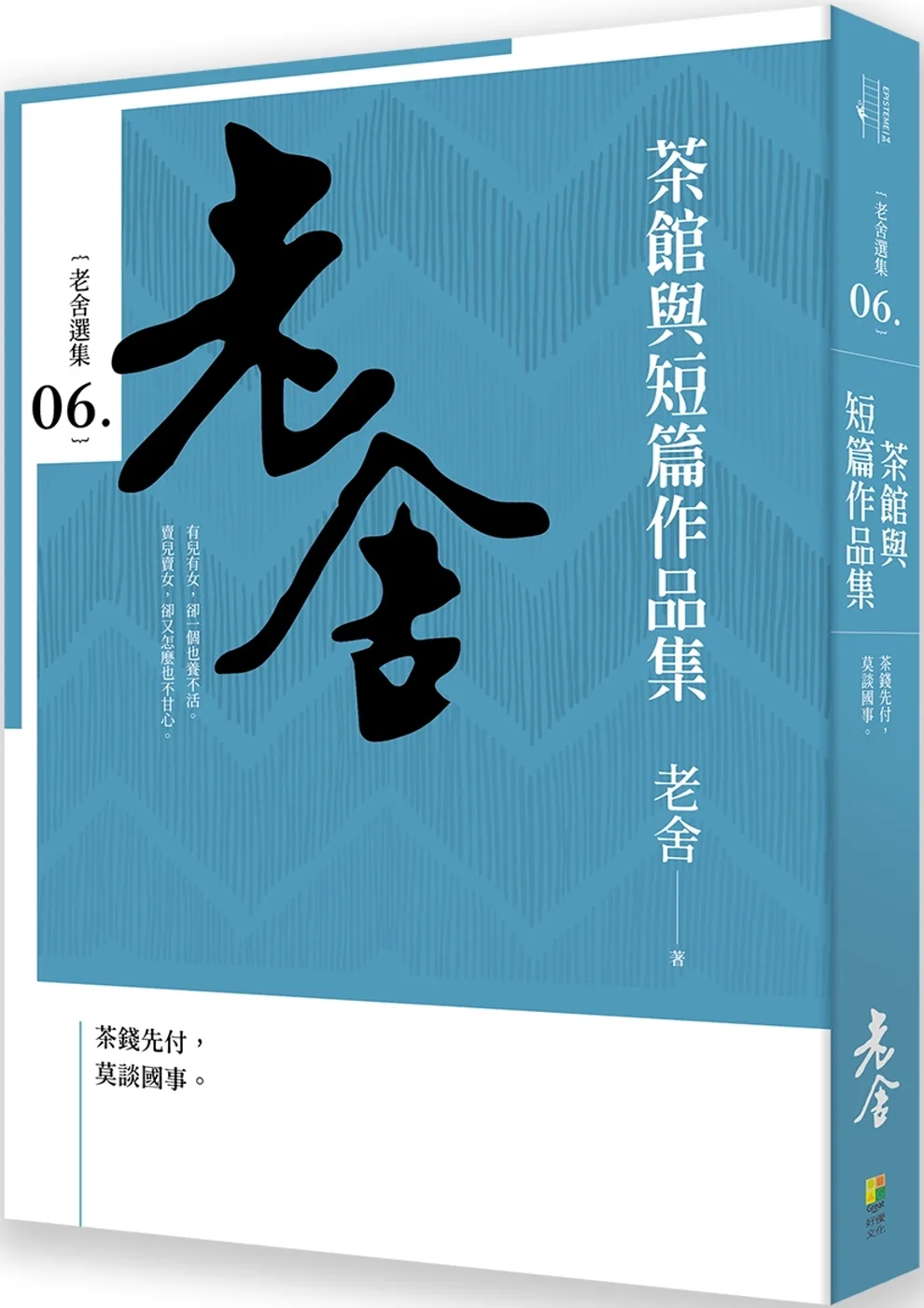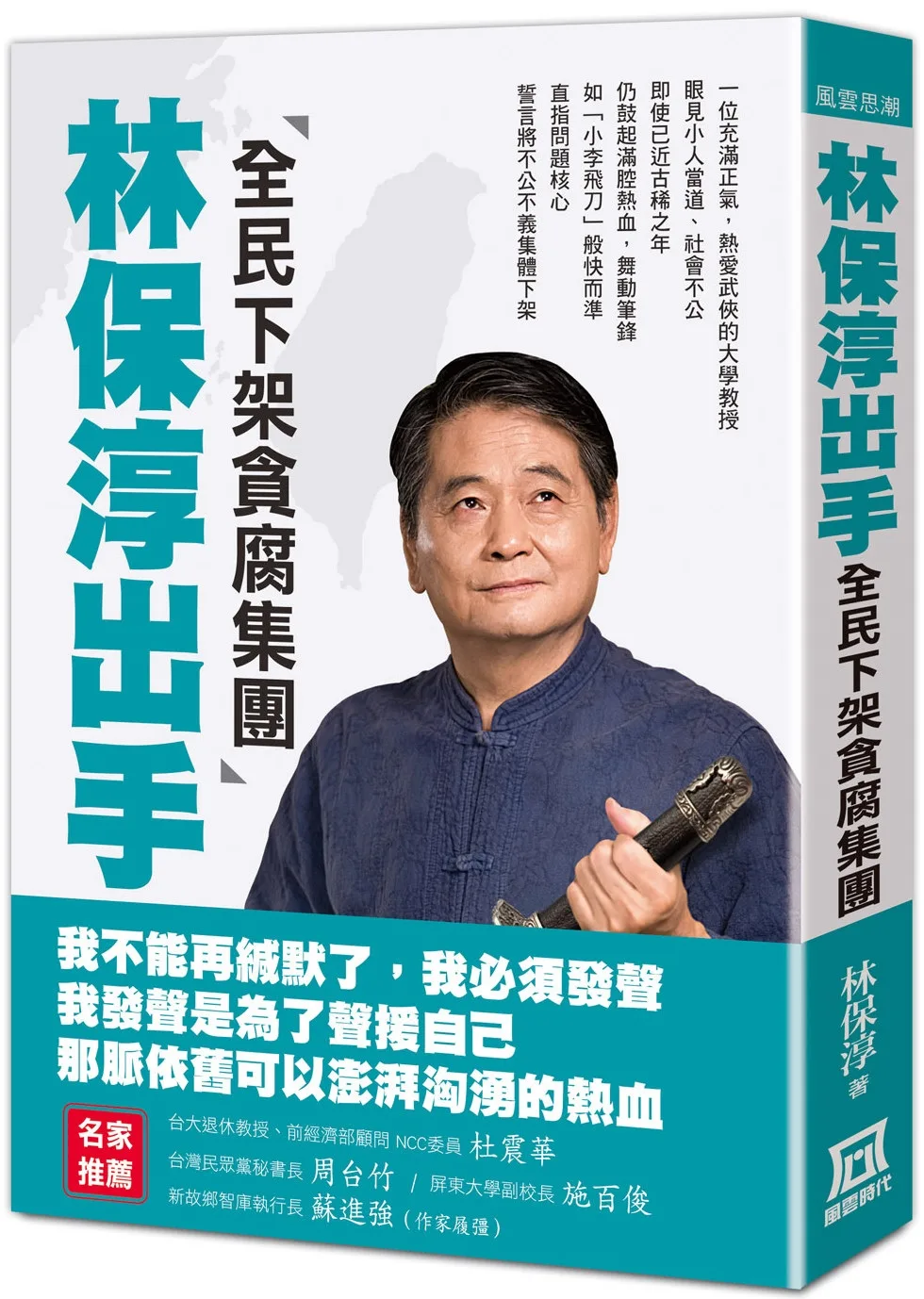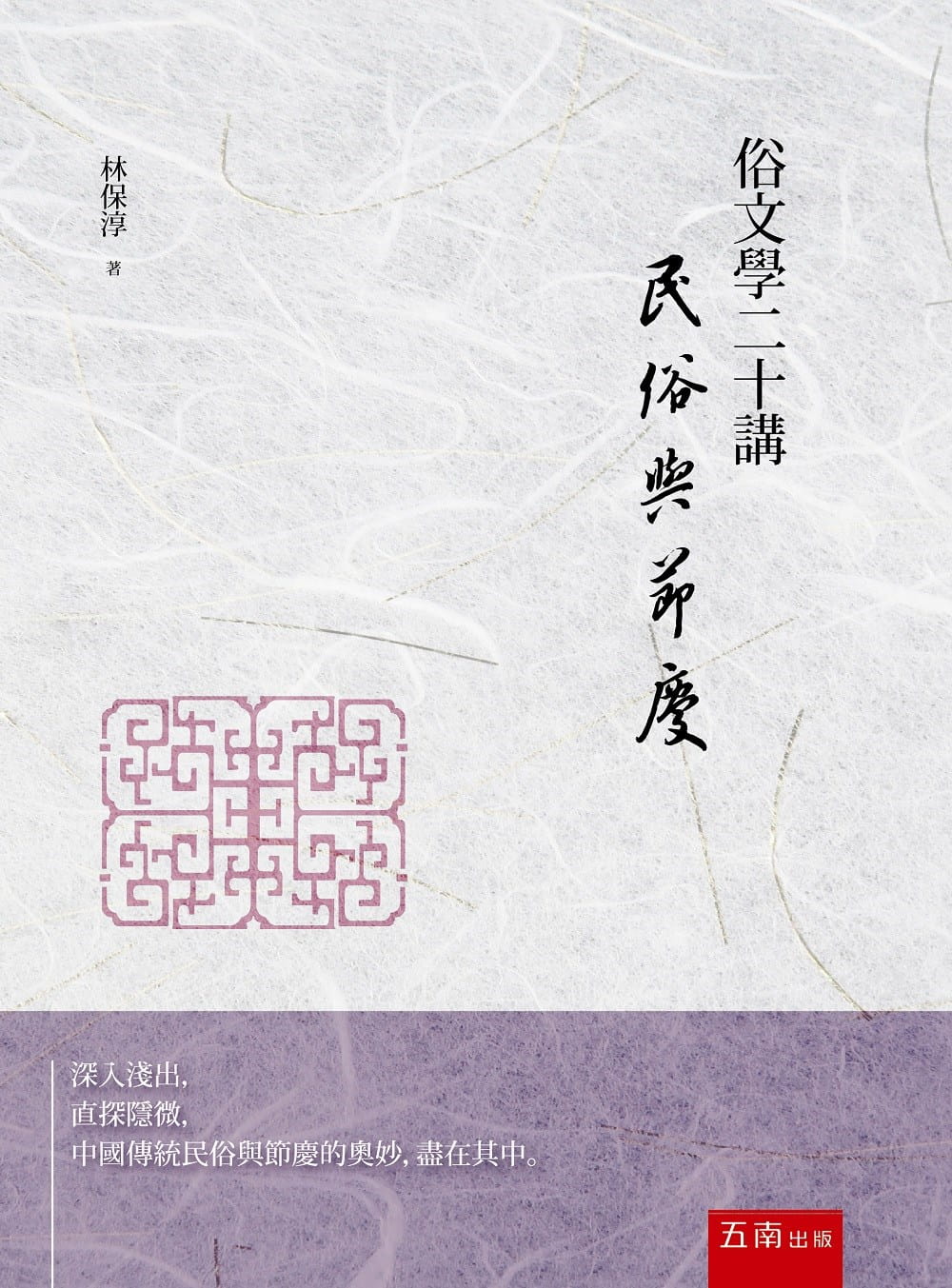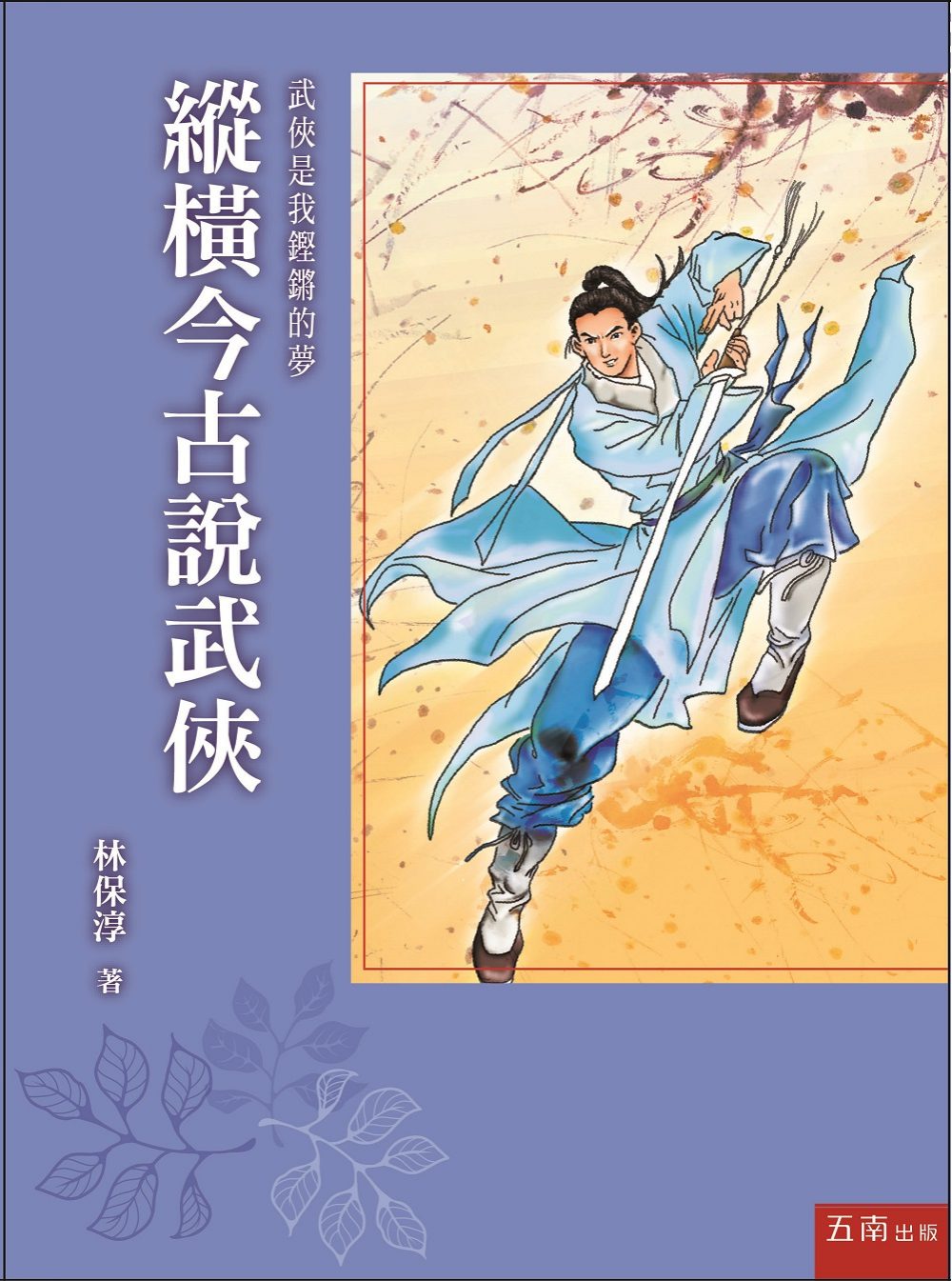自序
我是懷著「作家夢」進讀中文系的,也幾度黽勉不懈,大作過這個不切實際的夢。刊登過幾篇詩文,獲得過幾個小獎,但卻深知,才分不足,終是難以圓成的,最後只能遁逃於學術,作了文藝界的逃兵。儘管偶爾仍會提筆操觚,藉詩文略抒胸臆,卻早已慧劍青鋒,揮別了「作家」這頂桂冠。
作家於我何有哉?那像是高懸於天際,閃閃爍爍,卻攀摘不得的星子,只能憑空臆想而已。不過,在嘗試築夢、追夢的過程中,卻還是別有收穫的。學究這條路,最忌諱的就是文字詰屈聱牙,讓人難以卒睹,我幸而能夠不誤蹈此一禁區,文從字順而意暢,未嘗不是受惠於這個階段的磨礪。這時候,我不得不感謝,在我仍然深陷於「作文」的埳阱中,難以自拔的時候,是當初「神州詩社」的儕友,以對文藝的滿腔熱忱,極盡其鼓勵、刺激、指正之能事的開啟了我的竅門,讓我了解到什麼才是「文章」。金針度人,沉?能起,這應是何等的功德?
當然,針砭那一剎那,不但有痛楚,而且也有開示,我也知道,自己是距離「作家」這兩字越來越遠了。撤下黃昏時詩人懸掛的那盞燈,我在故紙堆中、武俠情裡,在我的江湖世界,另燃起一根燭。我不知道這根蠟燭能有多少光度,但至少也照亮了我生命中的一隅。劍氣書香,未能兼得,簫聲劍影,舞著舞著,卻也是酣暢而淋漓。我不能作趕赴長安在雁塔題詩的士子,卻作了埋首燭下爬梳經典的學究,一失就有一得,人生就是如是的奇妙。
但這個夢卻還是清晰分明的。當學究已老,絳帳寂寥的時候,案頭經卷,卻不知為何突然間若有似無起來。句讀古文,擬想古今俠者,而書帙層疊、寶劍生塵,卻也自知江湖已不是我這鏽劍老馬可以叱吒的所在了。當年往事,不經意間,就毫末畢現地浮映出來。少女情懷是詩,中年心事如酒,老年心境,則是一個緊接一個的如煙舊夢。
我想起童年時的歡樂,想起青少年時的困頓,想起當年舊友,想起陳年故事,我是潯陽江頭船中的琵琶,聲聲奏起如歌的行板,「夜深忽夢少年事」,那正是我曾經一步一腳印,難以忘記的行跡。既是難忘,就不妨記下,所以我寫,所以我記,終始如環,我又回到了從前作夢的情境。
我的過去的日子,常自覺是突梯而又滑稽的,荒唐的事做過不少,正經的事反倒不多。我以今日的老眼,看我昨日的花心,自評自批,倒也頗有點評經籍的快意。我一路走過,最感念的,既是當年的自己,更是當年與我共玩樂、共教學、共砥礪、共歌哭的師長、友伴、情人,有笑有淚,有欣喜,有悵惘,有記念,迤迤邐邐,我寫,我記,這也是我迤迤邐醴的一生的側寫。
知我者,相信不會是我的學術成果;罪我者,更不應當會是這本小冊子。其實,不管是要罪我、知我,我都是這樣「曾經」走過了,事非經過不知難,「曾經」才是最重要的。
早年有夢,晚年還會有嗎?經過了一段歲月的洗滌沖刷,舊夢是依舊,還是會煥然而一新?我不知道,也無心探究。但是,非常感謝九歌出版社,很多很多年前,九歌所出的《閃亮的生命》,是我所寫文章首度被印成紙本的,今朝首次集結,又回到九歌,對我是深具意義的。總編陳素芳,是我大學同班同學,也是神州舊友,蒙她不棄,此書才有面世的機會。
我商請了舊友蔡詩萍、李宗舜為本書寫序。蔡詩萍是我竹中與台大學弟,在新聞、藝文界早已聲名卓著,由他領銜,料能沾光不少;李宗舜就是黃昏時天空中的那顆星星,是我入神州的啟蒙者之一,名聞遐邇的大馬詩人,他以詩代序,寫了百行,更讓我這本小冊子多了幾分別開生面的意趣。在此是要致上深厚的謝意的。
《夜深忽夢少年事》,夜深了,夢醒未?突然想起譚詠麟所唱的〈半夢半醒之間〉,又想到《莊子》裡「夢蝶」的故事,其實,世事一場大夢,舊夢、新夢、真夢、非夢,都無所謂,最重要的是,我還有夢。
?
歲在辛丑,仲秋,林保淳序於木柵說劍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