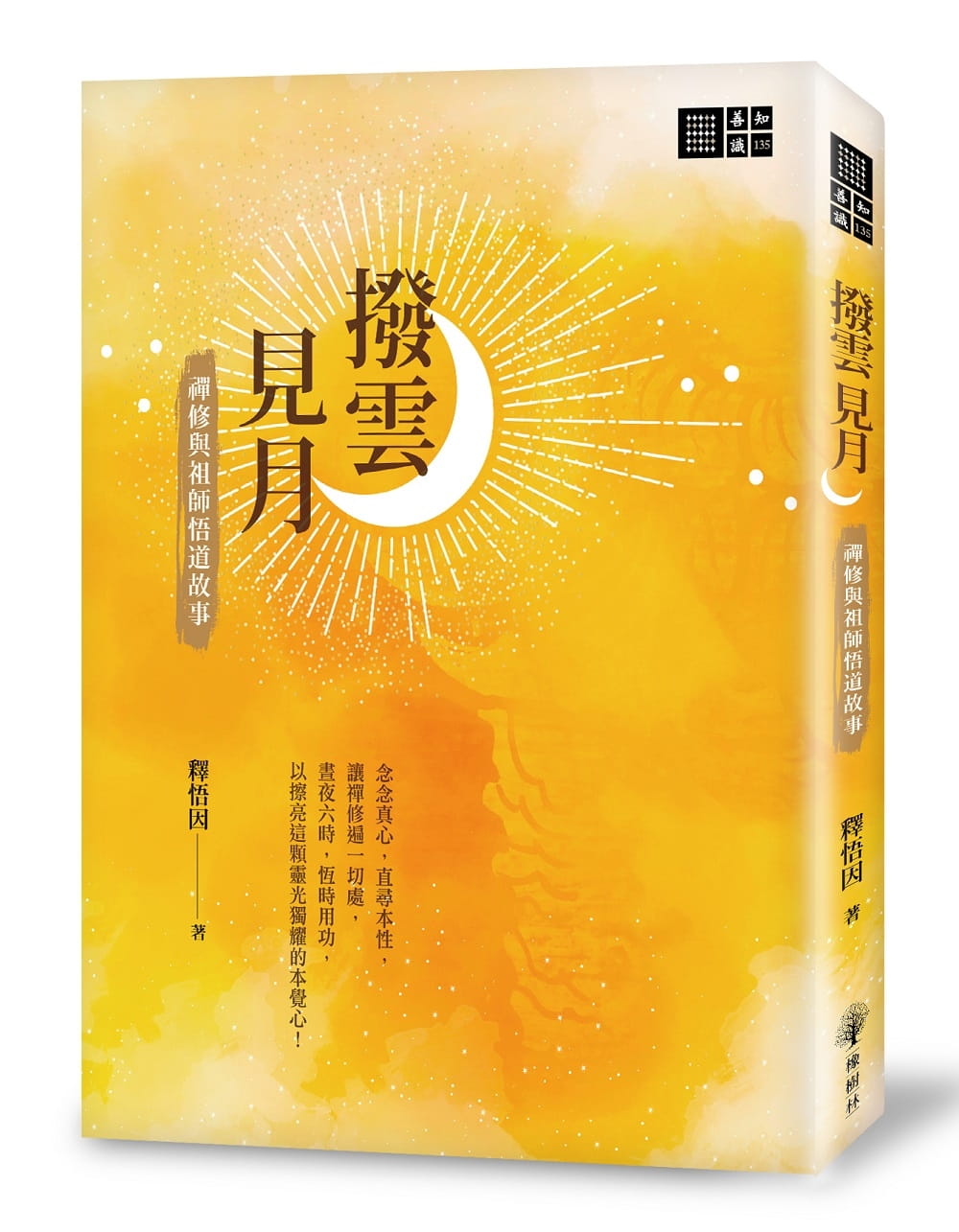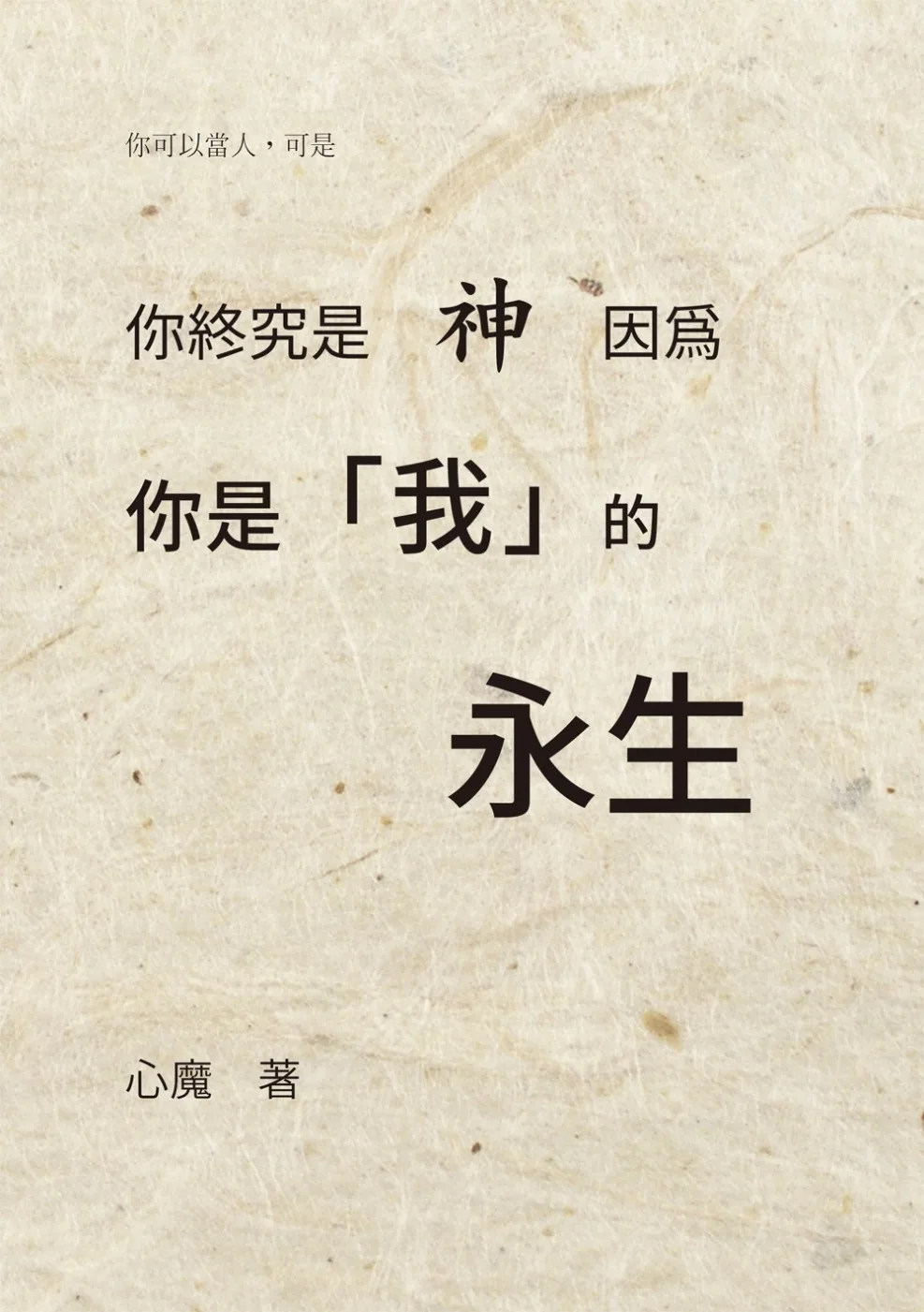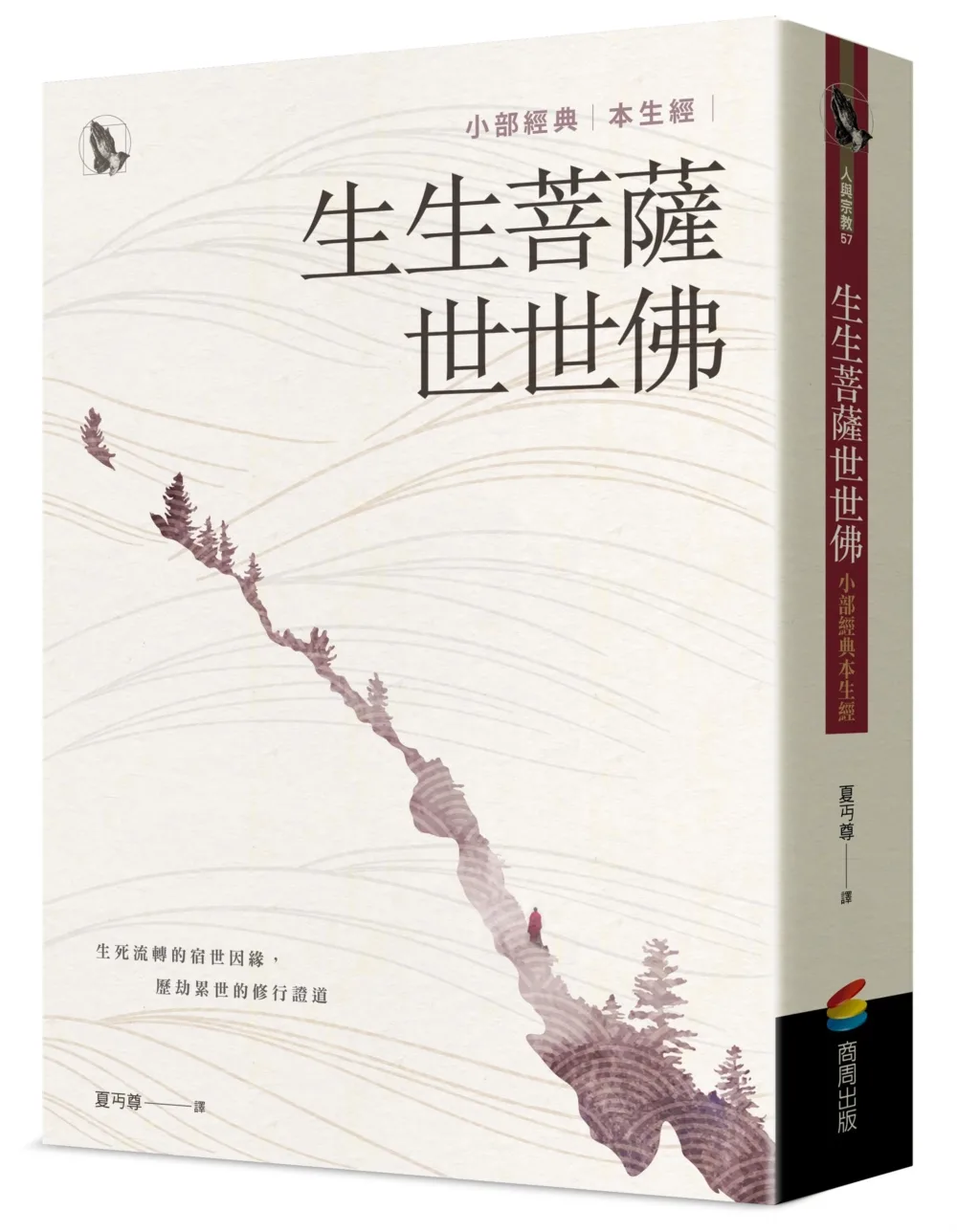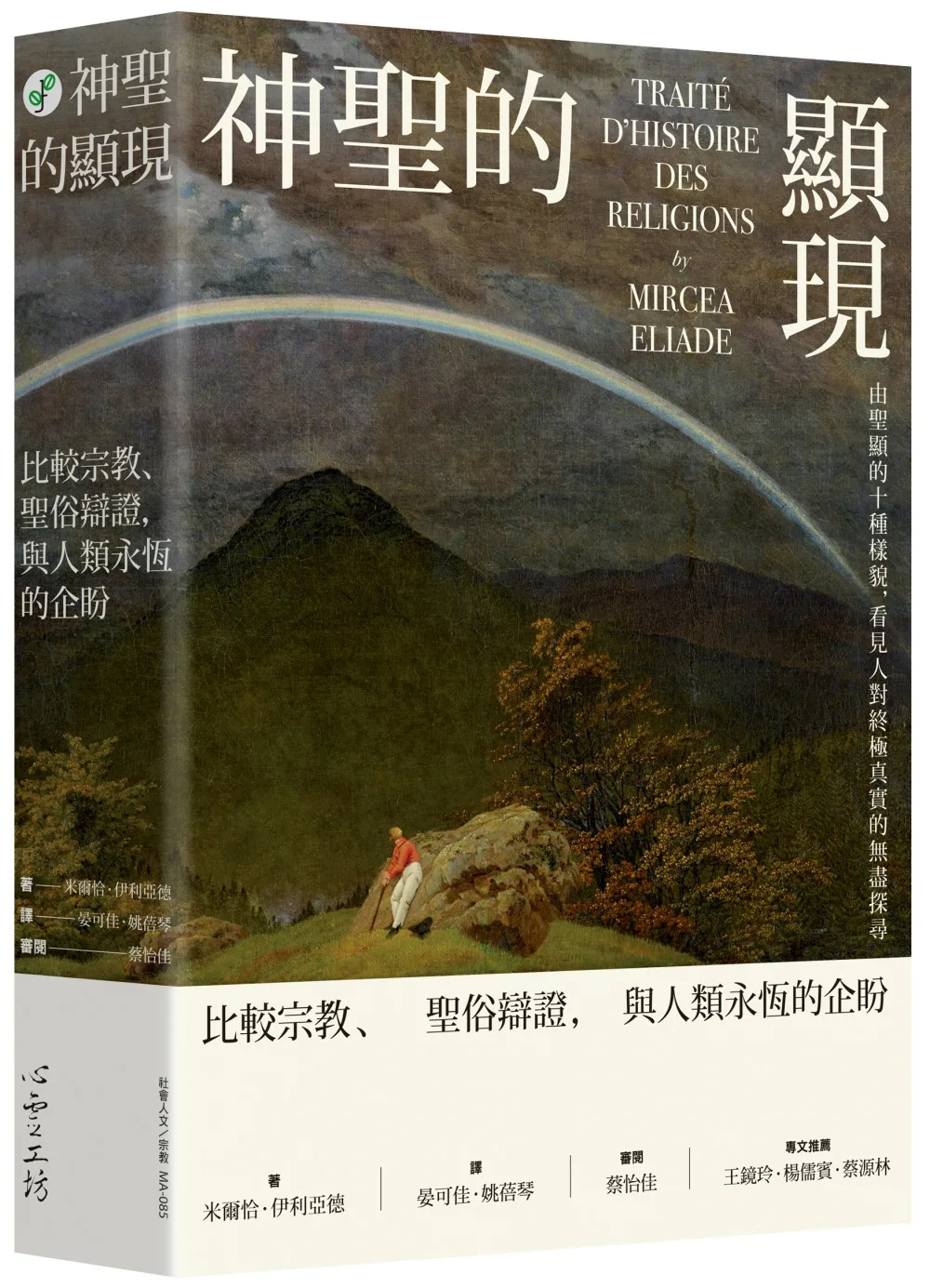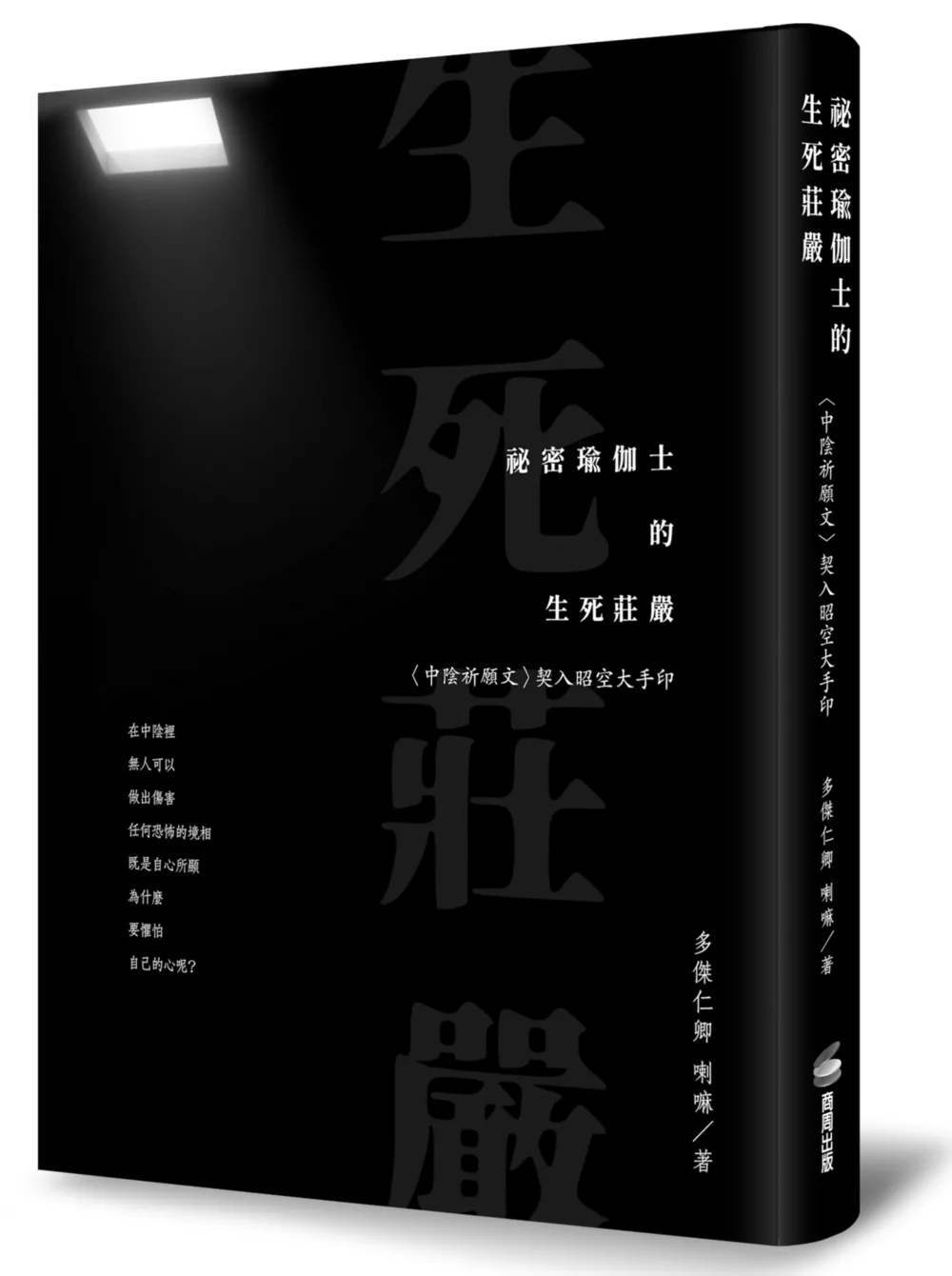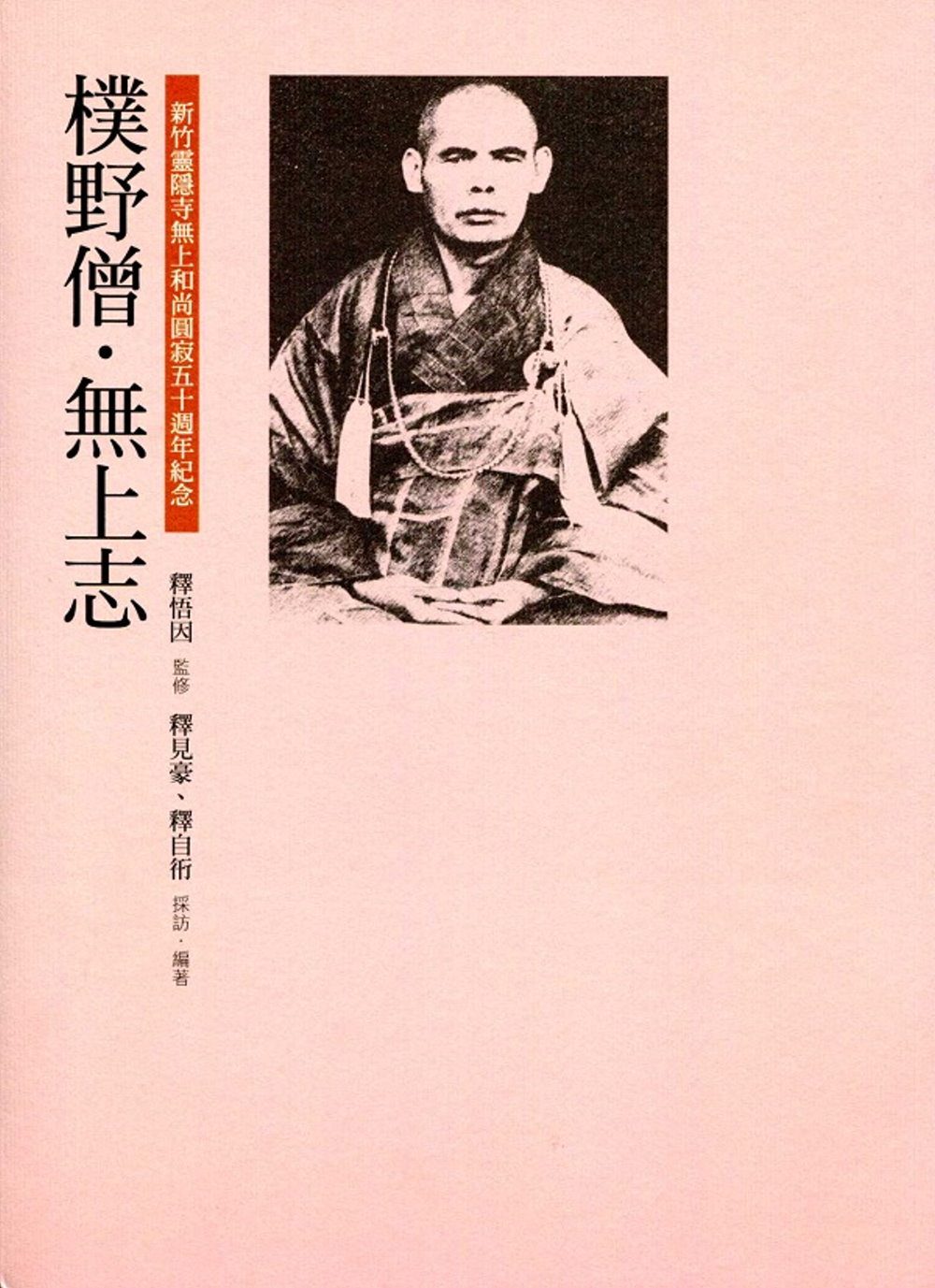撥雲見月,「見月」一詞還得從「指月」講起,這是出自《楞嚴經》中,佛陀告訴阿難的一段話:「汝等尚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非得法性。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所標指為明月故。豈唯亡指,亦復不識明之與暗。」佛陀運用各種教學方法引導學人,為的是要讓行者悟入第一義諦;淨除諸多障礙,直到見證到自己本來面目的那一刻,即是撥雲見月的一刻。
禪修靜坐是佛陀的教學方法之一。禪坐可遠溯至西元前五世紀前後的印度,當時印度許多宗教,如婆羅門教、耆那教,都以靜坐冥想作為修持方法。不同於其他宗教,佛教更強調智慧的重要,亦即禪修是為了理解緣起、苦、無常、無我等基本教義而達至解脫,也就是佛教「戒、定、慧」三學,乃至「八正道」所揭示的修學階次與要義。
四念住是佛教根本修行方法,從身、受、心、法四個面向,建立持續及穩固的覺知。一般會從盤腿專注於呼吸(又稱安般)開始,進而專注於身、受、心、法四種對象,觀察其起落相續狀態,進一步體驗到緣起實相。也由於佛教將打坐到進入三昧過程中的心理活動,細緻地分為「止」、「觀」等階段,因此,也產生了四禪八定等禪定階段與成果的系統。禪修的範疇和意義不斷擴大,後世部派或宗派也就開發了各自不同的禪修技巧,像是數息、內觀、慈心觀、四界分?觀、念佛觀、參話頭、默照等。
針對禪修的方法以及詮釋的宗派中,最具特色的就是菩提達摩傳來中國的禪宗。達摩祖師約莫於中國劉宋時期(420-478)從海道來到中國,之後傳法慧可,再到被推尊為六祖的曹溪惠能(713卒)、百丈懷海(814卒),之後至唐武宗會昌法難(845)前後,這四百年間,印度禪法逐漸適應中國文化而成為興盛、獨樹一幟的「中國禪」,是中印文化融合的禪,不僅帶動中國哲學、藝術的發展;唐代時期建立的漢字文化圈如日、韓、越等區,也深受其影響;至近代,「禪」(Zen)也與世界思潮呼應,在歐美地區有其新的演繹與運用。
禪,本來就不限於達摩所傳,只要重於內心持行,為修道主要內容的,就是禪。但是,禪宗影響力這麼深遠,達摩祖師對修行的看法到底是什麼?是必須要認識。
《菩提達磨大師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觀》裡提到:「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不出二種:一是理入,二是行入。」趣入菩提道,不外乎有兩條修行徑路,一是悟理(理入),一是修行(行入)。什麼是「理入」?
「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凡聖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文教,此即與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之理入。」
理入,從理上悟道、入道。是「藉教悟宗」,也就是依「教」去悟入的。藉什麼「教」?「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覆,不能顯了。」要深信一切具有生命、有知覺的有情皆「同一真性」,是具足佛性、法性、覺性——法性即是空性,佛性也是空性,空性當中還具有覺性。要深信人人都有佛性,是同一真性。
人人都有佛性,為什麼不受用?「但為客塵妄想所覆,不能顯了。」這個說明同《楞嚴經》:「皆由客塵煩惱所誤。」煩惱、妄想就是客塵。「客」是客人,打妄想這念心,塵勞境界這念心,就是客。「若也捨妄歸真」,假若能夠捨棄妄想,回歸真性;去除客塵、妄想,就可返本還原,回歸自己的清淨法身。例如,打坐時,起妄想時,不要理它,繼續專注你的所緣,心不動,這就是能作主,就是主人。心能作主,就能返照自心,能夠突破妄想、執著。
我們的心像日、月一樣,時刻都有光明。忽然變暗了,不是因為日、月失去光明,而是被雲霧所遮,只要遮雲撥開,它的光明依舊。此一心性本具光明,現在為什麼沒有?就是被妄想、煩惱所覆蓋,因而不能顯發它的光明。所以,就在無明煩惱當下一心,就真性具足,當下即是,無二無別。
從「凝住壁觀」下手。此時凝心、安心、住心,從依言教的聞而思,到不依言教的思而修,「與真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當下這一心了了分明、寂照不二就是與理相應、相符,此刻沒有分別,一念不生,如同六祖惠能對惠明所說:「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即是明上座本來面目。」這念心一想到善、想到惡,就是分別;不思善不思惡,但是,了了分明,「名之理入」。到這裡就是如智不二的般若現證。
悟了還要行入──發行。「行入者,所謂四行;其餘諸行,悉入此行中。何等為四行?一者報怨行,二者隨緣行,三者無所求行,四者稱法行。」事上就是行,有四種方便的入道行門。「其餘諸行,悉入此中」,所有八萬四千行門都含攝在這四種行門當中。這四行都是從實際的事行進修,前三行強調的是人與人的和諧共存,無論是個人或佛教,在世間行事,要不違世俗,恆順眾生,從克己中去利他。稱法行是「方便」──以「無所得為方便」而行六度。所謂「行菩薩大行而無所行,攝化眾生而不取眾生相」,從利他中銷融自己的妄想習氣。所以,什麼是禪修?像這樣的處世修行,才能真正的自利利他,莊嚴無上菩提。達摩祖師所教授的,如同印順導師註解:「精要簡明,充分顯出了印度大乘法門的真面目。」
這本書輯錄自二○一四年至二○一八年,我在香光尼僧團封山禪修的開示,讀者會一直感受到「理入」與「行入」兩個概念穿插而行。香光尼僧團是以漢傳大乘佛教為本質而開展的比丘尼僧團,在個人理入精進同時,也在團體事相的行入上磨練;不僅留意念念心的妄想清淨,也關注整個佛教界、社會的宗教需求——除了原本的教育文化志業之外,香光尼僧團近年也嘗試一些跨領域、跨學科的弘化,如開設國小兒童心智教學課程;安養院陪伴老人晚緣計劃;與世界藝術大師合作帶動桃園偏鄉國小學生的藝術素養;我也親自領著僧俗二眾至印度、馬來西亞、緬甸、中國、美國等地,與當地佛教團體或宗教文化單位交流合作。但是,不變的行程是封山禪修,每年的十一月份,香光尼僧團所有僧眾此時都要用功,絲毫不耽擱。
最後,還是回到佛陀對阿難開示的場景中,《楞嚴經》之所以啟講,是因為阿難遭遇修行生涯中最大的考驗與挫折。當然,此時的阿難還不知道自己未來將再面臨什麼樣的困難,佛陀只是這麼說:「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當應看月。」你順著我手指的方向,就會看到月亮。如果沒看到月亮呢?希望你讀完這本《撥雲見月》後,能夠生起這樣的信心:月亮一直都在,不過是一片雲彩,揮一揮,帶不走什麼的。
?
悟因
二?一九年九月 序於 香光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