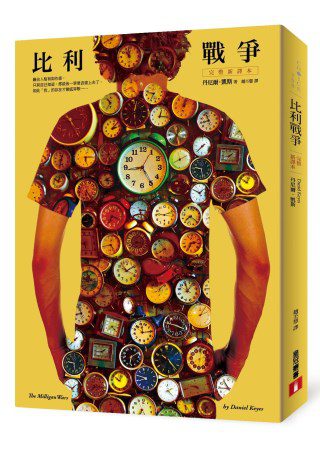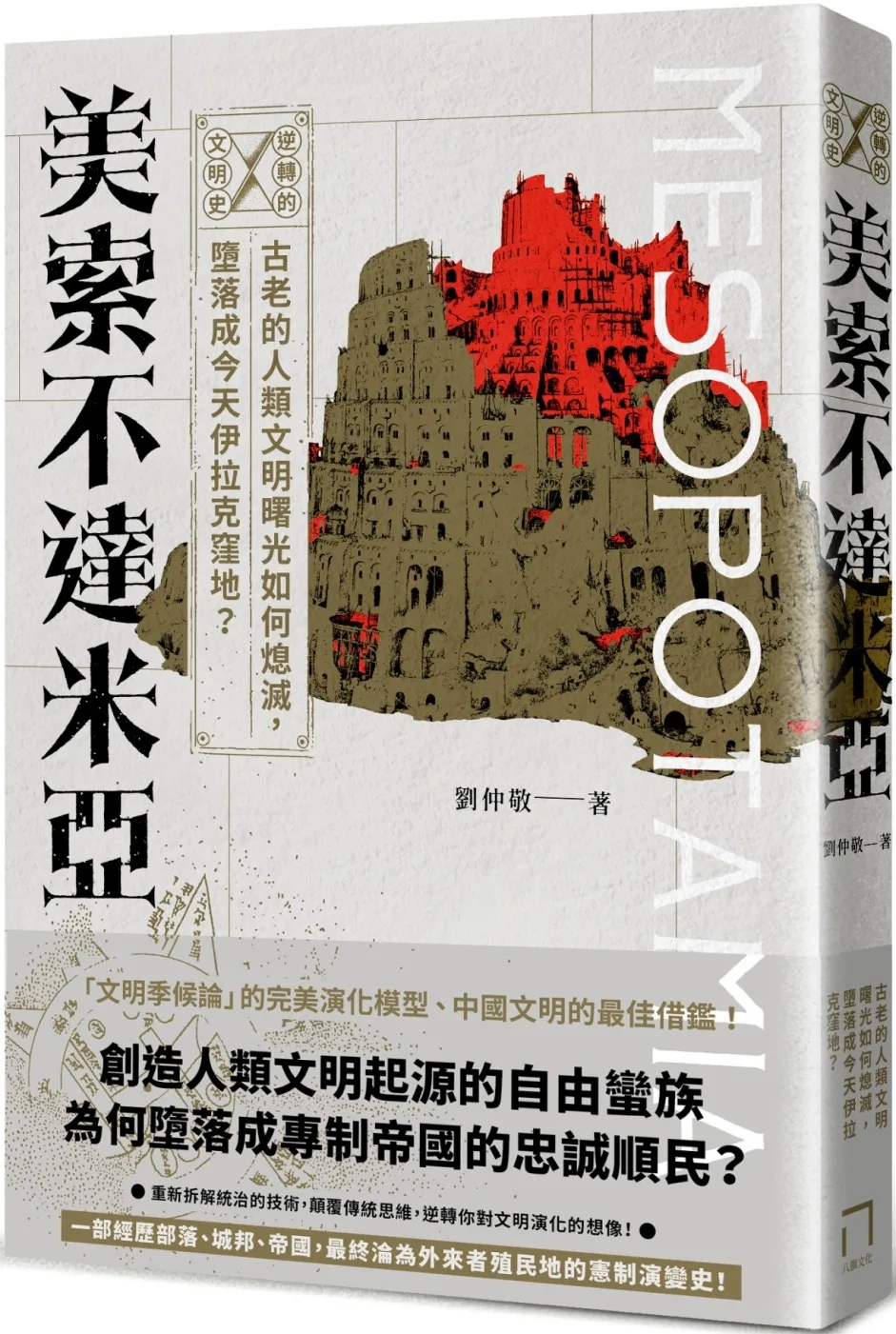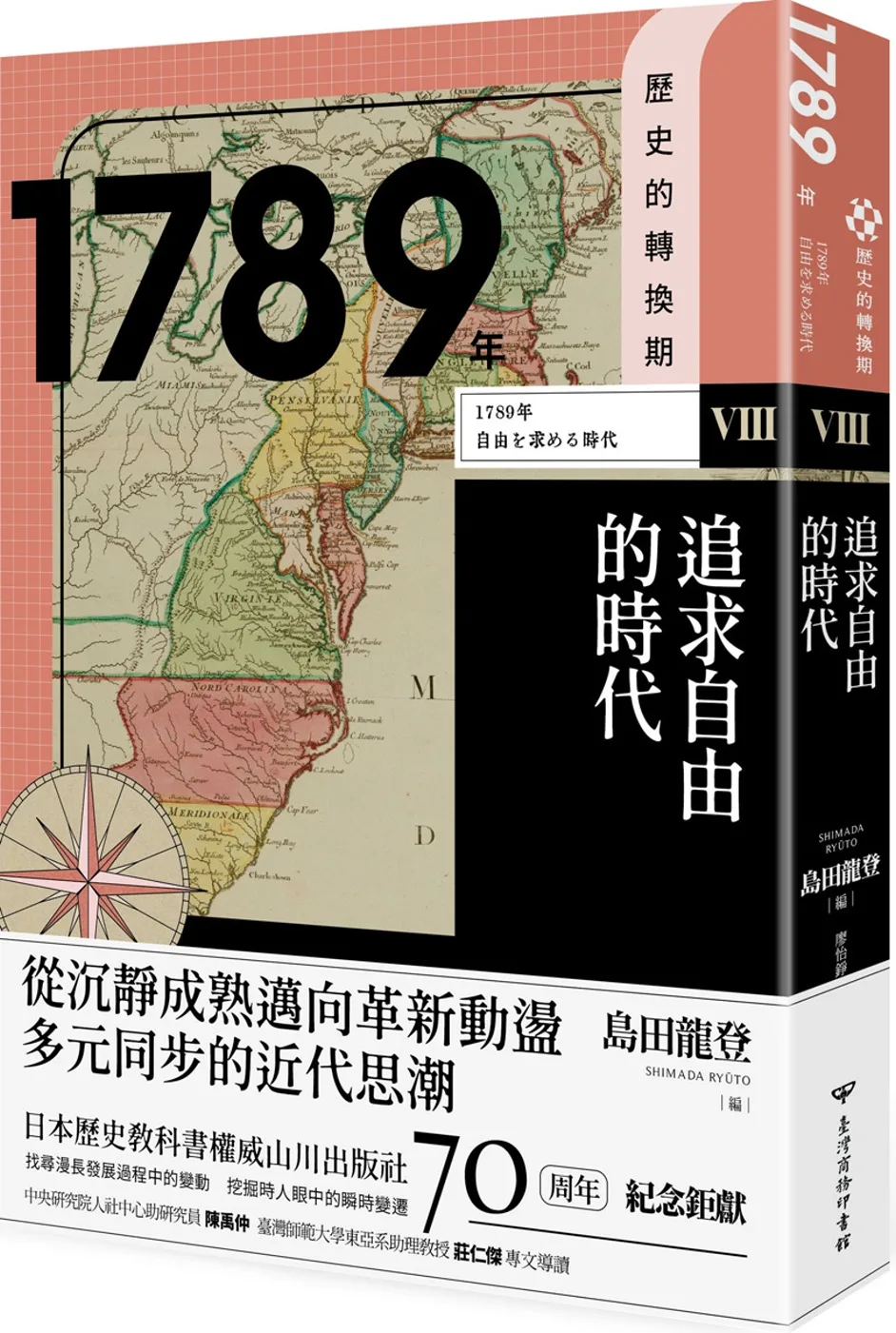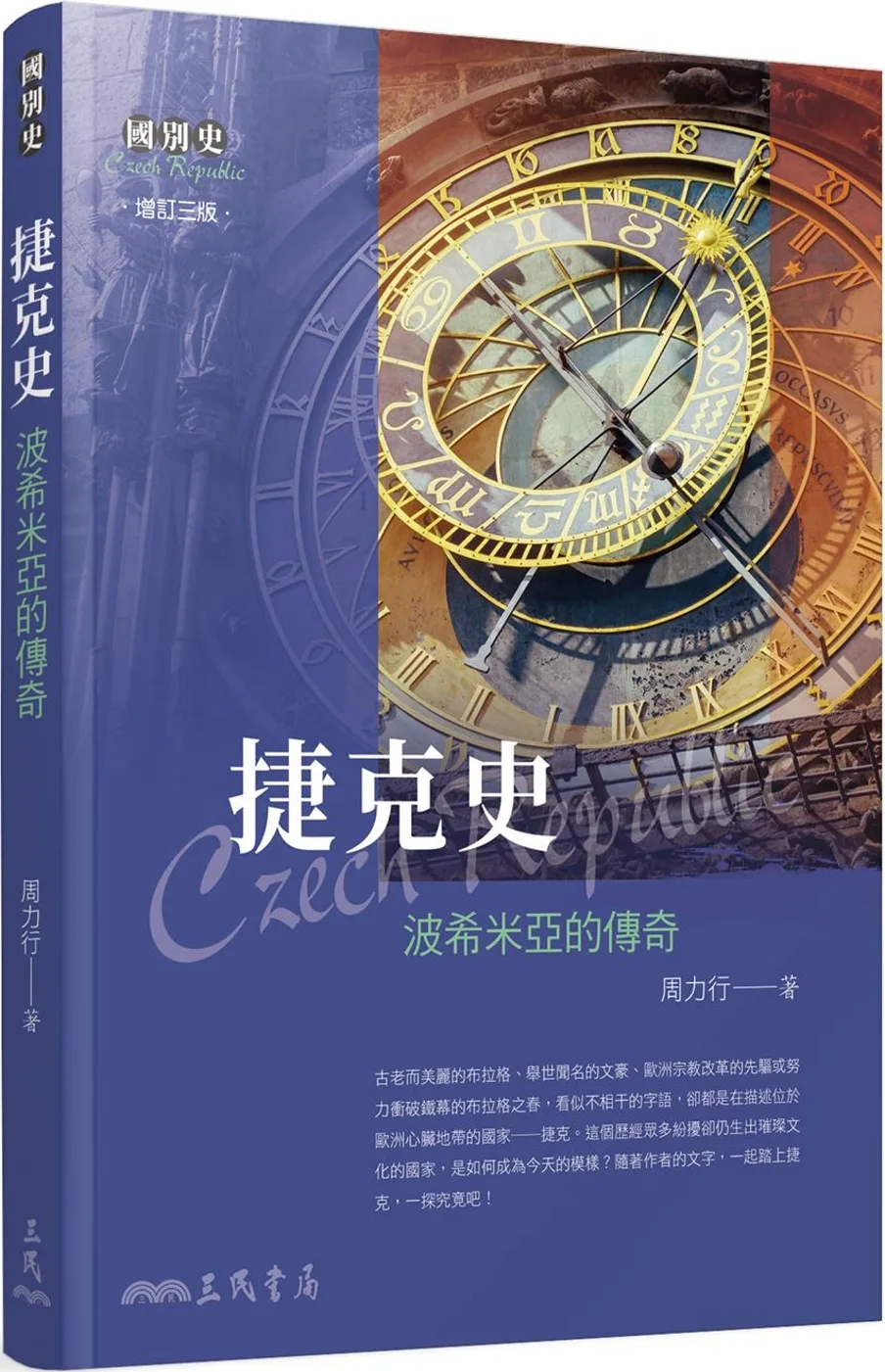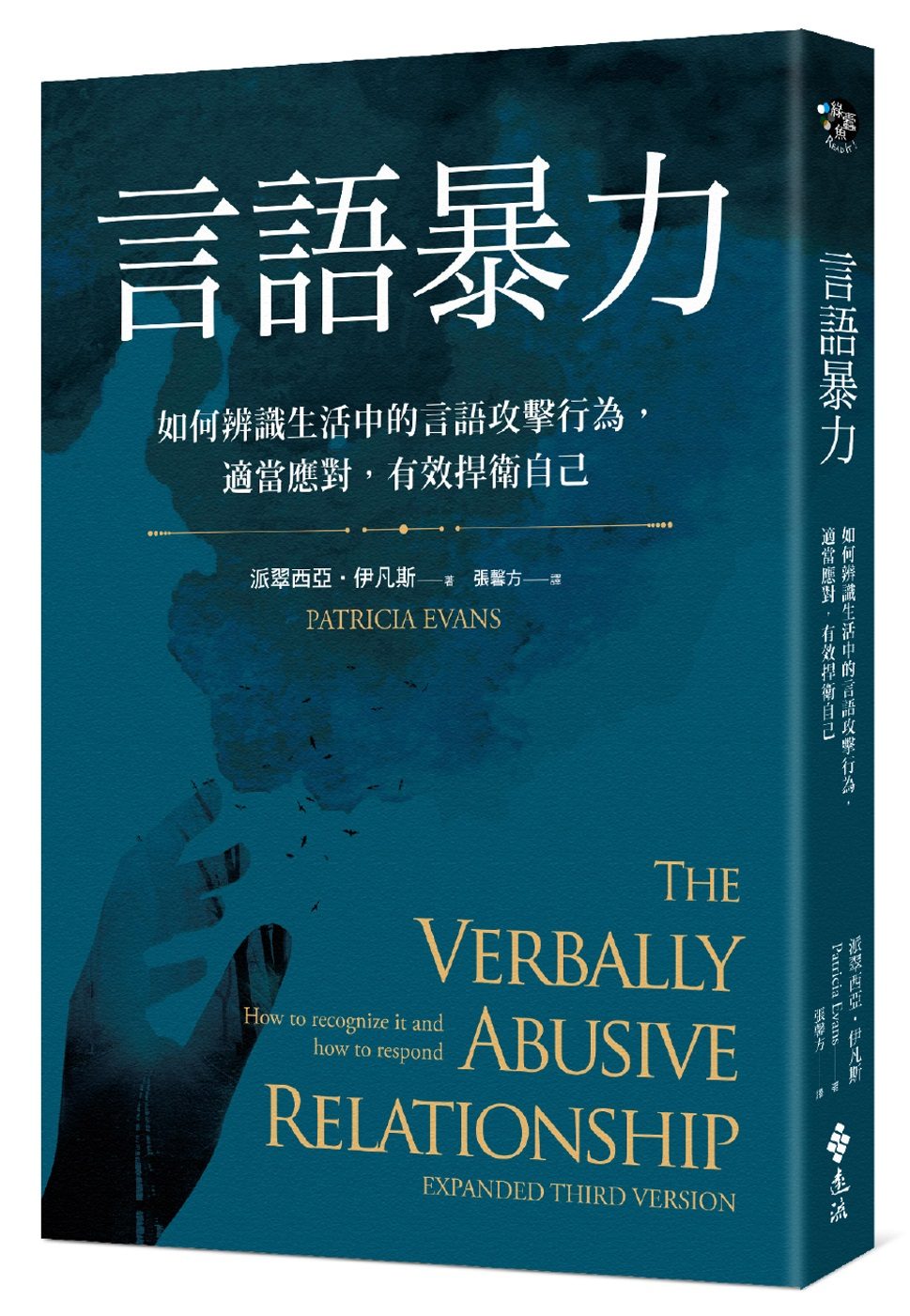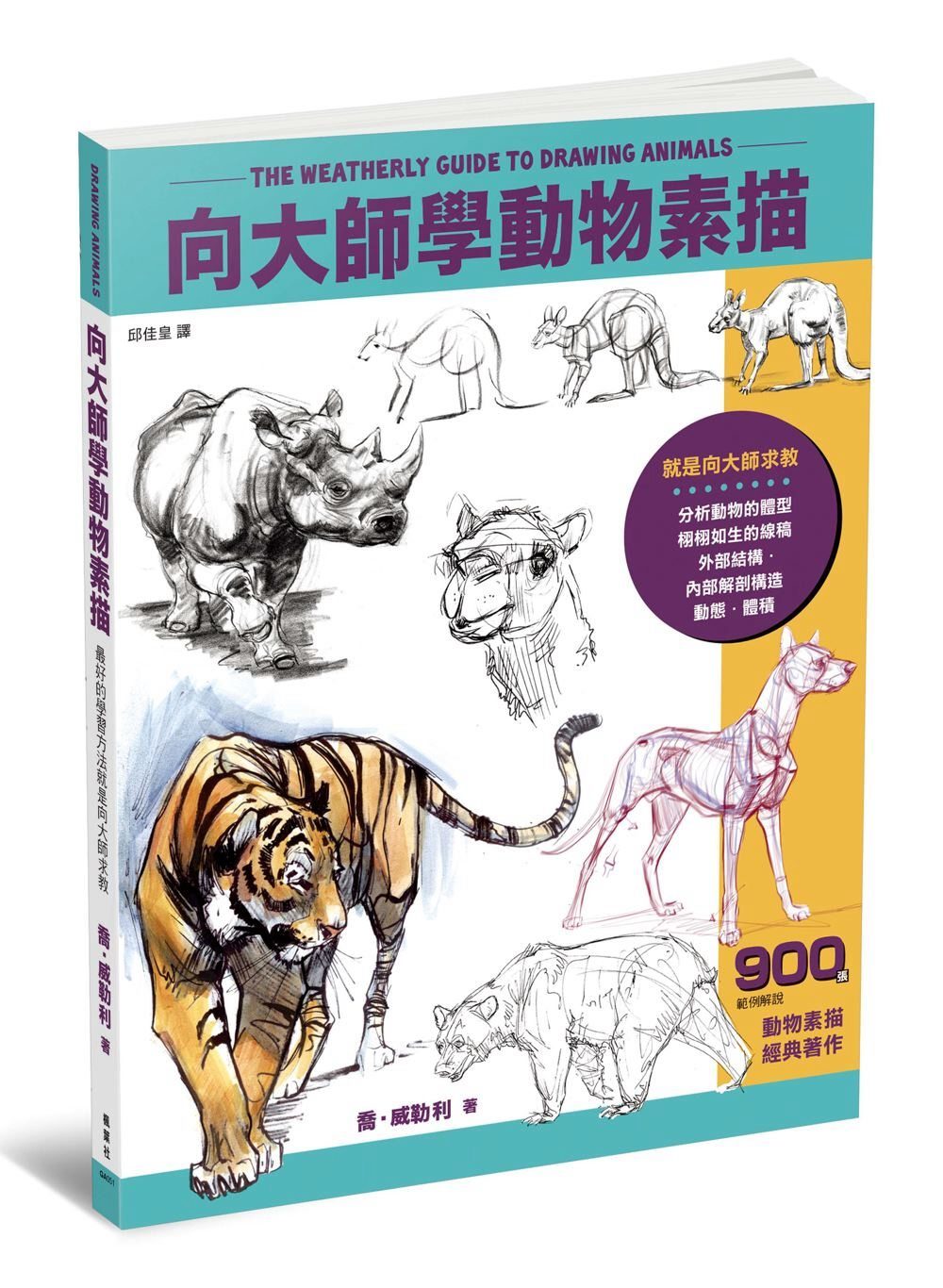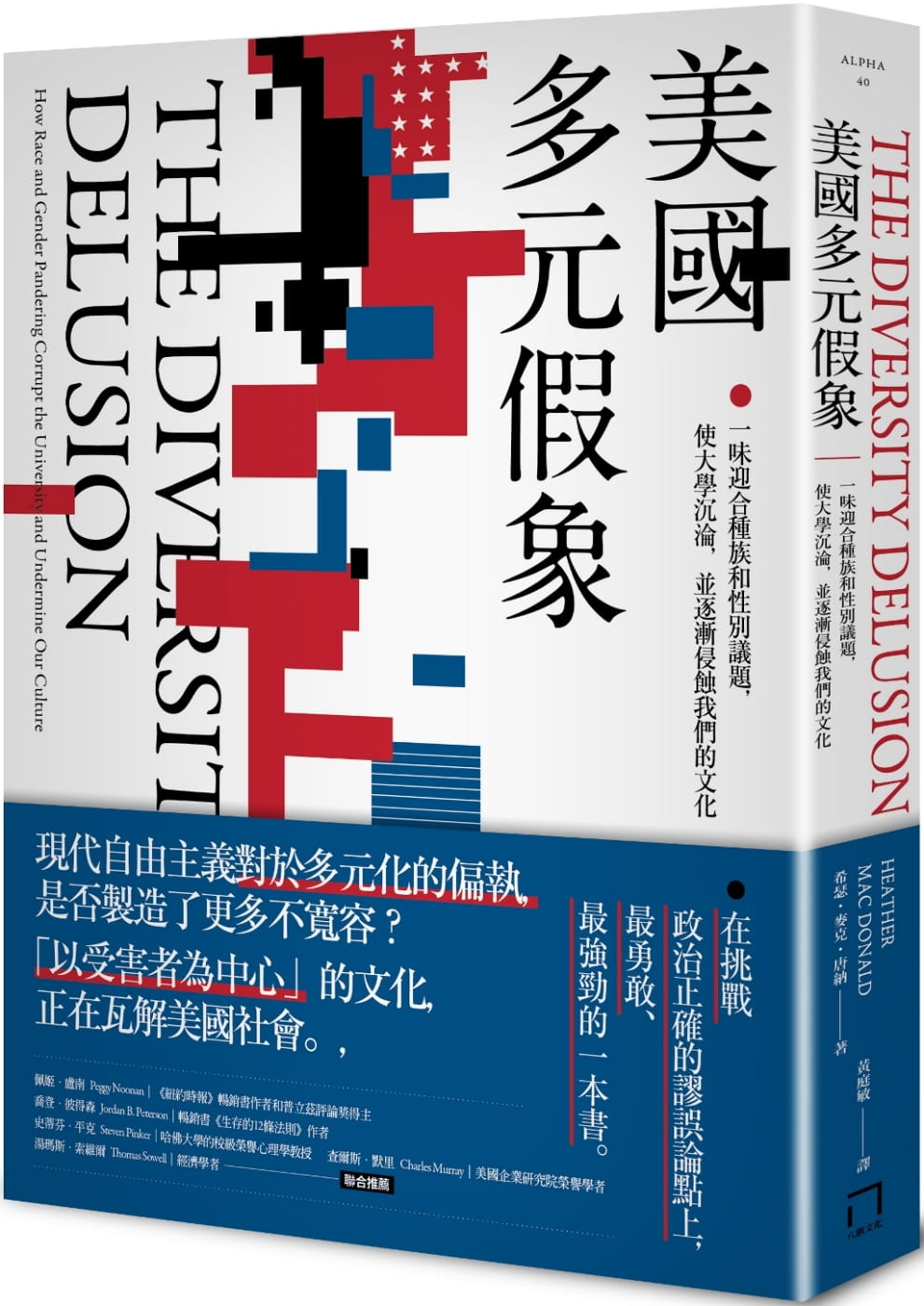推薦序(節錄)
思想史側寫:不平等世界的元凶、幫凶和模仿犯
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我們的眼前應有盡有,我們的眼前一無所有。我們都在走向天堂,我們都在走向另一端。簡而言之,那時和此時是如此相似,聲量最大的某些權威人士都堅持以形容詞的最高級來形容—認為好的,就說那最美好,認為不好的,就說那是最糟糕的年代!──狄更斯,《雙城記》
顯而易見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讓這些人明白,另外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也存在世上。──歐威爾,《戰時日記》
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以上面那一段話來開啟《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1859),一個背景設定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關於發生在倫敦與巴黎的幾位人物之虛構故事。究其內容,除了同時描繪革命前夕貴族對平民百姓的凌虐,以及革命本身的殘酷與暴力,其書名似乎也留下了另外兩種「雙城」的想像:貴族與平民各自生活的平行宇宙,以及革命者憧憬的,那個烏托邦與革命之後的另一個血淋淋暴政的兩種國度。換言之,倫敦與巴黎之外,狄更斯這本歷史小說也暗示了同一個城市的兩種階級,以及革命事業的理想與現實之差距。
或許筆者過度詮釋了,但讀者手上這本《憤怒年代》卻真的意圖說明:何以我們身處一個充滿怒火且憤怒的年代?因為這是一個贏者全拿,政治與金融菁英欺騙並壓制了社會大眾的不平等世界。
這個極其不平等的時代,是曾被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高舉為「歷史終結」的時代。因為人類自古以來對於自由、美好的社會制度之追求終在冷戰結束,資本主義與憲政民主全面戰勝了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之後迎來終點,人類也跟著成了歷史的「末人」(the last man);這個極其不平等的世界,也曾被《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宣稱為被全球化推土機(包括推倒柏林圍牆的民主觀念與自由市場思想,全球資訊網及其相關技術)給「抹平」的世界,人們不但可以隨時跨越國界,也必須順應這趨勢;放火燒麥當勞之類抗議資本全球化的活動根本毫無意義。
對於上述福山與佛里曼競相代言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立場,一度是英國新自由主義—或說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主要推手;然而教主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欽點的傳人政治哲學家格雷(John Gray),在《紐約書評》上嚴厲批評洋溢於佛里曼《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過度樂觀與自滿,也早於九○年代福山出版《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之後立即撰文批評。據其理解,佛里曼雖然在思想觀念迥異於馬克思主義,但卻犯了與後者相同的化約主義(reductionism)錯誤,認為歷史最終會選擇一種經濟模式及其伴隨而來的單一生活方式,亦即追求自利、競爭以及贏者全拿的邏輯,且所有人類都必須按此遊戲規則生活,這才是正途(一如福山的錯誤);另一方面,全球化雖讓有錢人能隨時跨越國界,特別是那些標榜商人無祖國的成功企業人士,但對勞碌的受僱大眾而言,地球不但是圓的,還崎嶇不平,多數人沒有說走就走的旅行,更不可能脫離就業牢籠,甚至愈是工作,愈是讓富者恆富、窮者恆窮。
來自印度的潘卡吉•米什拉選擇了站在格雷這一邊。正如本書在提及格雷時說的,冷戰不僅沒有讓歷史結束,甚至會讓「本來被冷戰制伏住的『更多原始力量(即將回歸),包括民族主義和宗教,還有基本教義派,和或許很快就會出現的馬爾薩斯主義(Malthusianism)。』……他(格雷)不僅點出自由主義在知識體系上的無能為力,也同樣點出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事實上,米什拉與格雷近年來數次共同現身英國思想沙龍進行對談。牛津思想史教授麥爾坎•布爾(Malcolm Bull)和澳洲資深記者賽巴斯蒂安•斯特朗吉奧(Sebastian Strangio)也分別在《倫敦書評》與《洛杉磯書評》當中指出,米什拉在思想與寫作風格上類似格雷,而著名作家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甚至將此一書寫風格追溯至以撒•柏林(Isaiah Berlin)。(想必熟悉格雷與柏林思想史著作的讀者,閱讀本書時也能會心一笑。)
柏林、格雷和米什拉的共同特點,在於試圖以思想史的敘述方式來分析當前政治現象的緣由。格雷曾以《夢醒啟蒙》(Enlightenment’s Wake, 1995)嚴厲批評源自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所採取的進步史觀,亦即相信人類的理性長久發展下來必然會支持個人自由與憲政民主(反對者當然意味著某種落後、野蠻或受制於非理性思維),不但簡化了人類的歷史發展,且若以國際政治手段來推動,既不尊重又恐有抹滅不同文化或文明之虞,因此他提出了「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理論,倡議以「和平共存」為目的的「暫定協議」(modus vivendi)政治方案。其後出版的《虛幻曙光》(False Dawn, 1999)更直指新自由主義的思想盲點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蓋達組織以及何謂現代》(Al Qaeda and What it Means to be Modern)一書則將國際上的恐怖主義與宗教基本教義運動追溯至現代性本身的矛盾。
某程度而言,米什拉接續了格雷的思想史工作,並將針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延伸至國際層次的文化交流與比較思想史。二○一二年出版的《從帝國廢墟中崛起》(From the Ruins of Empire)一書,已充分展現了他的博學和恢宏視野。其主要論點為:從中國的梁啟超到印度的泰戈爾,東亞知識分子在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入侵時,應對方式皆不脫「以夷制夷」的基調,其實踐結果不僅失去了自己,更繼承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
據此觀點,追求富國強兵對抗西方船堅炮利是一種,「全盤西化」也是一種以想變成像敵人那樣的心態的反抗方式。「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意圖擇取想要的部分來模仿,而即便是高舉自身文化的「復古」策略,本質也是一種被動、一種反應,而非展現積極能動性的主動。至於作為改革方向的各種舉措,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手段而非本身被當作目的追求,即使高舉自身文化傳統,實則暗藏著怨恨與羨慕,想藉軍事、政治或和人家平起平坐來恢復民族自尊心基調,其背後動機不脫效仿意圖!
無論如何理解,追求現代性本身就是種想變得跟西方一樣的心態。即使可以將其目的修飾成「東方」或「另一種」現代性,仍是以西方現代性作參照或對照。甚至,東方與西方的界定本身就是源自西方,更別提我們身處的「遠東」兩字意味什麼。畢竟,「民族國家」(nation-state)源自十七世紀西伐利亞體系建立之後的政治體制,而以共同文化和語言作建國基礎的「國族主義」(nationalism)之所以成為一種系統性論述和席捲全球的政治運動,也是源於西方,或更精確地說,是起源於德國浪漫主義。
本書基本上是《從帝國廢墟中崛起》的延續思考。在此,作者一方面把目光轉移到世界各地正在進行的各種抗爭,從溫和的公民抗命到激烈的革命,乃至宗教基要主義以及各種恐怖主義,另一方面則把焦點放在「模仿」與「怨憤」概念,更進一步細緻化這兩個解釋工具。這兩條敘述路線,匯集在對法國思想家盧梭的理解上。 米什拉基本上將盧梭理解為「憤青」(angry young man)始祖,並將向來與尼采連結在一起的「怨憤」(resentiment)概念歸功於盧梭,然後接受了齊克果對此概念的界定:一種誘發於「既認為自己與他人平等,卻又想取得壓倒他人的優勢」之嫉妒心理。作為一種負面情緒,那是能凝聚散眾為一個集體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即使人們以「正義」為名來控訴,那也只是包裝,因為真正的怨憤對象並非「不平等」,而是為何「你」有,但「我」沒有?為的是想要取得嫉妒對象的地位、擁有的一切,甚至想在存在上取而代之。
嚴格說,取而代之的意圖是想同時消滅受妒的「他人」和原本的「自己」。就此而言,「欲望的模仿」(mimetic desire)既是對敵人的最高敬意,也是對自己最極致的貶抑。反帝國主義的米什拉和活躍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倡議者,英國史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於是難得有共識:掌握資本主義的中國,終究只是下載了西方的應用軟體。此模仿是注定失敗的策略。更弔詭地說,成功即是失敗!
「怨憤」和「欲望的模仿」兩個概念的提出,雖然能回頭更好地解釋《從帝國廢墟中崛起》裡關於國家效仿何以注定失敗的論點,不過《憤怒年代》一書旨在說明目前發生於全球各地、非國與國之間的大小規模政治抗爭與鬥爭,並指出類似的弔詭無所不在。值得注意的是,米什拉將這些衝突歸結為「現代性」(modernity)本身的困境,且根源在於其所承諾的一切似乎永遠不能落實。
本書所謂的現代性,指的是啟蒙運動開啟的一種獨特的認知與感受結構,其組成包括了普世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價值,相信科學、理性,以及脫離中世紀傳統與習俗的可能,且認定世上所有文化都在這一個發展的過程當中的線性進步史觀,也因此有先來後到之別,而先進者有教導或提攜落後者的義務。更重要的是,這也包含了一種個人與他人乃至世界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論及現代性內在矛盾的時候,本書將焦點圍繞於伏爾泰與盧梭的爭辯之上。伏爾泰是法國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且宣揚世界貿易、物質繁榮和炫耀性消費文化,盧梭則及其厭惡財富所帶來的各種社會不平等,以及其所導致的相對剝奪感、嫉妒,還有在嫉妒當中的自我迷失—換言之,平等與自由不過是有錢人的權利,而作為啟蒙運動政治化身的自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偽善,不過是西方帝國的幫凶。
自由主義建構的現代政治和經濟秩序,在米什拉的眼中其實是帝國主義的修辭;肆虐當代世界的國族主義及其經常伴隨的威權乃至獨裁政權,其實是西方帝國的模仿犯,伊斯蘭國和其他恐怖主義也是如此。存在於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特別是指向平等、均富的社會,但實則只能讓一部分的人先富起來,然後藉各種法律制度來保障此一優勢,讓窮者恆窮、終身為其服務,這是人們憤怒的理由,也是當前各種極端政治鬥爭的溫床。
過去生活於印度北方喜馬拉雅村莊的作者,曾擔任記者並親眼目睹自己國家的政客如何高舉自由主義的進步大旗,以教化為由壓迫穆斯林教徒和克什米爾。《從帝國廢墟中崛起》一書的出版,已讓他在祖國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物,而想必本書並不會讓事情改觀。畢竟,《憤怒年代》不僅解釋了人們憤怒的理由,更提供了一個多數人應當憤怒的理由。換言之,它替二○一一年「占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的口號做了一個漫長的思想史注腳:這是一場百分之九十九對百分之一的戰爭!
移居倫敦的米什拉如今儼然是格雷的繼承者,雖然在推論的嚴謹度不如後者,但在反自由主義的言論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有憤青的味道,本書對數十位思想家與革命家的描繪,更讓人聯想到柏林的綽號—「思想界的帕格尼尼」。《憤怒年代》提供的敘事也許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卻闡述了新自由主義陣營長期意圖掩蓋的另一半真實故事。畢竟,正如歐威爾所言,任何事情都不會讓那百分之一的人明白,另外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也和他們一樣存在同一個世界上。現代世界的主題曲是《雙城記》,而弔詭的是,對於百分之九十九當中不會生氣的多數人,作者其實也沒有憤怒的理由,因為他們願意相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涓滴效應」(trickle-down effect),依舊想張開大口等待那百分之一的人吃著大餅時掉下的屑屑,甚至為了占有比較好的位子互相推擠,而不是起身反抗體制。
這不正是模仿犯會做的舉動嗎?
葉浩 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