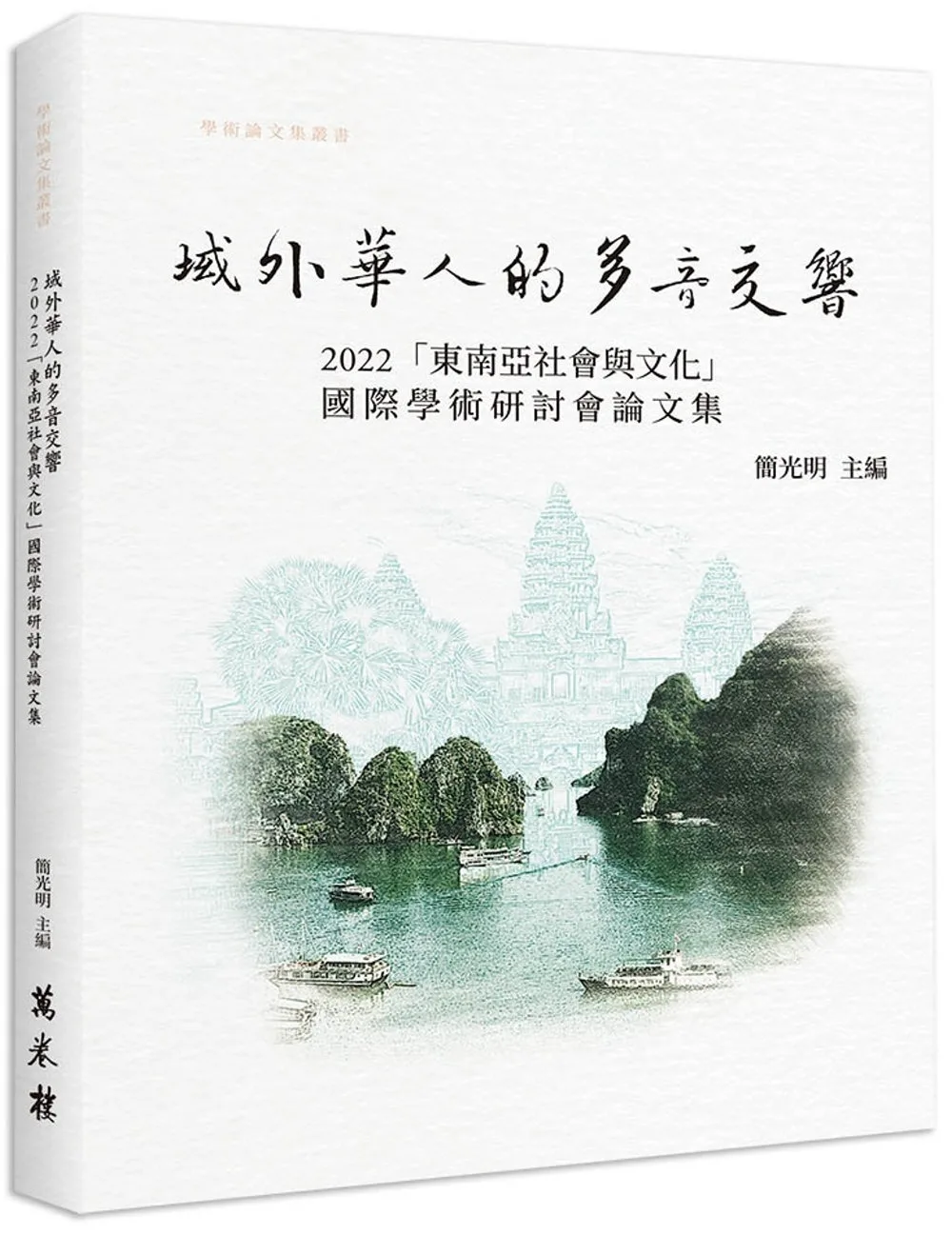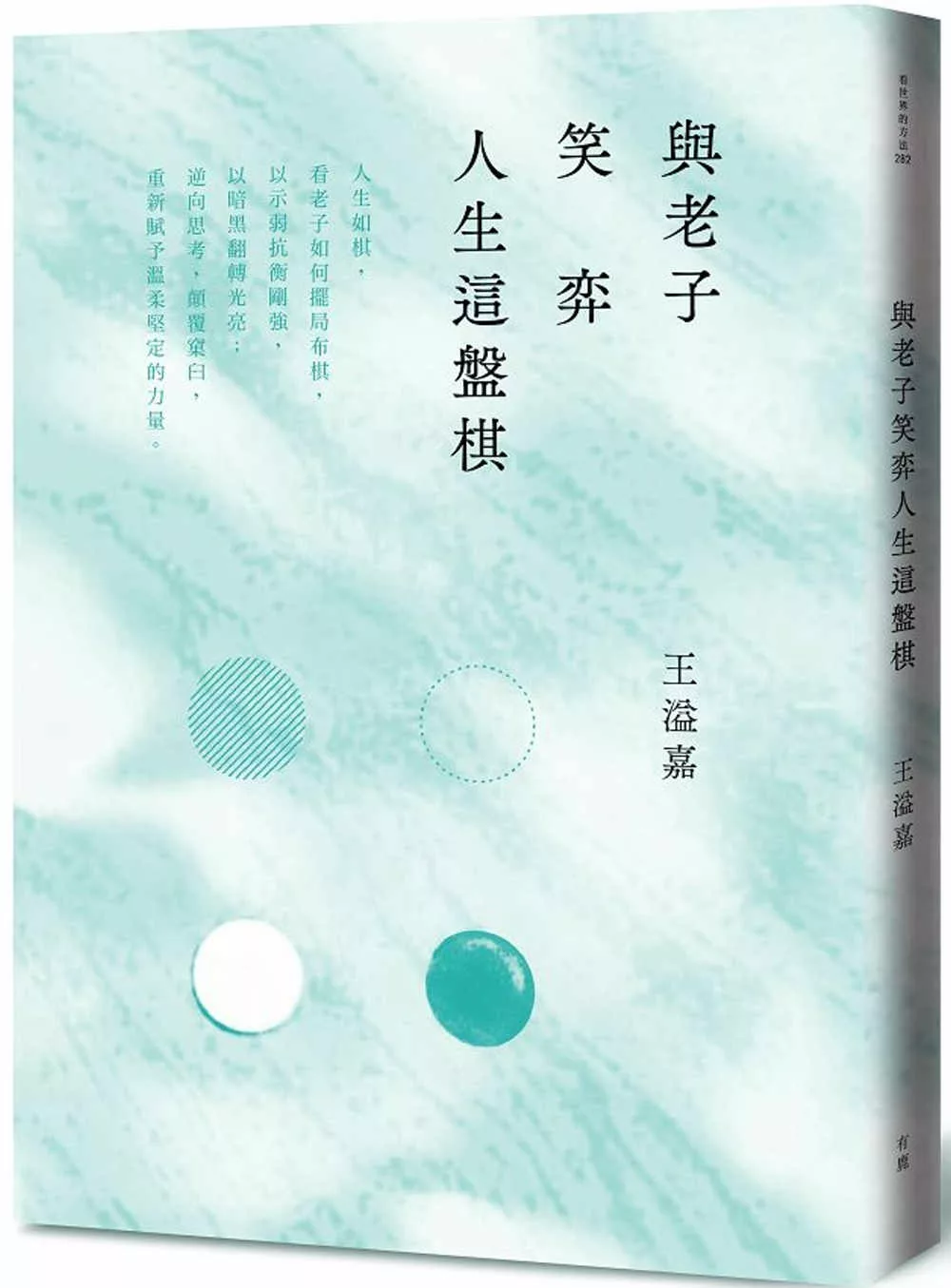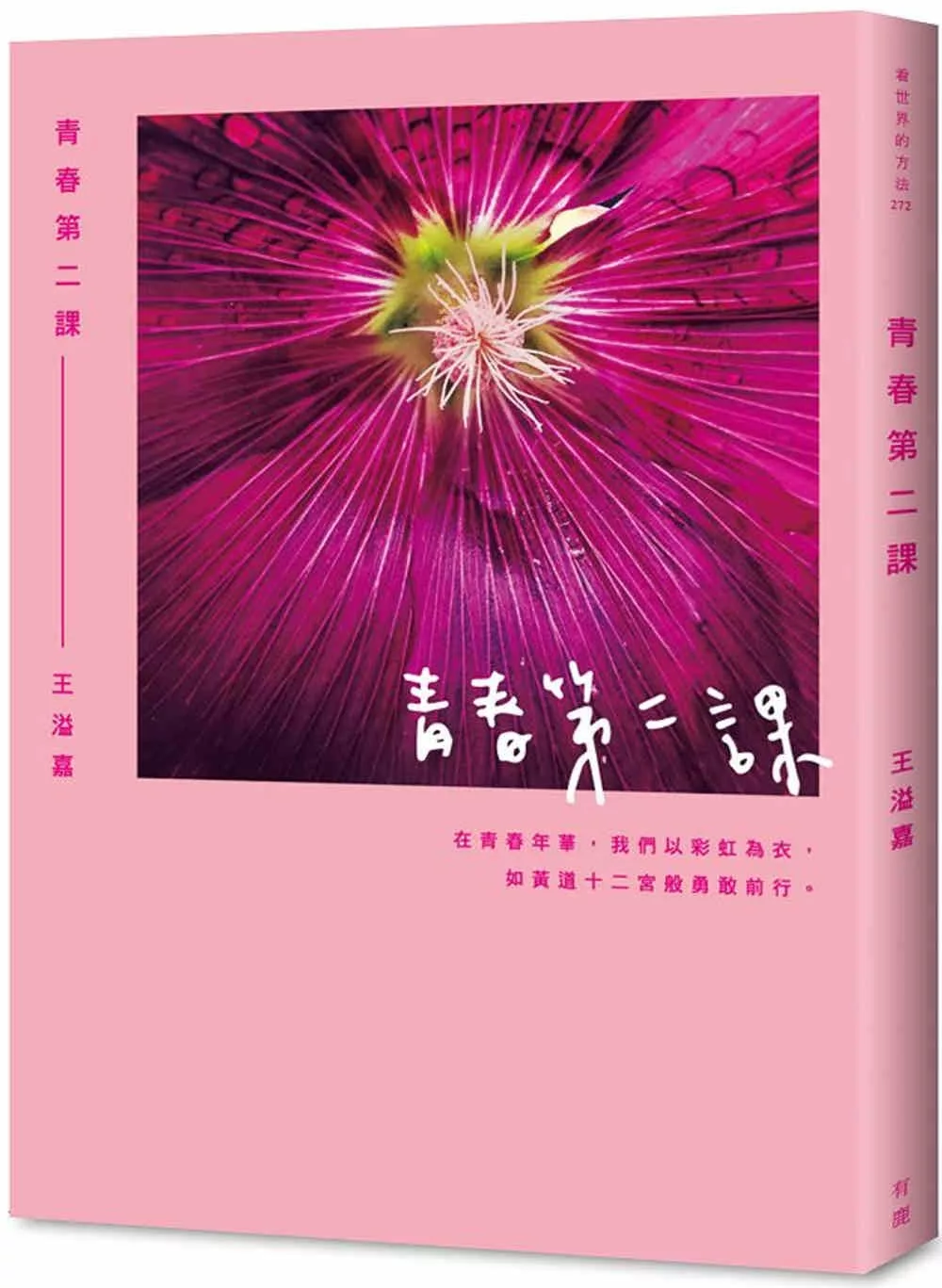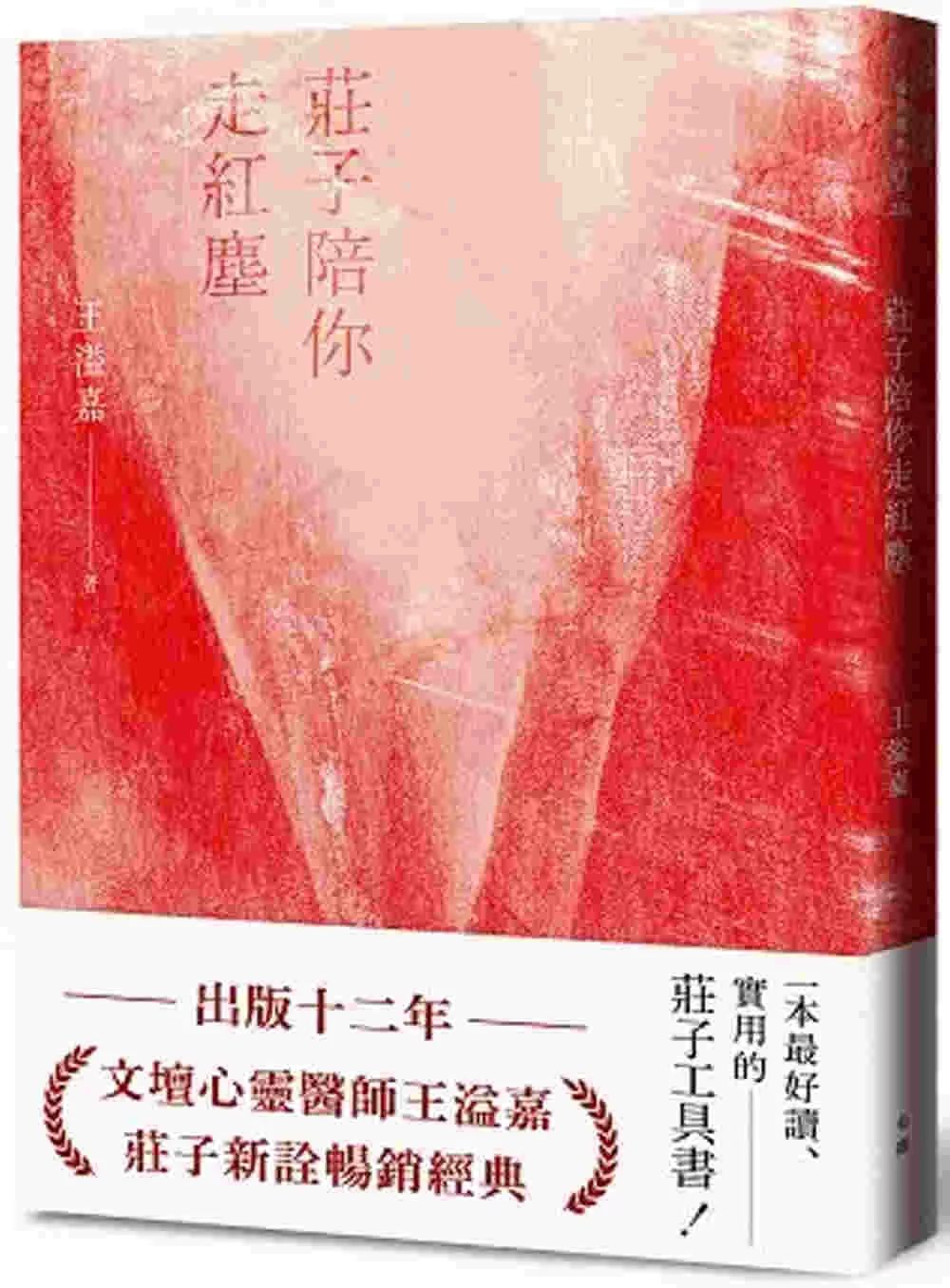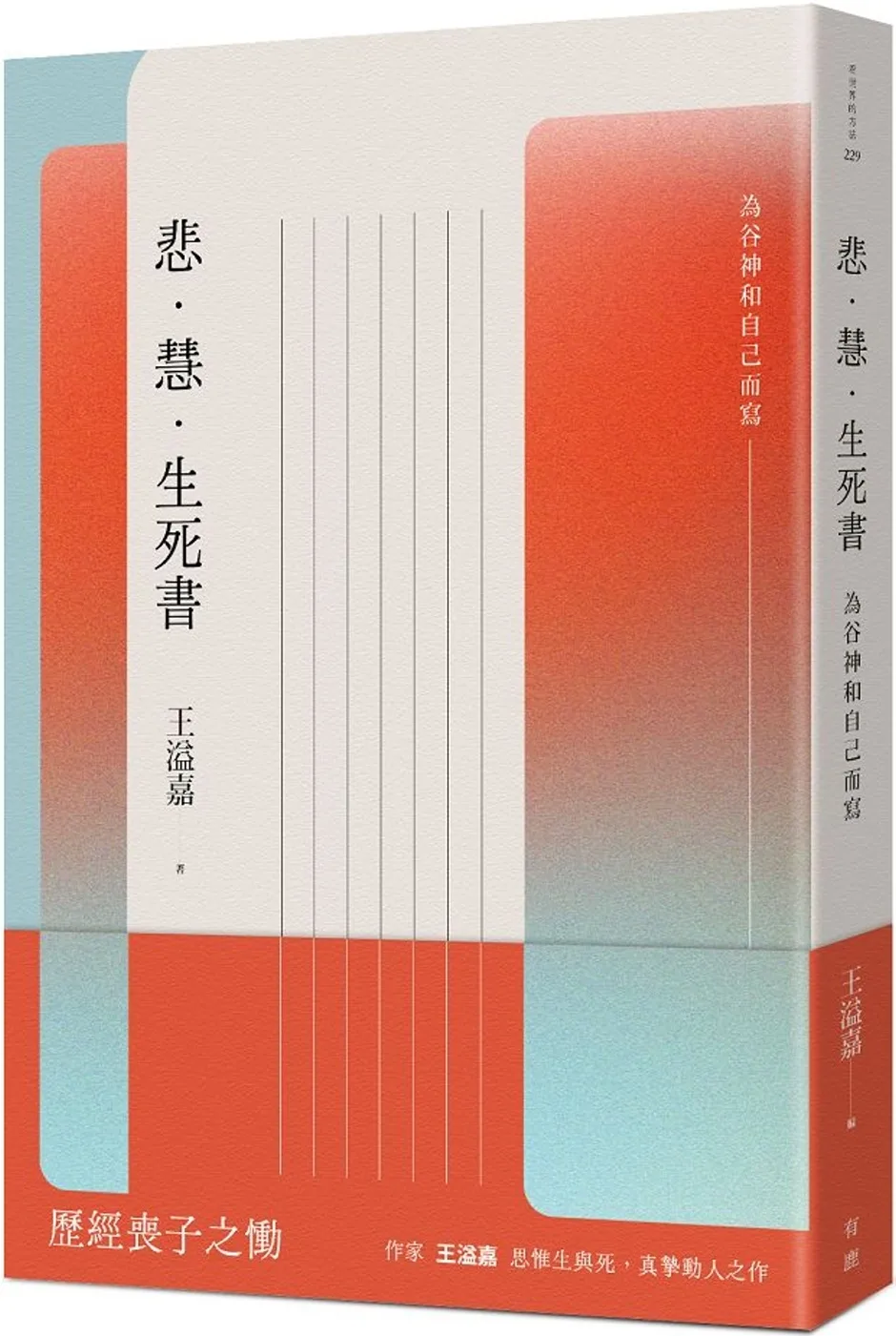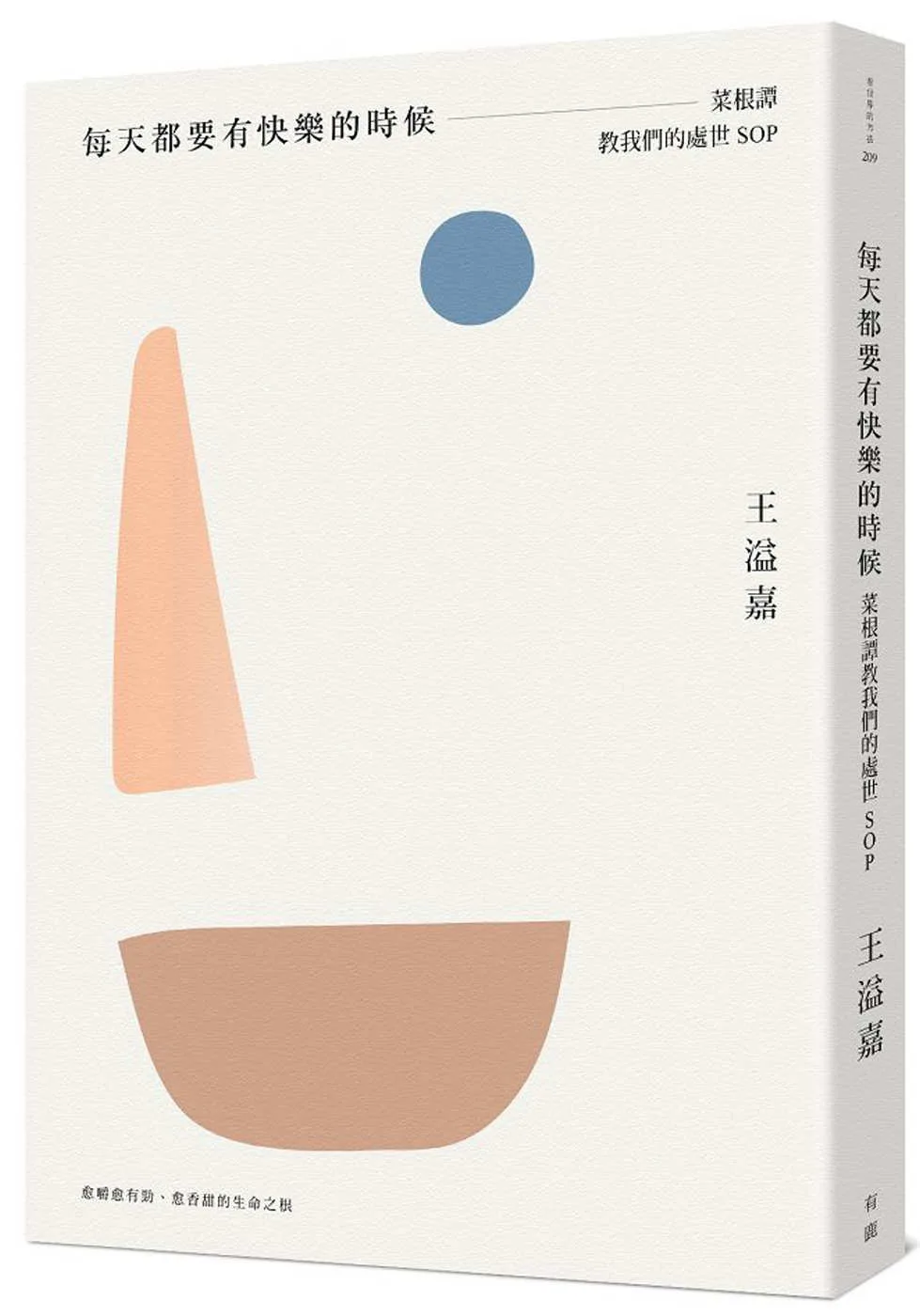自序
別窗有奇景:古典文學的新詮釋
我的闖入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可以說是出於偶然的機緣。將近三十年前,師大中文系的鄭明娳教授打電話到《健康世界》雜誌社來,說她為《台北評論》策畫一個「從古典文學看中國女性」的專題,希望我能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分析一下《金瓶梅》裡的潘金蓮。與文學界殊少來往,將近十年未在外面的報章雜誌寫過文章,也從未分析過文學作品的我,第一個反應是以「忙」為「遁」。當時我的確是在「窮忙」,除了《健康世界》的編務外,更忙著由我和妻子一手包辦的《心靈》雜誌的一切瑣事。但拗不過鄭教授的熱心與盛情,最後還是答應了。
在寫了〈從精神分析觀點看潘金蓮的性問題〉(現稍事增改,更名為〈誰是潘金蓮:《金瓶梅》裡的淫婦與性事〉)後,當時任《台北評論》執行主編的林耀德又來找我,要我「繼續寫」。恭敬不如從命,所以我又在《台北評論》寫了兩篇:〈從梁祝與七世夫妻談浪漫愛及其他〉和〈從薛氏父子傳奇看伊底帕斯情結在中國〉。後來《台北評論》停刊,耀德兄到《台灣春秋》擔任文學主編,他又來邀稿,要我轉移陣地,結果我跟著轉進到《台灣春秋》。隨後,耀德兄離開《台灣春秋》,我不知進退,還繼續寫下去,寫到後來,居然已到了能出一本書的地步。
但我的闖入中國古典文學領域,也有機緣以外而近乎命定的成分。在鄭教授向我邀稿時,我正處於「四十而大惑」的人生危機中,幾經徬徨,做了兩個重大決定:一是停掉以介紹西洋心理學、精神醫學、腦神經生理學、人類學和科學哲學為主的《心靈》雜誌;一是投靠名門大派,改到各報章雜誌上寫文章。鄭教授和耀德兄成了適時出現的「貴人」,雖然我很久以前就想以「西學為用」,來理解「中學」這個「體」;也很想碰一些古典文學,以博得出身台大中文系妻子的「讚美」,但一直停留在做白日夢的階段。若沒有他人催逼與發表的園地,我可能到現在還未動筆,或者已改寫別的東西。
這些文章在刊載時的專欄名稱為「古典今看」,但寫了一兩篇後,就發現我的「看法」跟學院派文人不太一樣,不同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我所探討的多屬「周邊文學」,譬如《七世夫妻》、《薛丁山征西》、《肉蒲團》、《封神榜》、《周成過台灣》、《子不語》、《笑林廣記》等;即使在討論《紅樓夢》時,我的主題依然是林黛玉的病與死這個周邊問題。一是我除了用已被接納為一種文學批評理論的精神分析學和分析心理學外,還用了大量的社會生物學、意識進化論、性醫學、超心理學、人類學甚至腦神經生理學來解析這些文學作品;事實上,我是用我比較熟悉的知識體系來「看」這些古典文學的。
這當然跟我的所學有關,每個人都會受到他個人知識經驗的局限。我為什麼會以周邊的方法去分析周邊的文學作品,在相關的篇章裡,都已做了說明,此處不再贅述。個人的一個想法是,中國古典文學是祖先留下來的一份豐富精神遺產,要使現代國民再度親近它們,我們應該以更寬廣的視野、更多樣的角度來賦予它們以新義,為它們爭取更多的讀者。筆者誤打誤撞,覺得自己所寫的,在學院派文人眼中也許根本稱不上什麼「文學評論」,但即使屬於旁門左道的散兵游勇,既然寫了,卻是有心要賦予這些文學作品以新義的。雖然有心,不過顯然也不夠用心,因為一個月要寫一篇,加以諸事煩忙,每篇文章從閱讀原書到撰文,只能有一個禮拜的時間,疏拙之處在所難免。
本書在一九八九年初版後,承蒙各界厚愛,發行了近二十刷,也在中國大陸發行簡體字版。後來因個人疏懶,賣完了沒有再印,想就此不了了之;如今在絕版多年後,承蒙有鹿文化許悔之社長好意,鼓勵我重新出版,所以我對舊文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在既有的架構裡添加新的枝葉,譬如在談《白蛇傳》時,多了文學進化論的看法;在談《金瓶梅》時,討論了潘金蓮是否有想要「自我羞辱」的被虐傾向;在談《包公案》時,增加了中國官場偵辦刑案時特有的「包青天情結」。另外,我也增加了一篇〈唐詩別裁:《楓橋夜泊》與《慈烏夜啼》〉從文學之外的角度去突顯這兩首唐詩所涉及的一些真實與心理問題,期望大家在欣賞優美的詩文之餘,能多一點省思。
?
王溢嘉
二○一九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