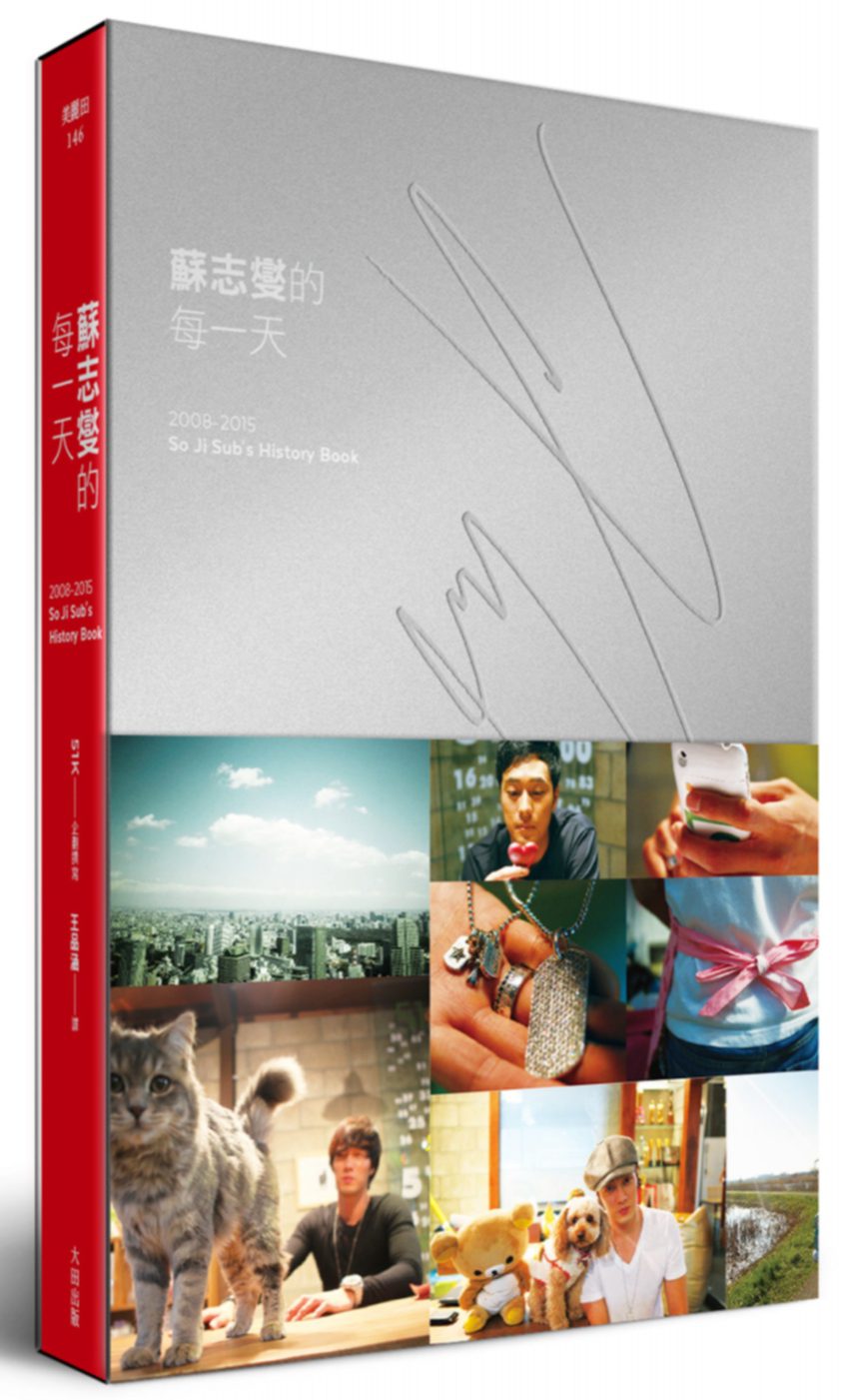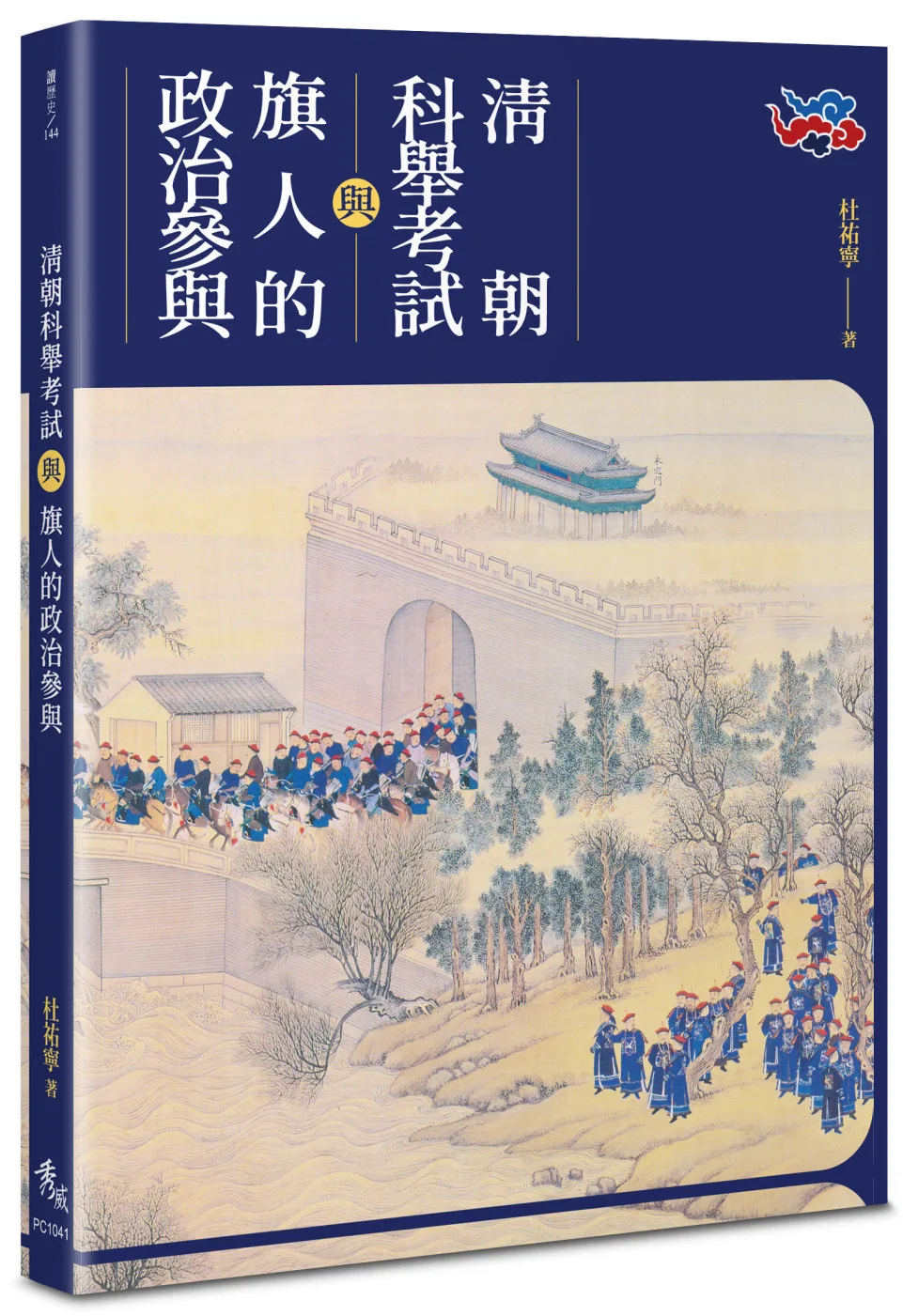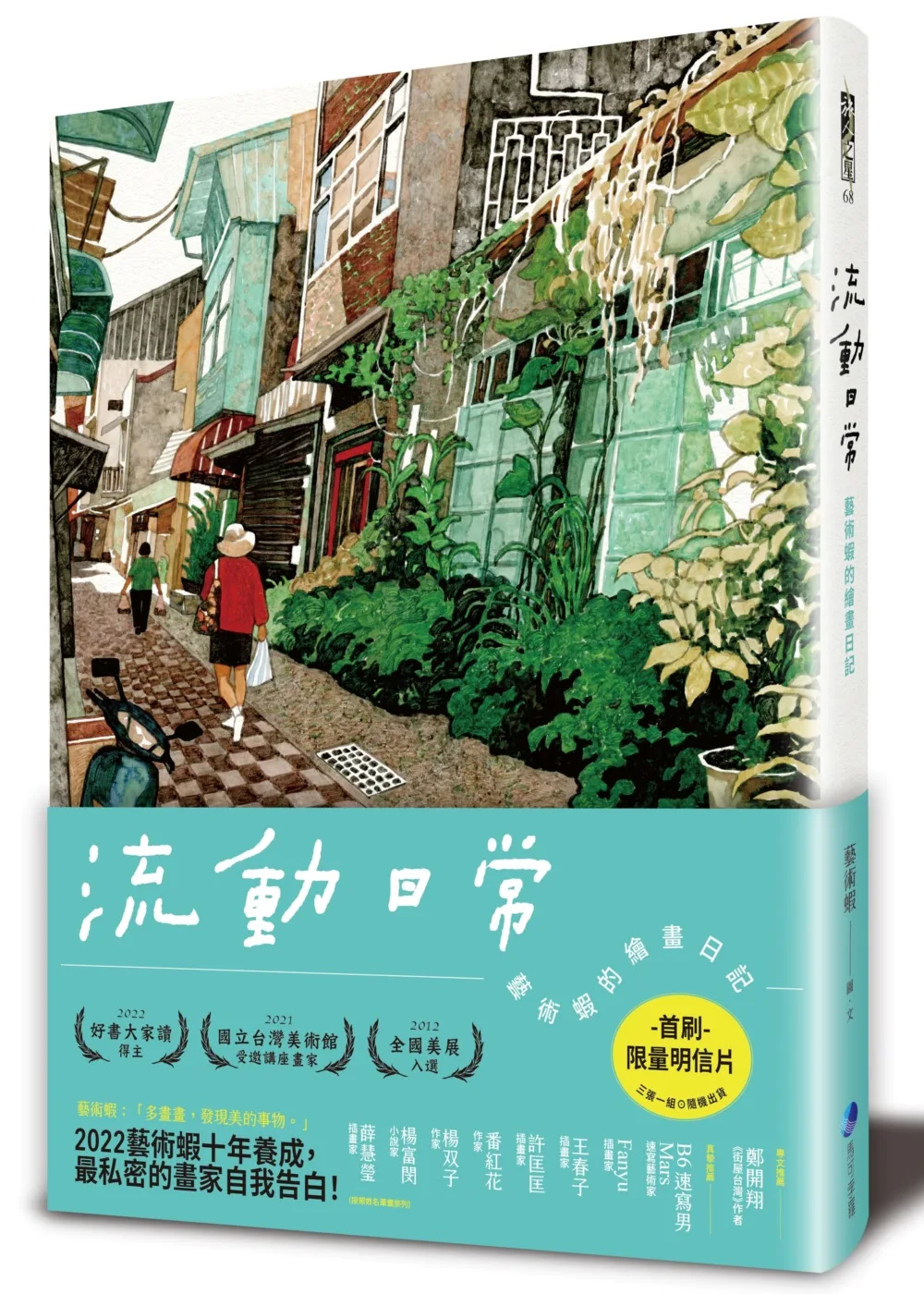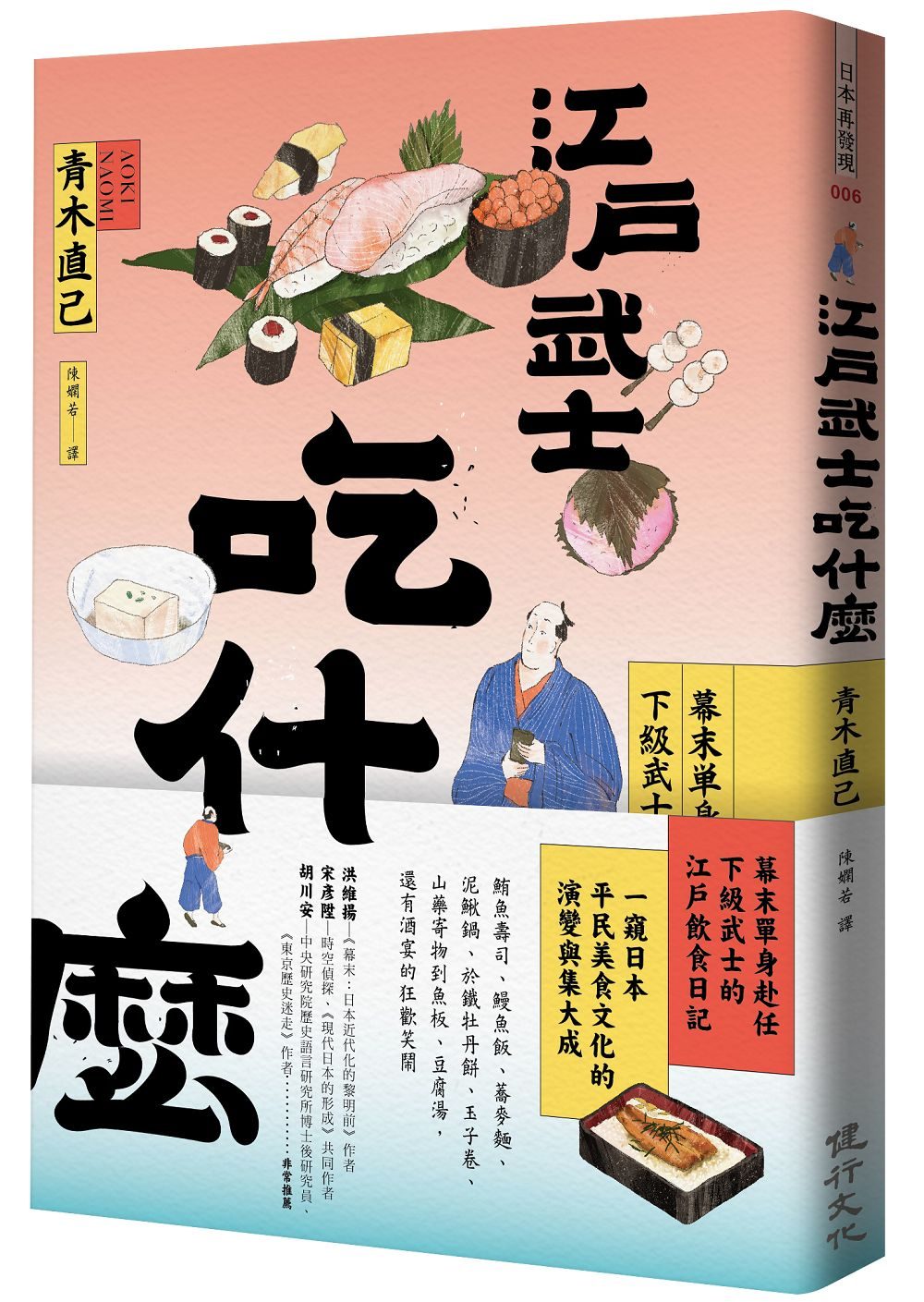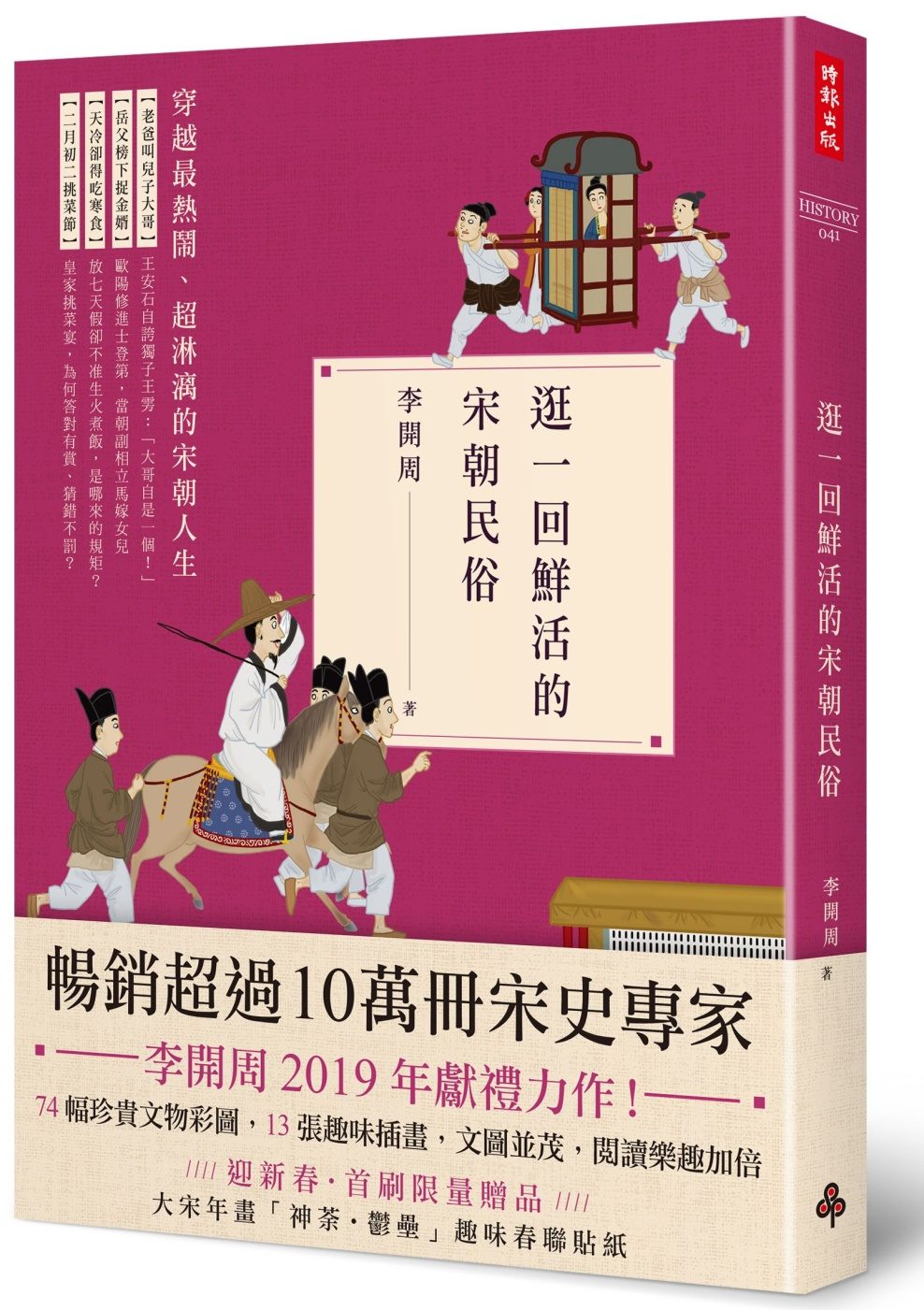導讀
郁慕俠和他眼中的老上海風華
郁慕俠(一八八二年-一九六六年)別名平章,上海青浦人。上海龍門書院和江陰南菁書院肄業,上海師範講習所卒業,晚清秀才。入民國後,曾任求實小學、龍門附小等校教員,一九一三年進入報界,先後供職《時事新報》當校對員,為漢口《武漢商報》、北京《益世報》、北京《晨報》等報館的通訊員。一九四七年任上海市銀樓業公會秘書,一九五二年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編纂,一九六一年受聘為上海市文史館館員。著有《上海鱗爪》、《慕俠散文集》等。編有《格言叢輯》、《慕俠叢纂》等。
寫上海老掌故的,最著名的有陳定山的《春申舊聞》、《春申續聞》。「春申」乃是指老上海,因戰國時代它是楚國春申君之封地,《春申舊聞》、《春申續聞》意思即是「老上海的風華往事」。陳定山從父輩起,便長居滬上,嫻熟上海灘中外掌故逸聞,他好京崑、工於書畫,又交遊廣闊,結識了老上海許多社會名流,目睹耳聞了老上海灘名流們的過往,故對老上海往事爛熟於胸,如老上海人如何過新年、吃西餐,或是「狀元女婿」指的是誰?「賭國詩人」又是何方神聖?他將老上海都會的人生戲幕,上至士紳名流、高官顯要,下及販夫走卒、戲子娼妓,一齣齣引人入勝的老上海風華放映在紙頁上。一代人事興廢,古今梨園傳奇,信手拈來,皆成文章,乃開筆記小說之新局,老少咸宜,雅俗共賞。
而郁慕俠的《上海鱗爪》顯然寫作的時間要更早,他請到名小說家兼實業家天虛我生(陳蝶仙),也就是陳定山的父親來寫序。陳蝶仙在序中云:「上海社會情形,誠所謂五花八門,千妖百怪,無奇不有。此書雖然不過緊緊披露一鱗半爪,然而窺豹一斑, 亦足以引起注意,使人有所認識。」書中所談的上海社會是指二、三○年代,而不同於《春申舊聞》的是寫到更多庶民的日常生活,包括食、衣、住、行、育、樂種種方面, 至於煙賭娼匪更是多所記載。它成了研究當年上海生活史不可或缺的珍貴材料。
例如談到老上海有著一個傳言:「要看上海灘最摩登漂亮的小姐們,只要每個禮拜天上午到億定盤路中西女塾的大門口去等著。」當時在上海剛剛興起的女子學堂就好比如今的高檔會所,聚集於此的女學生們大多都是家境殷實的小姐,張愛玲在〈談女人〉一文中曾經提及,「一九三○年間的女學生人手一冊《玲瓏》雜誌」,雜誌為女學生們提供最時髦的服裝樣式、最新的電影資訊、最流行的英文歌曲譜;而女學生們還成為雜誌內容的真人廣告。
對於摩登女郎,《上海鱗爪》有過較詳細的描寫:「現在最摩登的新女子,衣服尺寸越窄小越美觀。到了夏秋,只穿了一襲薄薄的短旗袍,袖口又短,不但露臂,竟是露肘,把她一雙臂肉完全顯露。又穿短褲和肉色絲襪,驟見之兩腿膀幾與雙臂一樣,走起路來扭扭捏捏,她的尊臀也一聳一凸的。總之這種形狀如叫思想陳腐的人瞧了,莫不斥為怪物;在軋時髦人見之,愈讚美她的全部曲線美的豐富了。」
另外《上海鱗爪》書中說,上海裁製衣裳的工匠,普通的是蘇幫、廣幫、紅幫;另外又有一種女裁縫,並不設店,而是上門幹活,主人供給飯食,一塊錢四個工。其所做活兒,大抵是布服、童裝,倘使是綢緞、毛皮,她們就要敬謝不敏。關於縫窮婆,《上海鱗爪》寫道:「縫窮一業,大半是江北籍婦人充之。她們臂膊上挽了一隻竹籃和一隻小凳子,籃中放著剪刀、竹尺、線團和碎布之類,在路上走來走去的兜攬生意。她們的主要營業是替人縫襪底、做脫線和補綴衣服上的破洞眼。」又云:「店家的夥友、廠中的工友與商鋪中的學徒,因為妻室和家長不在上海,故縫襪底和補衣服等工作都要叫縫窮去做,因此縫窮的生意也很好。至於『縫窮』兩字的解釋,是專門替代窮人做工,故名『縫窮』。」
二、三○年代之際,當時「洋」代表著一種時髦、一種潮流,國人尤其是有錢人對於「洋玩意兒」偏愛有加,有的甚至到了迷信的程度。《上海鱗爪》書中說:「叫起人來,滿口『密斯忒』、『密斯』;寫中國字,必喜橫寫;吃食水果,也要吃外國貨; 生病吃藥,也要購外國藥;連斷了氣直了腳,也要睏一口外國的玻璃棺材,才覺心滿意足。」對這股洋化的風潮狠狠地做出嘲諷。
郁慕俠描述,民國初年,大上海的電線桿上貼著諸多小廣告,也會夾雜出現「馬路如虎口,當中不可走」的警示語。雖然那時候已經在馬路兩邊開闢了一種專為人步行的道路,叫做「水門汀路」,奈何百年前的上海人和現代人一樣,常常喜歡在馬路當中踱方步,穿過馬路時也不左右張望,而是直剌剌地急衝過去。一旦碰上汽車疾駛而過,來不及剎車,往往會釀成慘案。當時上海已經有紅綠燈,雖然沒有專門的交警,但也有疏通交通的警捕。
《上海鱗爪》有一篇文章〈一席菜值三百元〉說:「常言說得好:『生在蘇州,穿在杭州,吃在廣州,死在柳州。』因為廣東人對於別的問題都滿不在乎,唯獨對於吃的問題,是非常華貴、非常考究,一席酒菜值到幾百塊,一碗魚翅值到二十塊以上,在廣東人看來很平常稀鬆的事,以故『吃在廣州』一句俗語,早已膾炙於人口了。」但是,誰都沒有否認,貴的背後,其實是更好,郁慕俠自己就作了說明:「據說這種奢侈豪貴的菜肴……原料是摒除豬羊雞鴨常見的肉類,都用山珍海味、奇禽異獸等貴重之品,價值越大,選用的原料也越貴。」
據平襟亞〈舊上海的娼妓〉:「『野雞』:凡屬蹤跡無定,臨時性的妓女,通稱『野雞』,在人行道口拉客。」而胡祖德《滬諺外編》:「『野雞』:滬妓下等者之稱,引申其義,凡營業之無行無幫,無統系者,皆為野雞。如野雞挑夫,野雞東洋車, 野雞輪船皆是。」但若把野雞說得生動傳神者要算郁慕俠的《上海鱗爪》:「海上之三等娼妓,亦猶平津之下處,然一般群眾口中不稱『下處』,都呼『野雞』(即雉妓), 此與平津不同。按雞為禽類,在家豢養的曰家雞,在郊野中自由生活的曰野雞,毛羽較家雞尤美麗,性喜翱翔,嘗四山覓食,行止靡定。今人稱此類娼妓為『野雞』者,因外表服飾之鮮華,其美相若;而深宵傍晚往往徜佯路旁或往返茶室間,川流不息,厥狀甚忙,似和在山陬荒僻中天然之野雞相類。此所以呼三等娼妓為『野雞』,義即指此。」 類似「野雞」的,還有如「十三點」、「吃豆腐」、「賣相」、「虛頭」等等當時流行的詞彙,更是研究滬語的流變不可多得的材料。
?
蔡登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