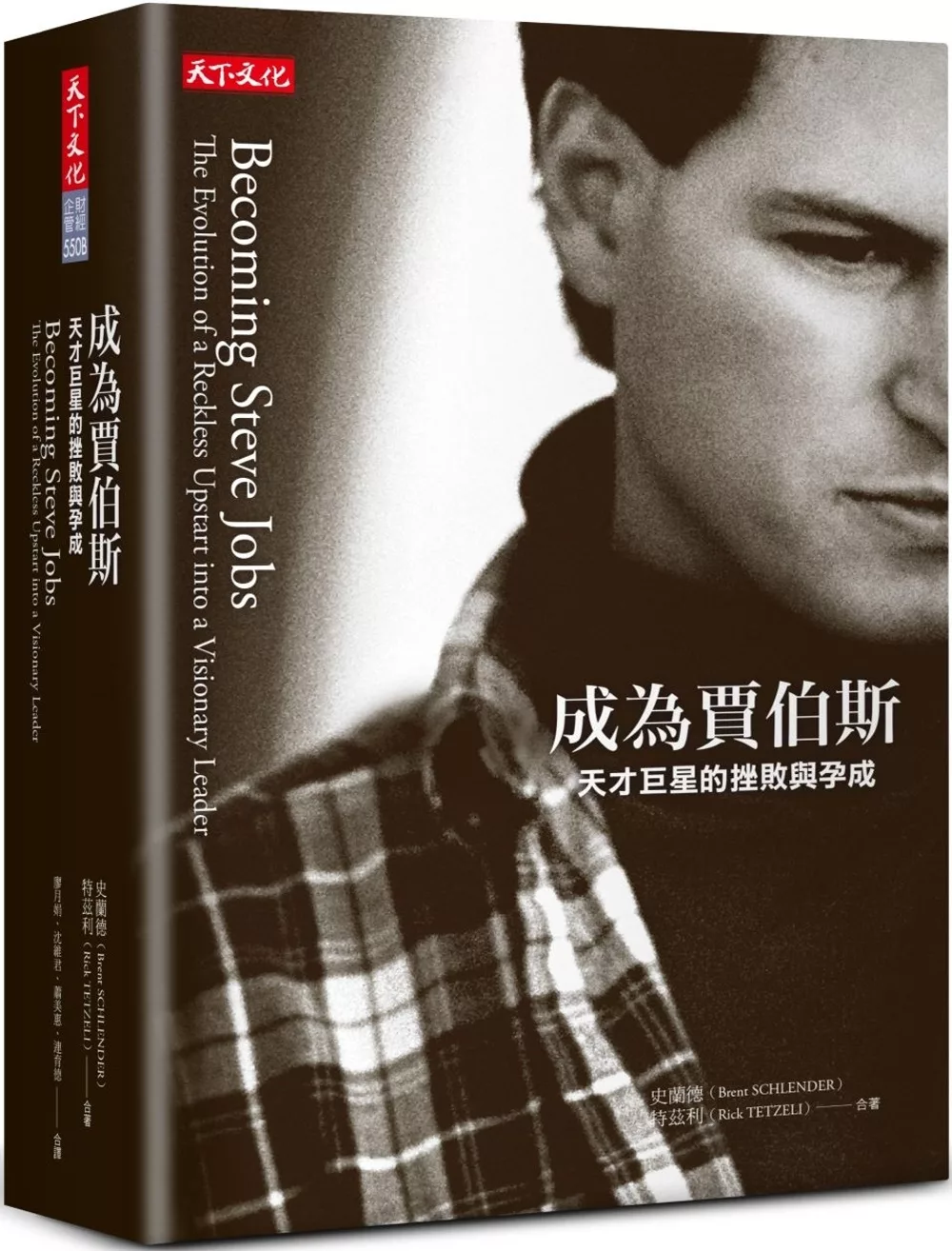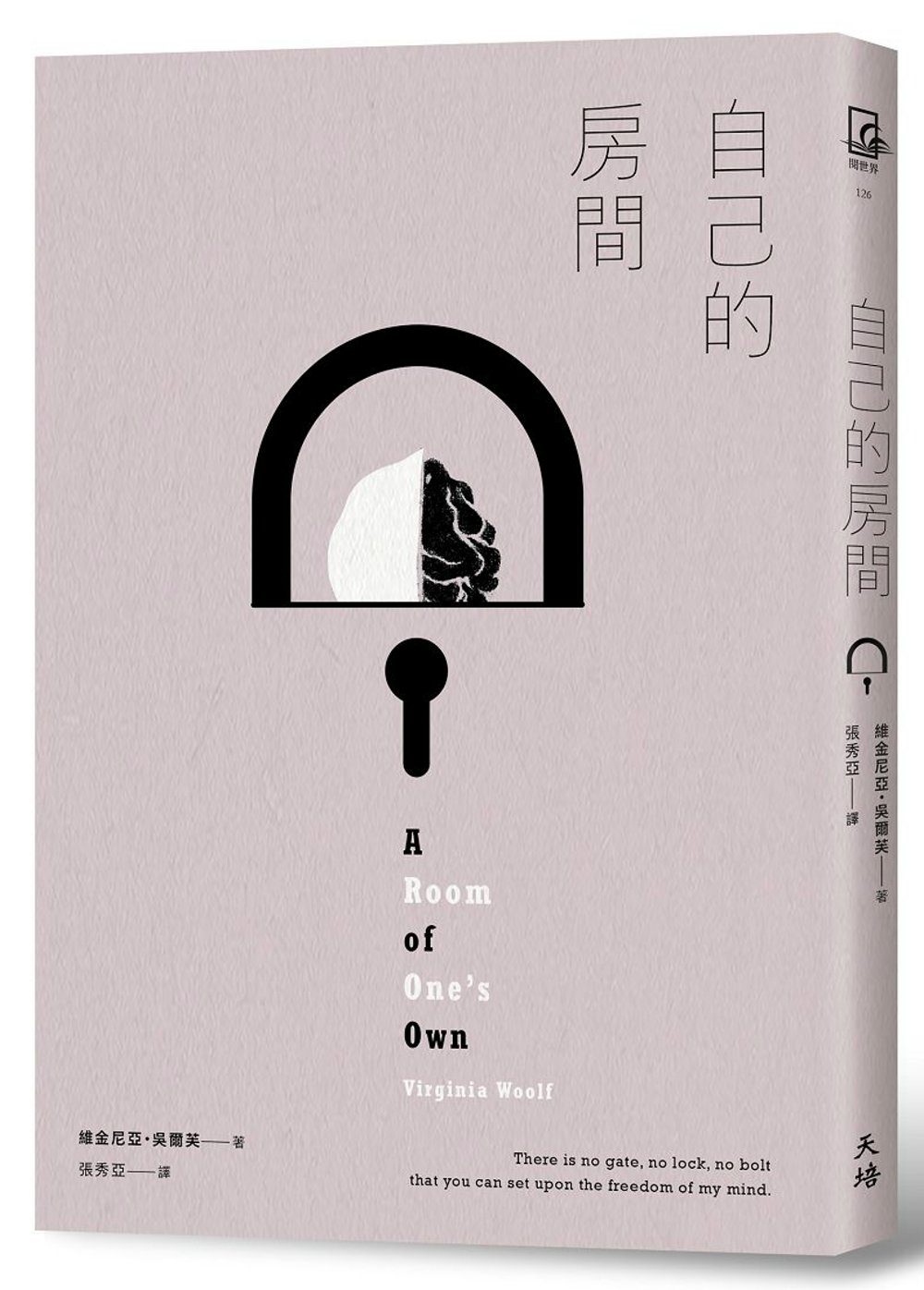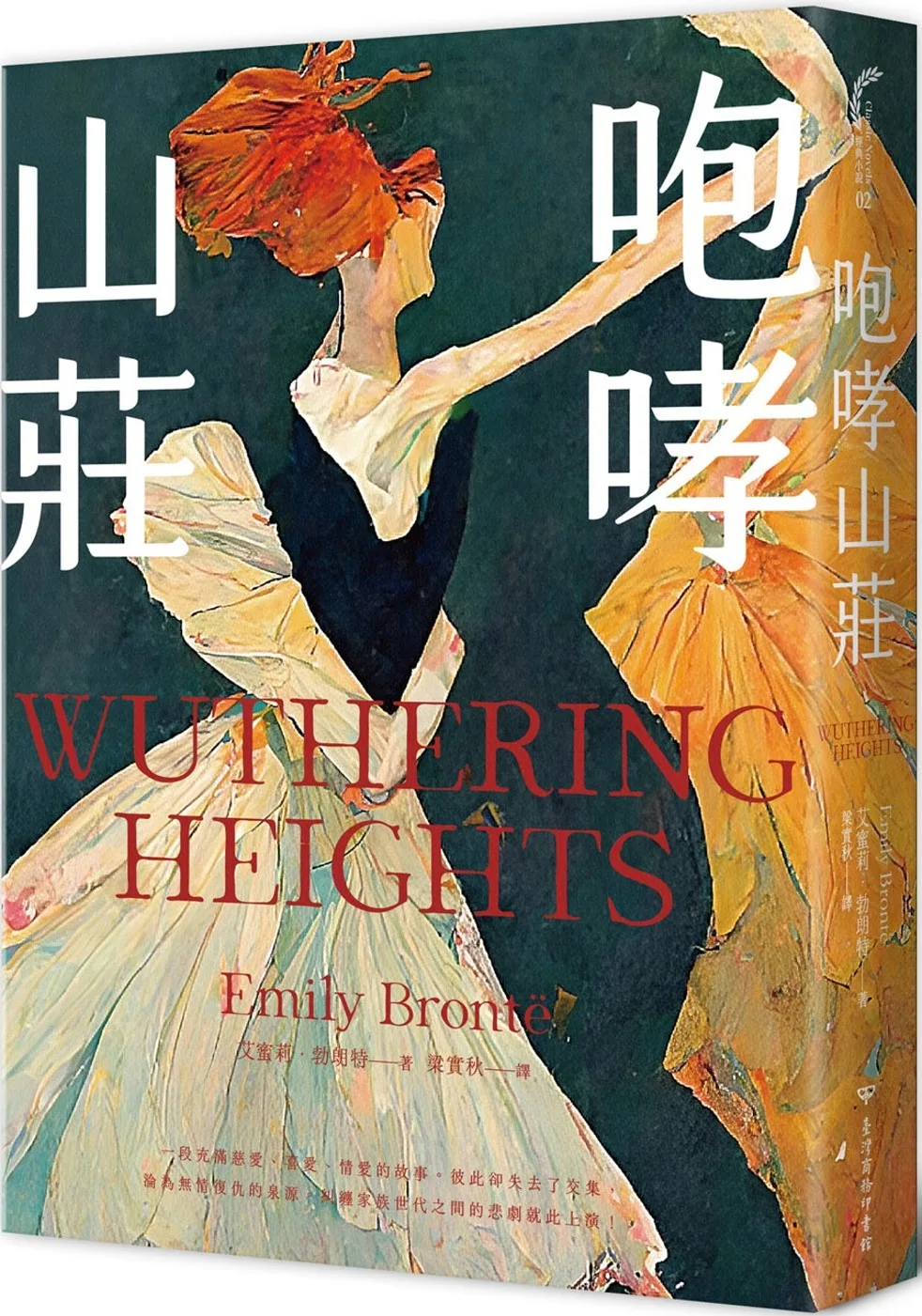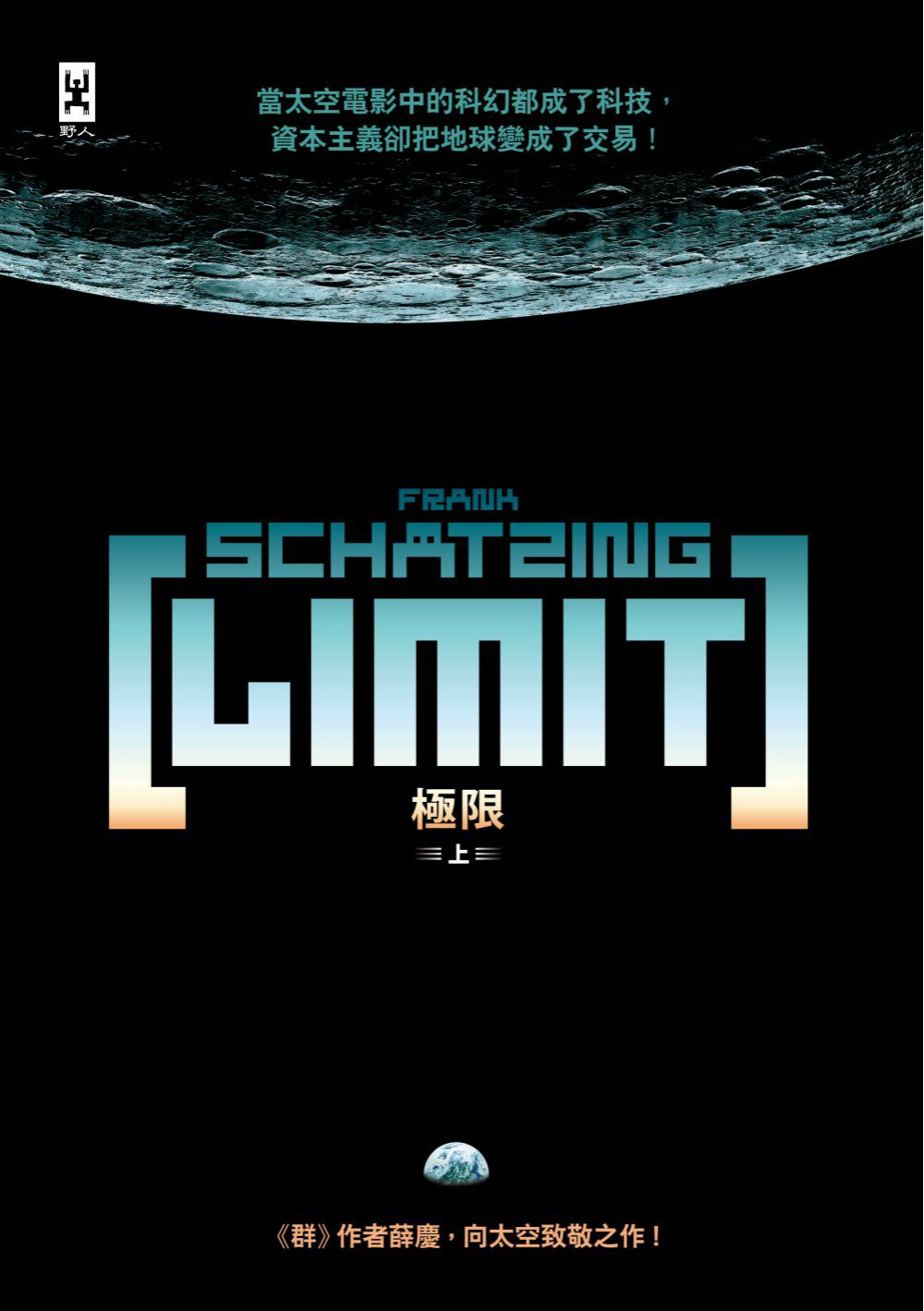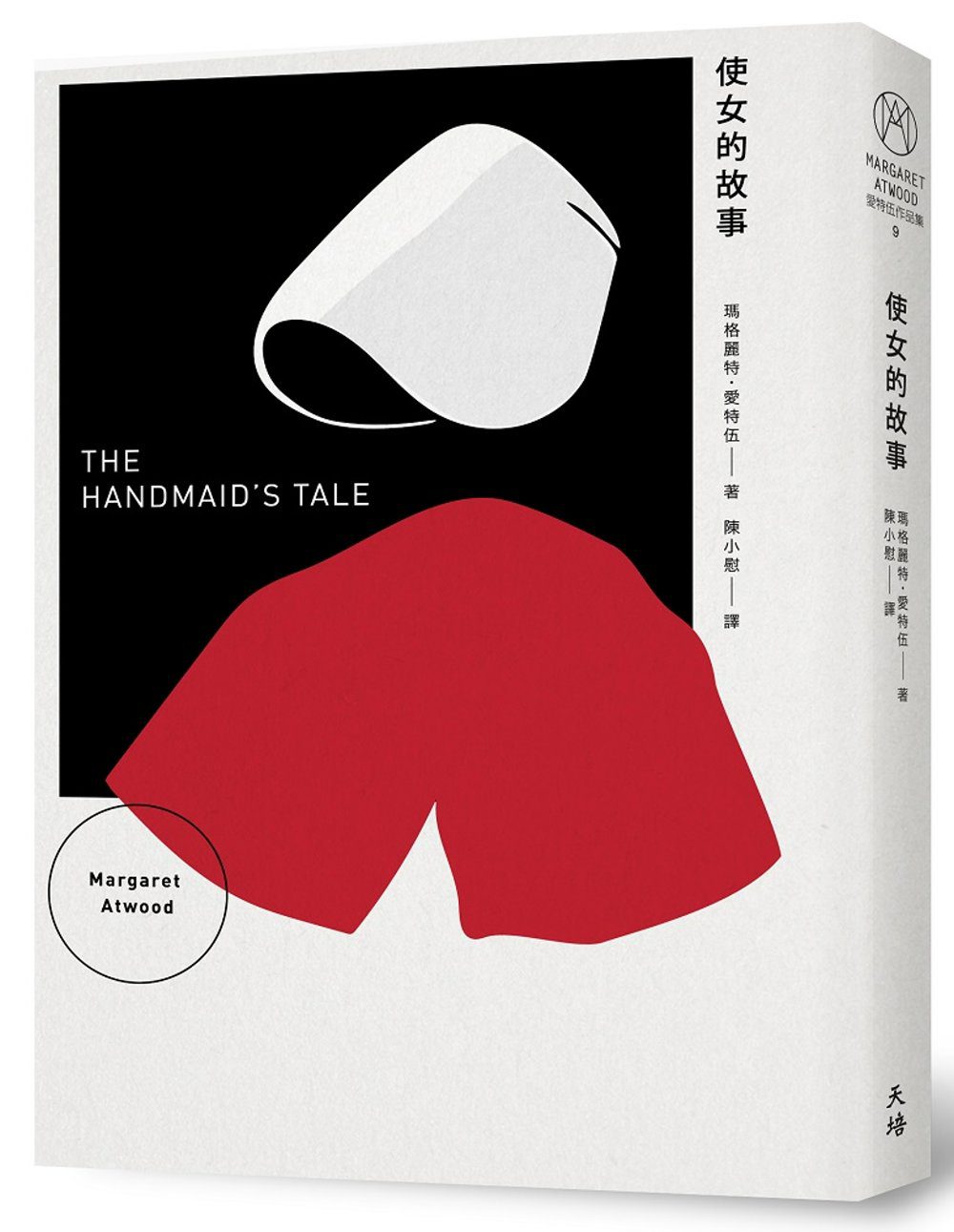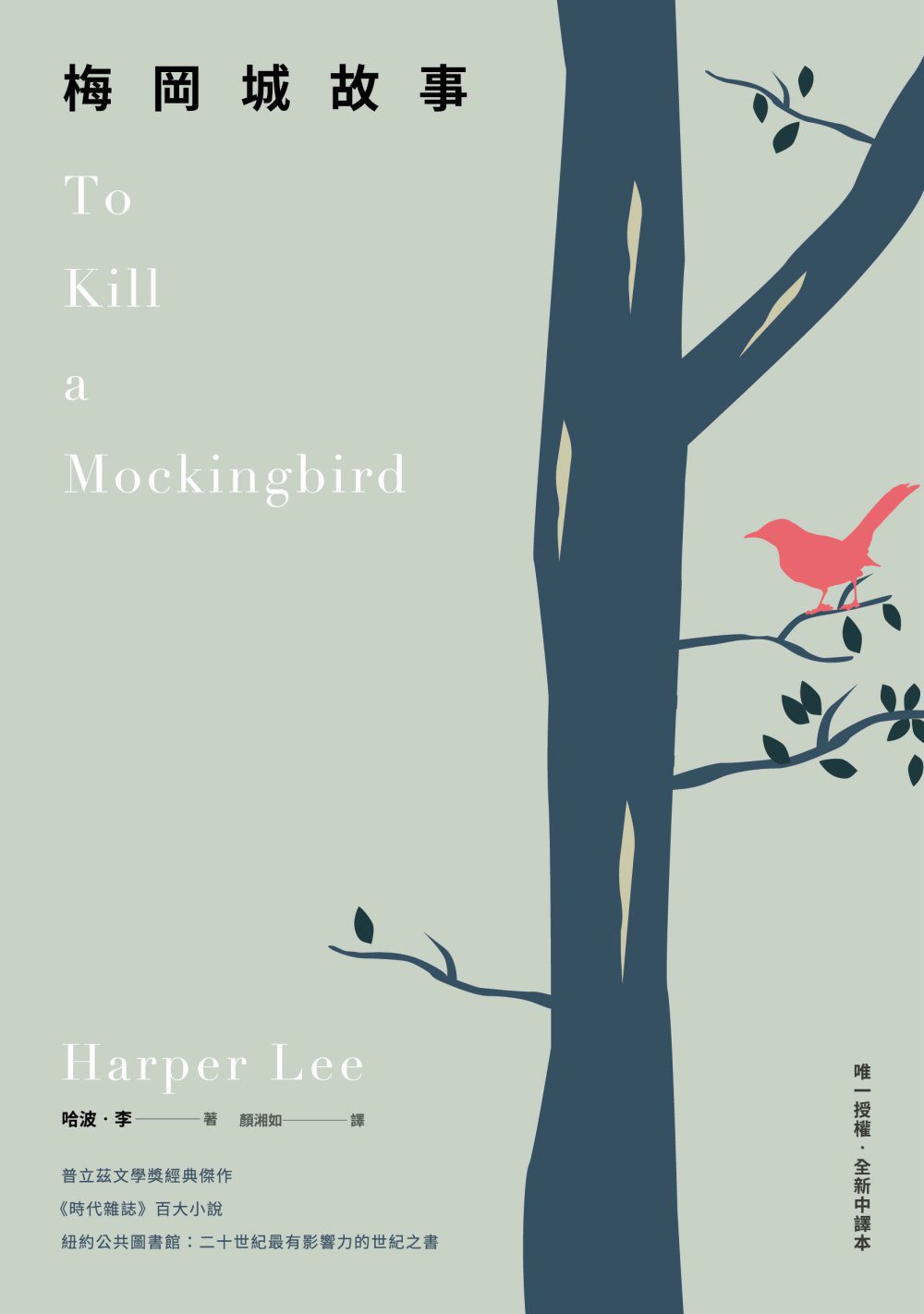序
維金尼亞•吳爾芙的寫作藝術
吳爾芙夫人(Virginia Woolf)的作品,是以文字形成的一種奇蹟。活潑、輕俏、空靈、閃著智慧的光澤,她的風格本身,就是一種美麗的存在。
我特別愛好的,是那篇千古奇文《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評者謂其性質雖屬論文,效果不啻小說,是她的最好作品之一。
這篇傑作,原是她兩篇講演稿拼合剪接而成的。我們誰有幸曾聽到這麼生動的講詞!富有靈智的啟示,哲理的探討,藝術的品評,更不乏一些極其綺麗的寫景抒情的片段,打開這本書的篇頁,你會發現到處有「美」在迸發著,使你目不暇給。
企圖讚美這一篇作品,我曾擲筆嘆息了多少次,面對著這樣一篇妙文,我深感到自己字彙的貧乏,竟找不出妥當的字眼來形容它,勉強說來,這篇文章像是水晶般的透明,波浪般的動蕩,春日園地般的色彩繽紛,秋夜星空般的炫人眼目。最妙的是:上一個句子給你的鮮明印象,你還未來得及給予適當的反應,接著在下一句中,她又推出一個更繁複神奇的,當你正在想借了其他句子的幫助,找到它的詮釋時,而她那枝筆卻又輕盈而俏皮的溜走了。例如在本書的一段的末尾她剛剛說到:
「所有的人都睡著了,縱橫偃臥在那裡,啞子一般,牛橋街上,杳無人跡,即或是一隻推曳那旅社門的手都看不到—連旅社裡擦皮鞋的都不曾有一個等我回來,給我照著亮,送我回到我住的房間,夜是這般的深沉……」
緊接著,在下面的一章中,她又是這樣的開頭了:
「現在,就請你們跟我到另一個地方去,樹葉仍然在落著,但是這不是在牛橋而是在倫敦了……」
她的文字就是這般的跳擲,像一股亂流急湍,像一陣沒有定向的風……她有她自己的邏輯路線,而我們常是望塵莫及。
多少年來,我對吳爾芙夫人的文章有一種深摯的偏愛,但是,她文字的魅力,她處理文字的祕訣,在我卻是一個難解的謎。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說,她有著比我們豐富的想像力,同時,她會挑選那極具實感的,表現顏色、形狀、感覺的字眼,來狀擬她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想像,似是「明說」卻是暗喻,為她的文字增加了一種難以言喻的美妙處。譬如,她在《自己的房間》中的一段:
「為了或此或彼的理由,女子比男子貧窮。也許,現在乾脆不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了,還是接受一些意見倒還好點,這些意見熱得像火山熔岩,黯淡得像洗碗的泔水。」
再如另一段:
「小說像是一面蛛網,它的尖角是黏附於人生上面。雖然也許永遠是輕輕的黏附著,幾乎是目力所不能見。例如,莎翁的戲劇就宛如四下裡無著無落的,獨自家懸吊在那兒。但是,等到那面網扯歪,邊緣?住,當中也撕壞了,我們就會明白,這些網不是那些視之無形的小蟲在空中織成的,而是一些受著痛苦的煎熬的人的作品,……」
又如:
「想到我的那一點兒天才—一丁點兒,不過,在真有這一點點的人總是可寶貴的—任它埋沒實在罪過。但是它在逐漸消滅,而我自己呢,我的靈魂亦隨之而逐漸消滅。所有這種種想法成為一種腐蝕,蝕盡春天花朵,蝕盡樹木的心子……」
她的幻想,瑰奇的幻想,波詭雲譎的幻想,和她的想像,是她彩筆上的雙翼,對它,我們只有嘆服的分兒,如下面的一段,她是在寫景,但那不是寫大地上的景色,卻是寫她心靈中的景色……
「我幻想,紫丁香的花朵顫搖在墻垣上,黃色的蝶兒張張皇皇地飛過來又飛過去,花蕊上的粉,飄揚在空際,一陣不知自哪個方向吹來的風,吹動了嫩葉,一股銀灰閃爍在空中。那正是日光與燈光交接的時刻,各種色彩在加深了,玻璃窗正在燃燒著,l紫金黃,像是一顆容易激動的心在跳躍!」
妙極了!「黃色的蝶兒張張皇皇的飛過來又飛過去」,整個的形容出那一雙薄得可憐的輕巧小翅子在風中捕閃!落日的光耀與燈光交映,那光影竟像是「一顆容易激動的心在跳躍」!我幾乎是心跳著讀完了她的這幾句(別忘了這是她的幻想!)沒有辦法,我只有托出王國維那句老話來讚美她一番:「寫景如此,方為不隔!」她分明將自己的情緒注入在景物裡,自然界裡的一切,都有著她的脈息!她的心中,佈列著奇景。
像她這樣的文章,實在是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奇文!支持著她那一枝神奇的筆的,原是她那一顆多感的心靈,也就憑了她這顆多感而又敏感的心靈,她才寫了那一部同樣美妙的散文體的小說《茀萊西》(Flush),將勃朗寧夫人—女詩人伊麗莎白的一隻小狗寫得活靈活現,吠叫跳鬧於紙上,天才的另一方面就是那格外豐富的想像,想像為我們擴大了同鳴共感的範圍,她的那部《茀萊西》推翻了若干年來影響作者們甚大的一句話:「只有自己實際經驗到的才寫得好!」天才者的想像,原正好用來彌補經驗上的不足!
當真,我不知如何形容吳爾芙夫人那通明如藍冰、燃燒如火焰、充滿了冷靜的智慧與澎湃的熱情的文字(她因為富於智慧,故精於分析,她因富有熱情,故對人間種種充滿了悲憫。)也許,說明她文章的特徵,還得借用她自己的話:
「……於是,我就讀一兩句來試試,我迅即發現其中有點什麼不對勁,文字間的銜接,似是受了阻礙,有點東西撕得碎裂了,有點東西戳破了,這兒一個字,那兒一個字,在我的眼前像火炬似的閃耀……我覺得她(指那個虛擬的作者瑪琍.卡米愷)宛如一個人在划著一根總是不燃的火柴……讀這本書,好像坐了一隻無甲板的船,浮泛於茫然的大海,忽升忽沉,那種簡練與語氣的緊促,分明表現出她在恐懼,或許是懼怕別人批評她愛傷感,否則就是她憶起了人們批評女性文章太綺麗,因而她就有意放進去很多不必要的芒刺……」
還有:
「我自語:我幾乎不能肯定的說瑪琍.卡米愷是在逗著我們玩,因為我覺得好像坐在那種玩遊戲般的火車中,我們滿心以為車子要溜下去了,誰知它卻驀的轉了個方向衝著上面開來了。瑪琍是在任意改變著事情的自然發展的情形,首先她破壞了文句,現在卻又來破壞了故事的進展,不要緊,只要她的目的是在建設而不是在破壞,她完全可以這麼做。」
在這兩段文字中,她假托有一個名叫瑪琍.卡米愷的女作者,且對其文字加以品評,實際上,這本是吳爾芙夫人的「夫子自道」,那位不見經傳的女士,代表的正是她自己,這兩段話中有幾句值得我們特別予以注意:「不然的話,就是她憶起了人們批評女性的文章太綺麗,因而她就有意的加進去很多不必要的芒刺……」以及「假如她的目的是在建設而不是在破壞,她完全可以這麼做。」
當真,吳爾芙夫人是「破壞了文句」且「破壞了故事的進展」的人,她厭棄一些舊有的,她有意來創造,所以固有的句法在她的手中破壞了,故事的一貫的發展的公式,也在她的手中破壞了,正因她的目的在於建設而不在破壞,我們覺得她「完全可以這麼做」。
最後,我想起了法國羅愛伊夫人的兩個文句,我覺得正好來形容吳爾芙夫人的文字:
「宛如一股綺風,在兩行石竹中穿過。」那綺風是帶著濃郁的紫羅蘭的芳馥的,何時你打開她的書,就會感覺到它的吹息。
張秀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