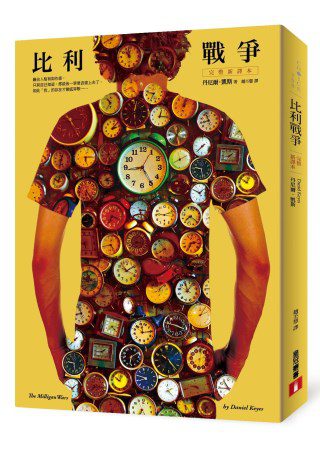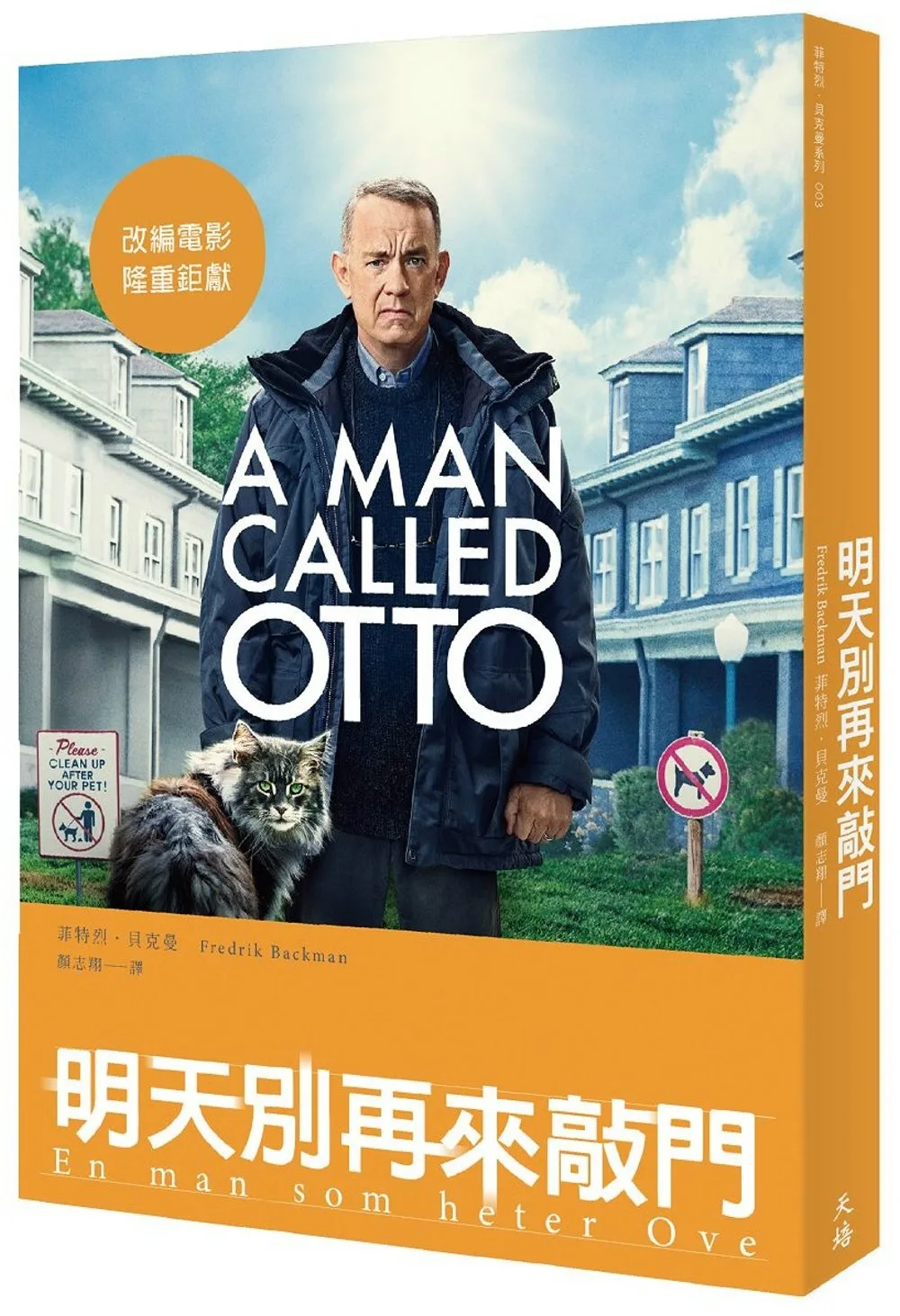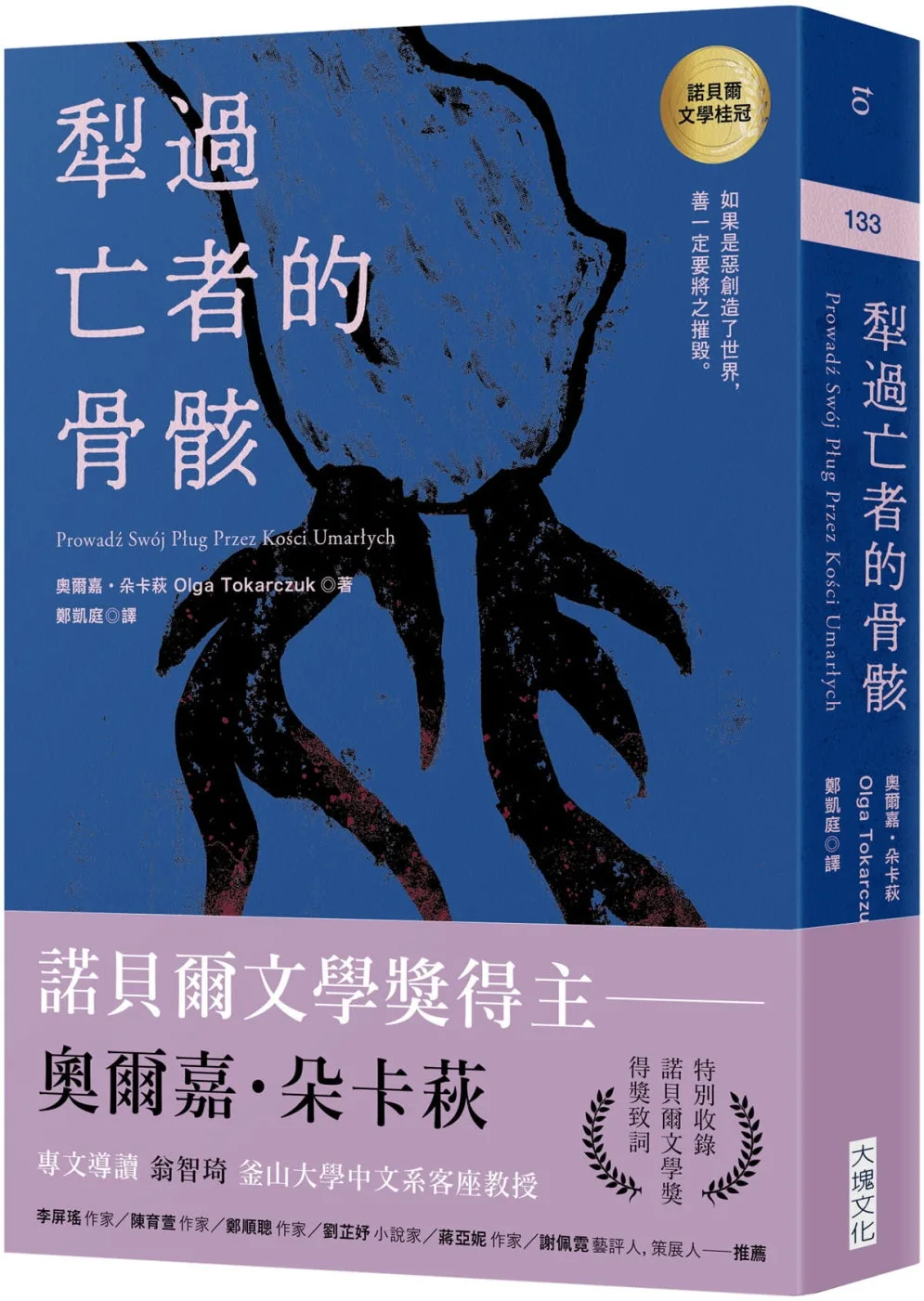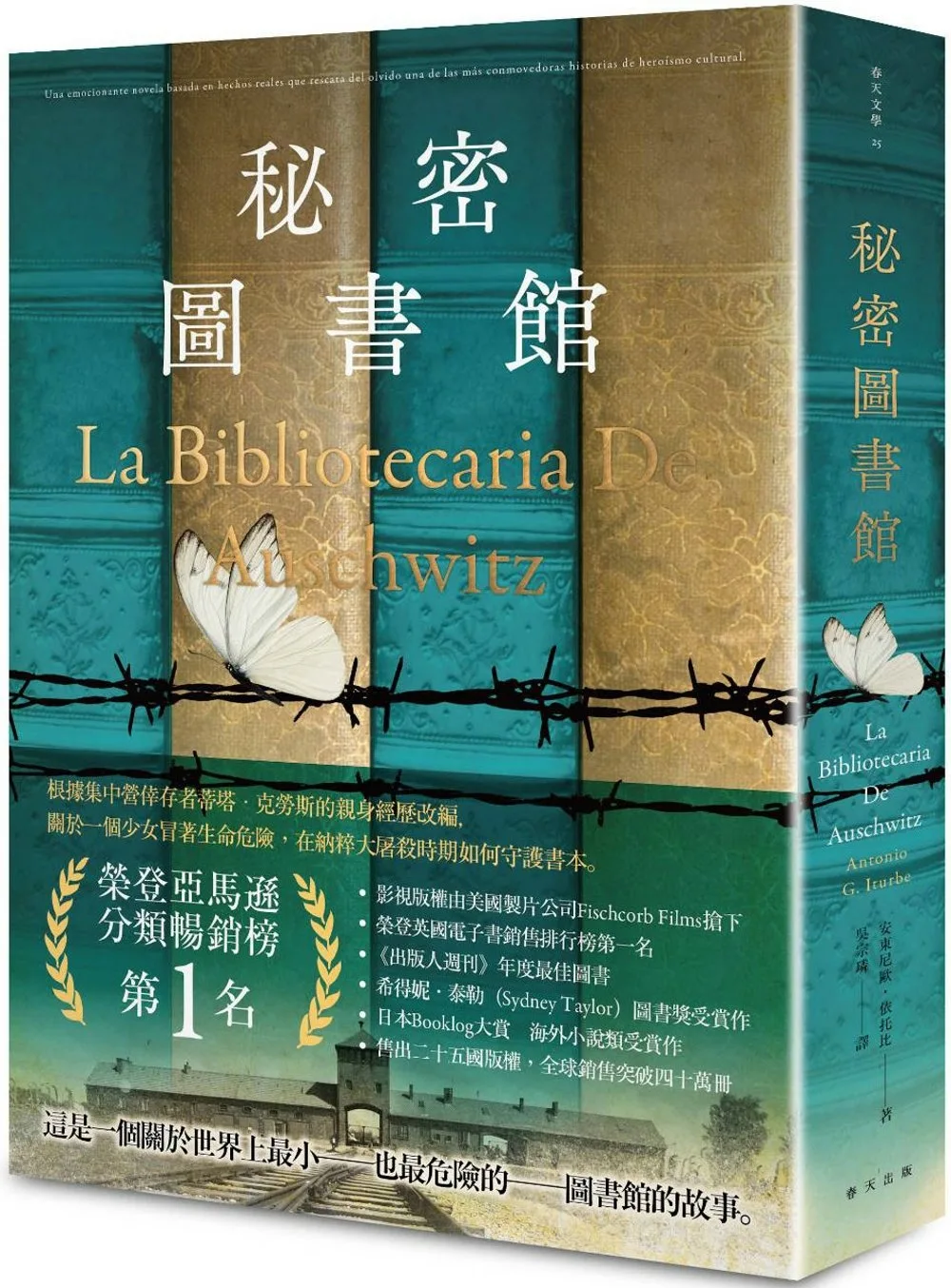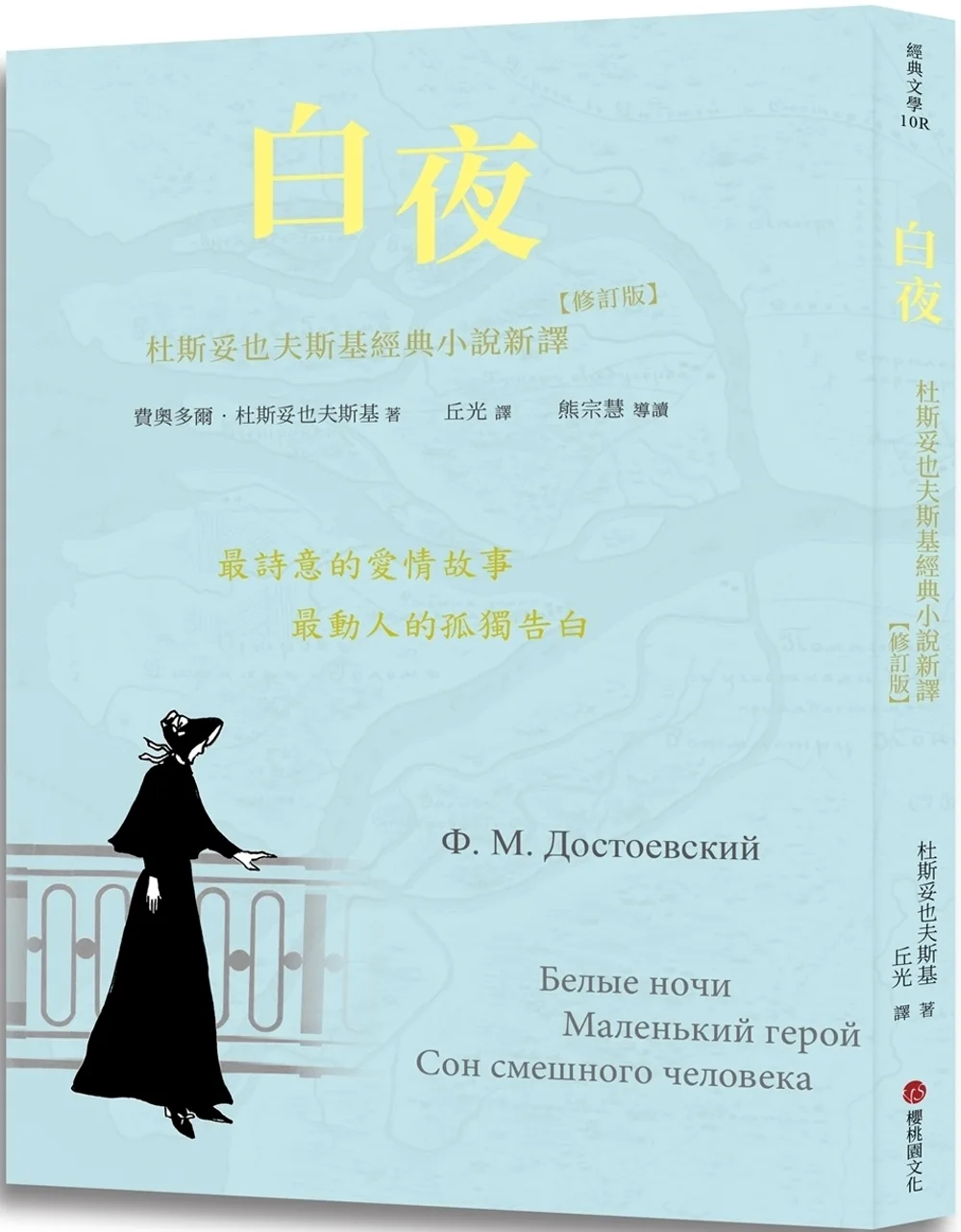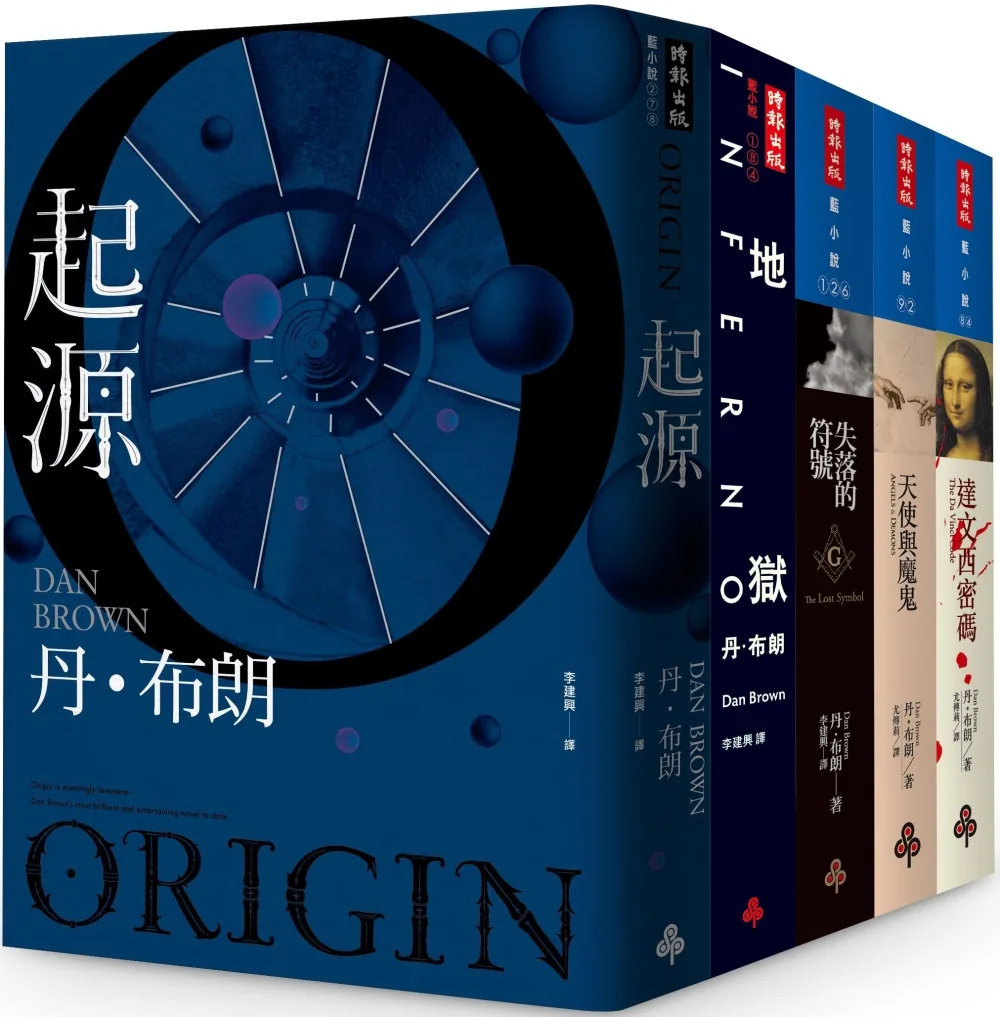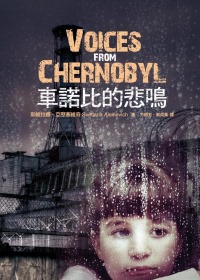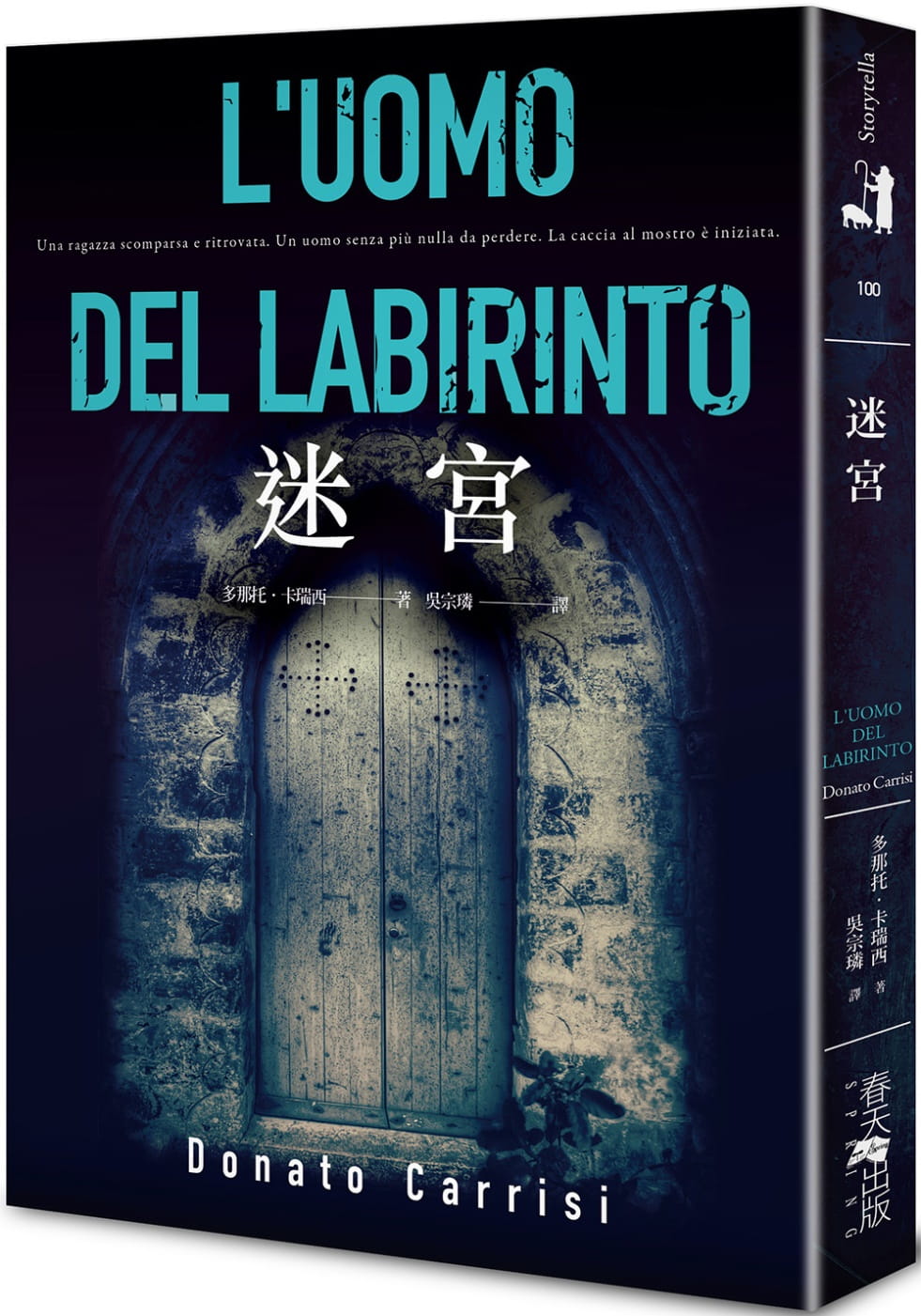導讀
百年孤寂,千年之愛
多年以前,出版社主編問我:「願不願意、有沒有可能用西班牙文將《百年孤寂》新譯重新出版?」面對這樣的詢問,我說:「除非原來的中譯本不再版,除非取得馬奎斯本人和經紀人的授權,除非譯者中西文底蘊厚度均足,原來的中譯並非不好,原著的精髓在於西班牙文的多重語意、發音和繁複的文化問題,新譯要完全超越更臻完美,未必是不可能的任務,但絕對是頂尖的挑戰。」當時,我以為《百年孤寂》中譯在這塊土地上不會再有第二次機會。
曾經,馬奎斯和他的經紀人卡門.巴爾賽(Carmen Barcells)為了向超過千萬讀者百萬冊銷售的中文盜版抗議,已經堅持多年拒絕馬奎斯所有作品的中文版授權,形同禁運的制裁。我以為改編馬奎斯的名言「給我一個親人,我就可以撼動你的心扉」(《預知死亡紀事》:「給我一個偏見,我就可以撼動這個世界」)、透過私人遊說或親情攻勢,可以有些效果,多次長途電話到哥倫比亞跟馬奎斯的姪女瑪格麗達(Margarita)商談,也和卡門.巴爾賽磨耐心,都是無疾而終,畢竟我不是出版社,亦非版權代理商。
曾經,比馬奎斯小二十歲的弟弟艾利希歐(Eligio Garcia Marquez ,一九四七∼二○○一)誤以為我是《百年孤寂》中譯的譯者,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寄給我一份問卷,提問幾個問題: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閱讀《百年孤寂》?現在如何看待這本小說?何時成為一位譯者?閱讀時是否發現與其他作品不同或相似的特點?如何翻譯這部小說?意譯?改寫?直譯?是否遇到語言及文化上的障礙?要解決這些問題,是否親自向作家詢問?或是參考其他譯本?花多少時間翻譯?再版時是否重新校訂修正?閱讀過哪些拉美文學作品?是否翻譯過其他小說?讀過哪些馬奎斯的作品?中譯印刷多少本?書的大小設計是否和本地作家或外國作家一樣規格?讀者接受度如何?評論如何看待?是否對貴國的文學創作產生影響?在馬奎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這麼多年來,《百年孤寂》在貴國的評價與地位如何?最後,還特別手寫,說我的西文名字跟他的母親一樣:LUISA: como mi madre, Luisa Santiaga.
艾利希歐.賈西亞.馬奎斯二○○一年因腦瘤過世,這一年,他出版了厚達六百三十頁的《解密梅賈德斯》(Tras las claves de Melquiades),彙整解讀他所研究探詢到的《百年孤寂》的創作、翻譯與閱讀史,以及其全球影響力。當時距離馬奎斯得諾貝爾文學獎近二十年,而如今已過三十五個寒暑,而且二○一七年是《百年孤寂》出版五十週年紀念了。馬奎斯和卡門.巴爾賽也相繼於二○一四年、二○一五年駕鶴西歸。最重要的是�事──他們在離去前,做了最關鍵的決定(雖以極高鉅額授權費):二○一一年《百年孤寂》的中文簡體版經正式授權出版了;更可喜的是,五十週年慶的今天,臺灣皇冠也出版了我們自己的版本。
回應一九九八年艾利希歐詢問我的問題,我認為二十年後的今天更適合回答。文學若要論「文以載道」的社會責任,那麼翻譯就是回應社會文化的「某時、某地、某世代、某文本、某譯本」的需求。華文世界四、五、六年級生的閱讀歷程各有《百年孤寂》某個譯本的集體記憶,今天看到正式授權的中譯本面世,我們的態度是正面的,是雀躍的,是積極的,是勇敢的。譯者不必為了「不趨同」而「求異」,也無需顧慮布魯姆(Harold Bloom)所謂「影響的焦慮」而另闢蹊徑。這是《百年孤寂》從盜版到正式授權,從簡體到正體中文,從英文到西班牙文原文翻譯的進程與努力,迎迓另一個閱讀世代的挑戰,繼續淬煉作品的韌度與質地,也是學者、作家、譯者面對社會變遷再現思維與反省能力,同時考驗讀者的知性及智性涵養,從而展現作品無國界永恆不朽的貢獻與價值。
魔幻寫實風潮和《百年孤寂》的巔峰從上個世紀一九八○年代開始,在全球風行草偃,識者應風披靡,成為拉丁美洲新小說的翹楚,成為後殖民研究的文本典範,是拉丁美洲身分與文化認同的導航,是所有想要書寫家庭史、國家史亟思的尺度和規模,更是所有想要成為小說家的人必讀作品,說它是二十世紀文學的《聖經》也不為過。馬奎斯和《百年孤寂》在世界文壇煜煜輝赫,成就其經典地位,誠如《馬奎斯的一生》作者傑拉德.馬汀所言,他是「新的塞萬提斯」。又如,與他同為拉丁美洲文學爆炸時期的尤薩(Mario Vargas Llosa)獲得二○一○年諾貝爾文學獎,證明了他們這個世代的文學的璀璨輝煌與豐厚實力;一九八○至一九九○年代以馬奎斯為宗師,說出「原來小說可以這樣寫」的莫言,贏得了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中國、臺灣許多作家,前仆後繼擬仿效尤者亦不遑多讓,應驗了艾利希歐所說的《百年孤寂》對外國文學的影響。《百年孤寂》連結魔幻寫實三十年(一九八二∼二○一二),從西方到東方,從拉丁美洲到華文世界,華文創作受到《百年孤寂》直接的影響堪稱國際文壇的顯例,這是跨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一個最耀眼的試金石,也是里程碑。
《百年孤寂》的磅礡故事,馬奎斯的寫作氣勢,兩者對世界文壇的貢獻、在歷史的定位,猶如詩仙李白登黃鶴樓讚歎美景,卻無法跳脫其一氣貫注的意境而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李白擱筆,他日另尋契機與靈感仿〈黃鶴樓〉寫下〈登金陵鳳凰臺〉。後馬奎斯世代,被稱作所謂的「馬康多世代」也將有李白的讚嘆與喟嘆,不會再有〈黃鶴樓〉,但一定還有許多另類的鳳凰臺。一如馬奎斯一九五五年閱讀了墨西哥小說家魯佛的《佩德羅.巴拉莫》(Pedro Paramo)後,突破創作瓶頸,潛心埋首十二年,寫出了《百年孤寂》。二○○七年,為了慶祝《百年孤寂》出版四十週年,西班牙皇家學院(RAE)聯合拉丁美洲國家共二十二個西班牙語研究院出版《百年孤寂》紀念版,結集三位院士──尤薩.紀嚴(Claudio Guillen),前院長賈西亞.龔恰(Victor Garcia de la Concha),兩位馬奎斯摯友、名小說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和穆迪斯(Alvaro Mutis)共五篇專論,以及四位拉丁美洲學者,其中一位是今年的塞萬提斯文學獎得主,前尼加拉瓜副總統拉米瑞茲(Sergio Ramirez),分別撰文析論馬奎斯與《百年孤寂》對拉丁美洲文學的影響。
比較文學理論大師紀嚴分析《百年孤寂》的「文學性」(literariedad),他指出馬奎斯結合歷史性、故事性和敘事體成一體;誇飾的敘述中又帶有獨特的精確度;馬康多的故事延展環繞在兩個向度:重複性和寓言�預言,也就是在循環的時間和未來的時間中鋪陳。儘管人物眾多,世代繁雜,波恩地亞家族的個性,對家族的情感、記憶和希望在時空的變換中,始終一致。賈西亞.龔恰從詩性的角度審視《百年孤寂》,舉出其時空的象徵──一種無限前進延伸的阿列夫(aleph)迷宮,小說人物處於一種二元對立的情感糾結:隨性 VS. 算計,暴力 VS. 溫柔,靜謐 VS. 躁動,搏鬥 VS. 擁抱……陷入永恆的孤寂。馬奎斯兩位好友,穆迪斯認為馬奎斯為拉丁美洲文學立下典範和典律,馬康多將會變成所有讀者情感與知識匯聚交集的地方。富恩特斯則以「美洲的名字」封號向馬奎斯和《百年孤寂》致敬,美洲的《吉訶德》(唐吉訶德)已然誕生。
身為爆炸文學的一員,身為研究馬奎斯最透徹的作家,尤薩的論述深且長。他從博士論文《馬奎斯:弒神的故事》(Garcia Ma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 ,一九七一)便認為馬奎斯的小說是在解構神話,顛覆神蹟,翻轉現實,用神話的奇幻鋪陳日常生活的真實,又以傳統迷信混雜人民心中堅信不疑的宗教信仰,詰問神的創造力。質言之,馬奎斯刻意將十五世紀歐洲人發現新大陸的種種奇聞軼�異事和誇飾書寫挪移到二十世紀的文本創作,以拉丁美洲的現實反諷歐美聲稱的魔幻。例如,哥倫布的《日記》(一四九三)、征討墨西哥的西班牙征服者艾爾南.科特斯(Hernan Cortes,一四八五∼一五四七)的《書信報告》(Cartas de relacion ,一五二二),跟著麥哲倫環遊世界的義大利航海家畢加菲塔(Antonio Pigafetta ,一四八○∼一五三四)的《環遊世界首航記》(Primo viaggi in torno al mondo),或多或少都帶著誇飾怪誕的口吻敘述在新大陸的所見所聞(「豬隻的肚臍長在背部;一些沒有腳掌的鳥兒,雌鳥趴在公鳥的背部孵蛋;沒有舌頭的鵜鶘群聚,尖嘴長得像湯匙」)。因此,我們可以領略馬奎斯嘲諷殖民旅行紀事的失真。拉米瑞茲的〈真實的捷徑〉也以殖民紀事為主軸,直言馬奎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將殖民敘述的虛構與想像元素植入《百年孤寂》,而「神化」的色彩,猶如《吉訶德》第二部的布局,逐漸淡化而轉入真實情境。尤薩用〈《百年孤寂》:全面的真實,全面的小說〉讚頌馬奎斯和《百年孤寂》。他說:「在我們的時代,文學天才──作品和作家──是深奧晦澀的、小眾的、令人疲憊的,《百年孤寂》是少數的例外,是所有人都可以理解,極度享受的作品。」
《百年孤寂》的「全面」還根植於它呈現一個鮮明的個體的故事,又同時是集體的歷史;小說素材完整,因為它講述一個烏托邦、一個封閉的世界,從個人、家族、社會到國家,從它的起源到它的毀滅;敘述技巧全面:從真實、想像、神話傳說、奇蹟到魔幻,馬奎斯筆鋒游刃有餘。例如,梅賈德斯透過神秘的技巧或知識變出花樣的能力;美人蕾梅蒂絲(Remedios)的體與魂隨著床單飛上天,這是與宗教信仰相關的神奇;流浪的猶太人(Judio Errante)引起鳥類暴斃的敘述屬於神話傳說;維克多.于格斯(Victor Hugues)的「私掠船幽靈,船帆被陰風撕碎,船桅被海蟑螂蛀蝕」不是魔幻,也不是信仰,是源於法國的歷史,在卡本迪爾(Alejo Carpentier)的小說《啟蒙世紀》(El siglo de las luces)中被重塑為神話傳說。此外,屬於客觀的真實,略帶點誇飾的筆觸而令人有前所未聞的驚奇的事蹟,就可以歸為奇幻的範疇,這應是《百年孤寂》裏爬梳最多的情節。例如,生出有豬尾巴的後代;忘在櫃子裡許久的空瓶子變得太重;有個鍋子裡的水沒有火卻沸騰;失眠症的瘟疫;動物園妓院……等等。馬奎斯對文字語彙的推敲也相當細緻,許多的形容詞讓文本的氛圍介於奇蹟與魔幻之間,例如,「《聖經》中的狂暴颶風吹起,把馬康多變成塵埃和殘磚碎瓦的可怕漩渦」;「當他們一拿走發黃的紙捲,有一股神力(筆者按:天使的力氣)將他們舉起,讓他們浮在半空」。這些分析有助對魔幻寫實書寫的解密與解套。
二○一七年二月我在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哈利.蘭森中心(Harry Ransom Center)搜集馬奎斯生平的手稿、圖像、書信……等各種文獻資料時,小心翼翼呵護著《百年孤寂》的初稿、二校、三校……付梓後的修訂稿,馬奎斯的眉批與鉛筆筆觸,他那臺跟著作品也成為經典的打字機,各種活動數百張照片,觸摸之間,心電川流,頓時彷彿領悟了作家苦心孤詣的一生。想到他在自傳《活著是為了說故事》(Vivir para contarla)寫到「生命不只是一個人活過的歲月而已,而是他用什麼方法記住它,又如何將它訴說出來」。馬奎斯用《百年孤寂》記住他的生命,用《百年孤寂》訴說出來,成為讀者、文學史上的千年之愛。
臺大外文系教授兼國際長•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 ?
張淑英
二○一七年十二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