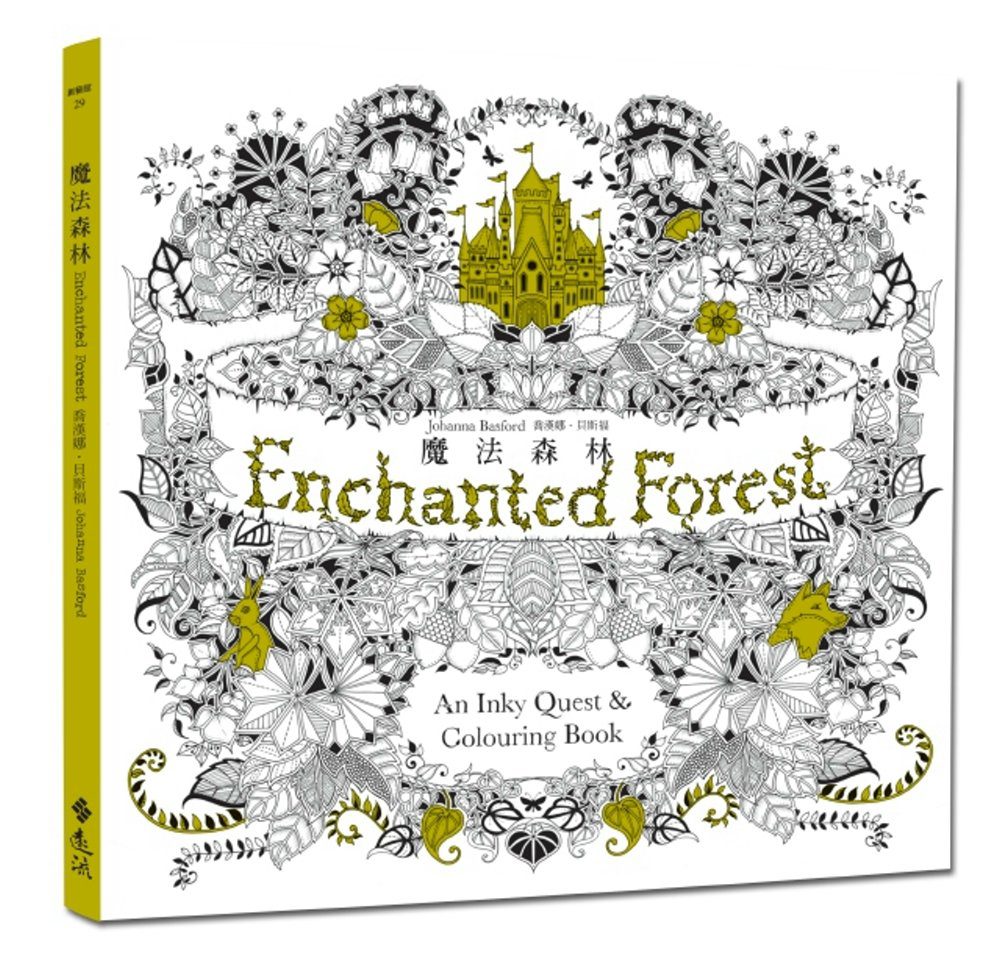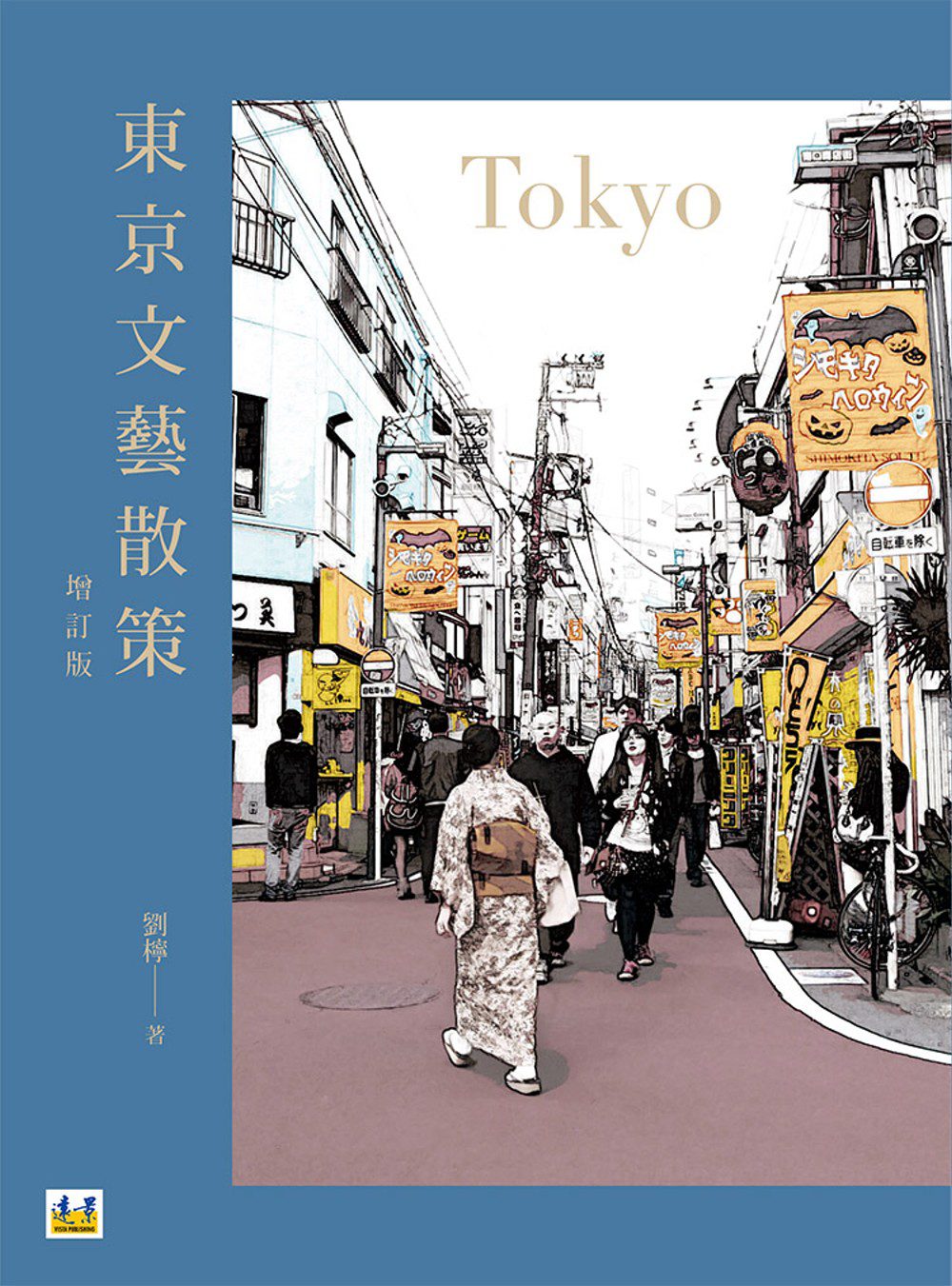序
落花時節讀華章
櫻花又落了。
魯迅也見過的上野櫻花「確也像緋紅的輕雲」,而今花下更不缺走向了世界的中國人。有成群結隊的遊客,他們看花也看人;有留學生聚在「噴雲吹霧花無數」的櫻樹下喝酒,頗有點「痛飲黃龍府」的氣勢,但因為早沒了辮子油光可鑑,即便把脖子扭幾扭也安能辨我是老外了。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我一直不明白魯迅說此話的來由,而劉檸是喜愛東京的。他說:「對我而言,東京則是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是我在北京之外,唯一居住、生活逾三年的城市。」有了這句話,不消說,他就得寫出東京的好來。他甚至說「本世紀初,哺育了周氏兄弟的神保町書店街,今兒哺育著毛毛」,說得也並非不知深淺。若沒有從神保町等處大大小小書店購讀的那些書,被書們哺育,恐怕他不會寫、也寫不來這一本《東京文藝散策》。
大概這個世界上我們中國人最恣意敲打的,非日本莫屬。因為有傳給它漢字文化的恩德,有被它侵略過的冤屈,還有自以為打敗它的驕傲,況且它那麼小,有什麼呀。不管出於什麼樣的情懷或情結,而今寫日本可謂多矣,既有作家論客學者洋洋灑灑地著書立說,又有哈日反日以及貌似廣場舞大媽的各色人等在網上暢所欲言,但我偏愛讀這個暱稱毛毛的劉檸。說老實話,本人有點古,不喜歡當下人們自以為有趣的怪詞流行語,可他很愛用,我卻不反感,因為他自有一份真誠在其中。囑我作序,畏之如虎也不能峻拒或婉拒,只好樹起「一升瓶」清酒,先浮幾大白,這才有了點「筆禿幸趁酒熟時」的意思(龔自珍《己亥雜詩》之一:閉門三日了何事,題圖祝壽諛人詩;雙文單筆記序偈,筆禿幸趁酒熟時)。況且「屢讀屢叫絕,輒打案浮一大白」,也得備好酒。
劉檸不止於讀書,還走路。在我的印象裡,旅遊是遠行,去哪裡看看什麼,很有點隆重,而散步多是在近處走走,優哉游哉,卻更帶有思考的形象。劉檸是思考者。即便在文藝中散步,思考也油然超出文藝的範疇。每次見到他,我都不禁想起黃遵憲的詩句。那是一八七七年,距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爆發,日本還有十多年的近代化時間,黃遵憲隨所謂兩千年友好以來頭一遭駐日的使團渡海,數日後寫下「此土此民成此國,有人盡日倚欄思」,所思當然是吾土吾民及吾國。百餘年過去,又有劉檸倚欄思,或許是「東方的悲哀」吧。
所謂「散步」,文學的或文藝的,日本這類散文很發達。早在一九五一年野田宇太郎就開始在廢墟的東京散起步來,探訪作家的足跡、作品的舞臺,題為「新東京文學散步」。起初叫「文學性散步」,似乎太硬性,乾脆就叫做「文學散步」。有人不願用「舊日軍」的說法,因為戰敗後日本只有自衛隊,沒有軍隊,沒有現任總理大臣安倍晉三公言的「我軍」,所以無所謂新舊。野田的文學散步有別於永井荷風的「東京散策」。永井趿拉著木屐在東京四下裡尋找的是惜乎逝去的江戶,而野田要發現「新東京」,發現希望。他記述與東京有關的文學遺跡,但筆下的東京面貌是現實的。《新東京文學散步》(續寫東京,結集為《東京文學散步》)暢銷,於是他繼續走下去,走遍日本,一九七七年出齊的《野田宇太郎文學散步》有二十六卷之多。
文學有跡可尋,或許日本文學是世界上最可以畫出地圖來的文學。這可能與日本文學最為獨特的「描寫真實」的私小說有關。倘若只敢把場景設定在臨江市靠山屯之類,以免對號入座,讀了也無從尋訪。劉檸去首都圈(東京及其周邊)尋訪了,背著雙肩包,和一肚子學識,尋訪文學,尋訪文藝。永井荷風的東京,以及新井一二三的中央線,福田和也的各種黃昏,早已是他們感情記憶中的往昔風景,我們看不到,似乎也無須再替他們演義。劉檸說:「時光倏忽,一晃小二十年過去了。過去因工作的關係,隔三差五飛來飛去,直飛到令人反胃的外埠城市,如今都成了漸行漸遠、溫暖醇美的回憶。正如我已不復是昨日之我,那些城市的變貌也早已溢出了我的想像。好也好,壞也好,這就是現實,只能接受。」那麼,他的散步要「散」出些什麼來呢?一個中國人,不遠萬里到外國散步,自然是睜著一雙比較的眼睛,外界的日本與內心的祖國在眼中交映,有重影,有錯位,字裡行間透露著他的思考,明白人自能會心一笑。從思考與批評來說,或許這本書更類似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街道行》。
《街道行》與其說是紀行,不如說是「散步」,司馬藉考察日本及其它國家的歷史、風俗暢談他獨到的文明觀。自一九七一年起筆,至一九九六年去世為止,整整在《週刊朝日》上連載二十五年,結集四十三冊。日本人的持之以恆常令我感嘆不已。這種恆,不單是作家的毅力,也是出版的操守。似乎我們的出版更慣於游擊戰,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文化的積累就顯得駁雜,沒人家精細。劉檸也寫到日本出版(出版社、書店)。特別是近代以降,文學與出版密不可分,文學就是書。他寫道:「對日本社會來說,支撐東洋文化軟實力的支柱,既不是東大、慶應、早稻田,也不是東映、松竹、寶塚,而是神保町。這塊以東西向的靖國通和南北向的白山通為『龍骨』的『飛地』,麇集了約一百七、八十家舊書店和三、四十家新書店及眾多的出版社、中盤商、製本屋、文具店,藏書量不下於一千萬冊,儼然一個印刷活字城。」他喜愛神保町,不僅「泡透了」,而且「穿越」到魯迅、周作人,神保町也為中國文化的近代化做出過貢獻。當今出版遭網路新媒體擠壓,可說是科學進步、社會發展所致,而且出版本身也在給網路充當「二鬼子」,例如把作品上網不另付稿酬。而網路一旦千金買馬骨,作者們紛紛拋棄小心眼的傳統出版也說不定。最終當然如劉檸所樂觀的,「閱讀本身永遠不會消亡」,讀者無非改變一下閱讀方式罷了。
一寫到淘書,劉檸的眉飛色舞就躍然紙上。我沒有藏書的雅興和恆心,逛書店跟逛花園差不多,買書的價值判斷全在於想不想讀和有沒有用,雖然也欣賞藏書家的書房,像極了精美的私人花園。所以,從未感受過劉檸那種錯失一本書而化作冰雕的遺憾,或者淘到書之後喝酒去的心滿意足。他酷愛日本啤酒。寫道:「從靖國通到水道橋,是一個上行坡道,所訪書肆既多,肩扛手拎,是真正的『北上』。春秋還好,冬夏的話,則異常艱辛。每每好不容易挨到水道橋車站西口時,我都會有虛脫感。此時的唯一選擇,便是踅進車站後面的小巷中,到那間狹長的、燈光昏暗、牆上貼滿了明治、大正年間老海報的Retro(法語,復古的,懷舊的)調居酒屋喝上一杯。端一扎連玻璃容器都被冰鎮得掛著白霜的生啤酒,邊低頭在膝頭摩挲剛買來的舊書的感覺,幾乎是感官性的。」每次遠遠看見他負重走過來的模樣我都忍俊不禁,和他歡聚的老地方是同胞開的酒館,可以放聲說中國話,可以喝他帶來的烈酒,聽他講見聞,令我們這些久居日本的人也耳目一新。真心希望他堅持散步,往深裡說,這是邁開雙腳的文學研究,而對於我們一般讀者來說,他寫出的是富有知識性的散文,況且總是跟讀者站在一邊。對東京叫好,並大談它為什麼好,那是寫論文;不叫好,卻讓讀者不由地叫好,才是好散文。
和劉檸有賞花之約,惜乎今年又錯過時節,花開了,又落了。花期短,太容易錯過。一位日本朋友年年歲歲忙工作,顧不上出門看花,歲歲年年想起來就罵一聲「早洩」。不過,「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每當看見上野等處的櫻花開得風起雲湧,我總會想起魯迅的話,也想起「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這是我被打上的時代烙印。即便其他人,領導新時代的也罷,嘲諷任何時代的也罷,身上的時代烙印是去不掉的。劉檸與我不同代,我已落後於他。這部書稿裡的文章以前零散讀過些,現在他整理成集,並賜我以重讀的機會,聊補以前未見全豹之憾。但我真不會作序,佛頭著糞是不可避免的了。趕上了落花時節,伏案又想起一句「落花時節讀華章」,以此為題,恐怕劉檸就只有苦笑了。好在鳥兒落在佛頭上,著糞,佛依然微笑著。我想,劉檸即使不「點上一支菸」,也要「再繼續寫些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以前為劉檸的大作《穿越想像的異邦──布衣日本散論》寫過幾句話,這是我對他的「定評」,曰:
不是小說家的浪漫遊記,不是近乎鑽牛角尖的學者論文,其特色有三:布衣的立場,散文的廣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見。沒有國人談日本所慣見的幸災樂禍、嘻皮笑臉,對世態人情的關注是熱誠的,對政經及政策的批評充滿了善意。他,自稱一布衣,走筆非遊戲;不忘所來路,更為友邦計;立言有根本,眼界寬無際;穿越想像處,四海皆兄弟。
?
◎李長聲
二○一五年落花時節於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