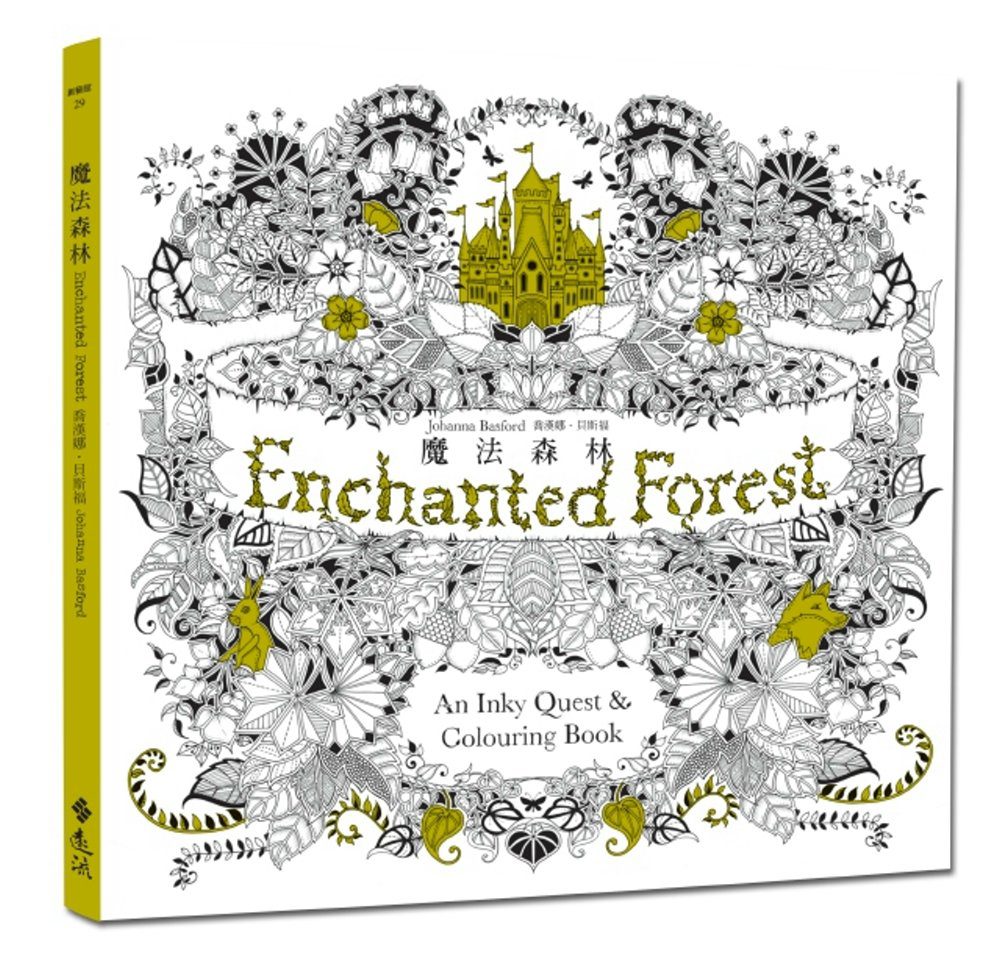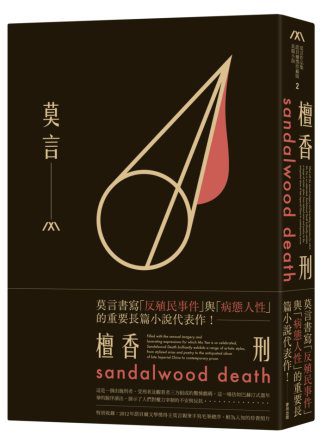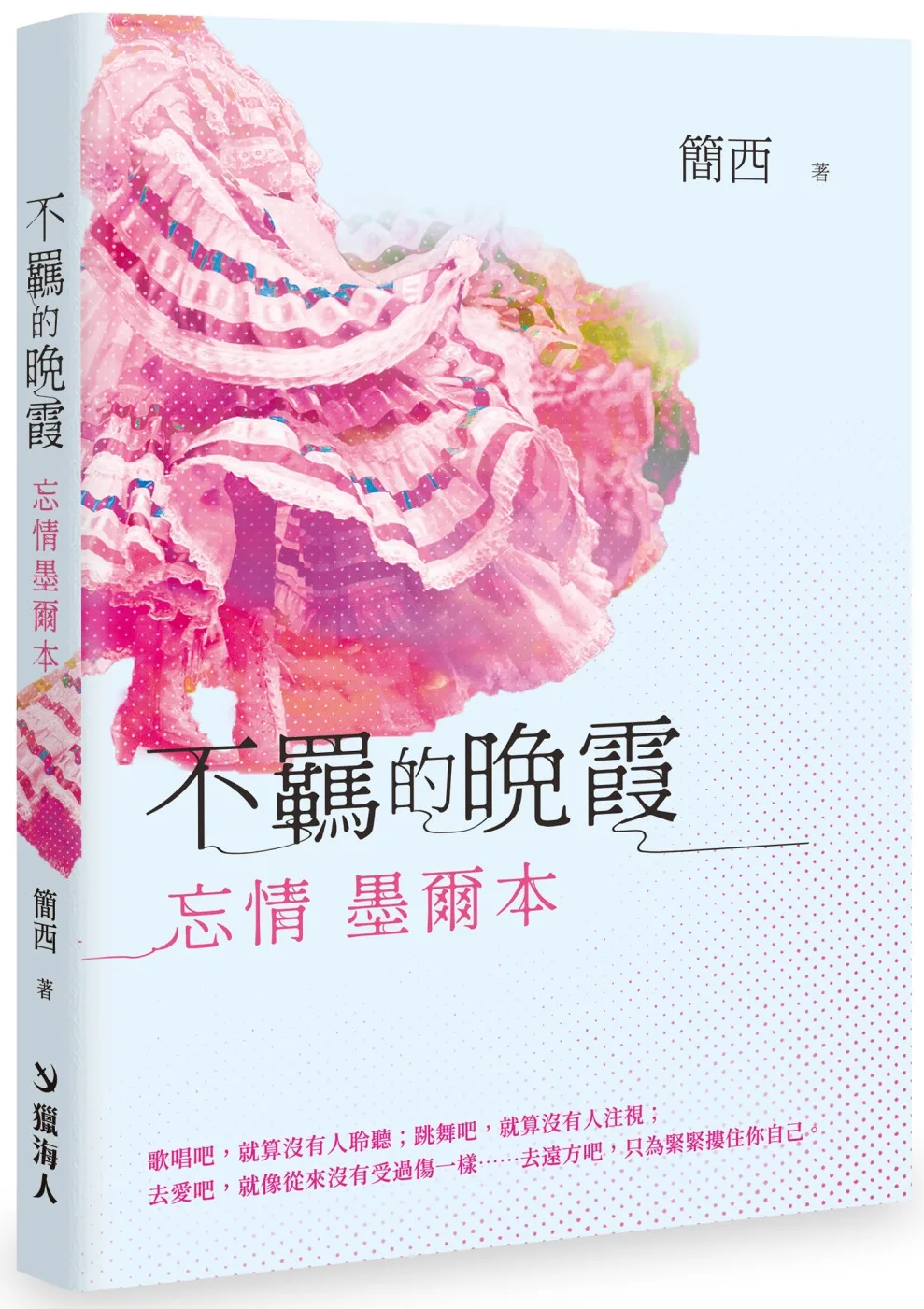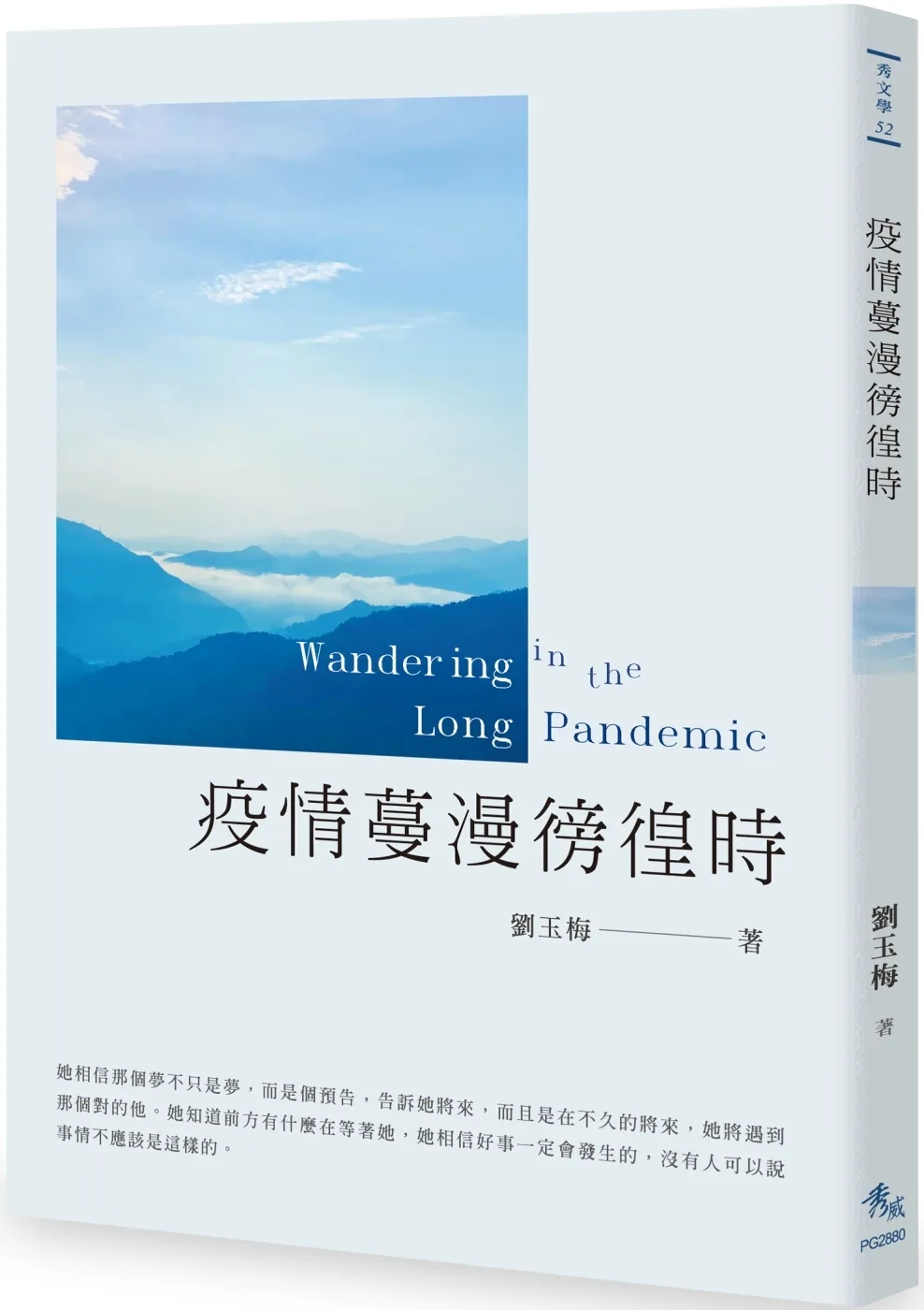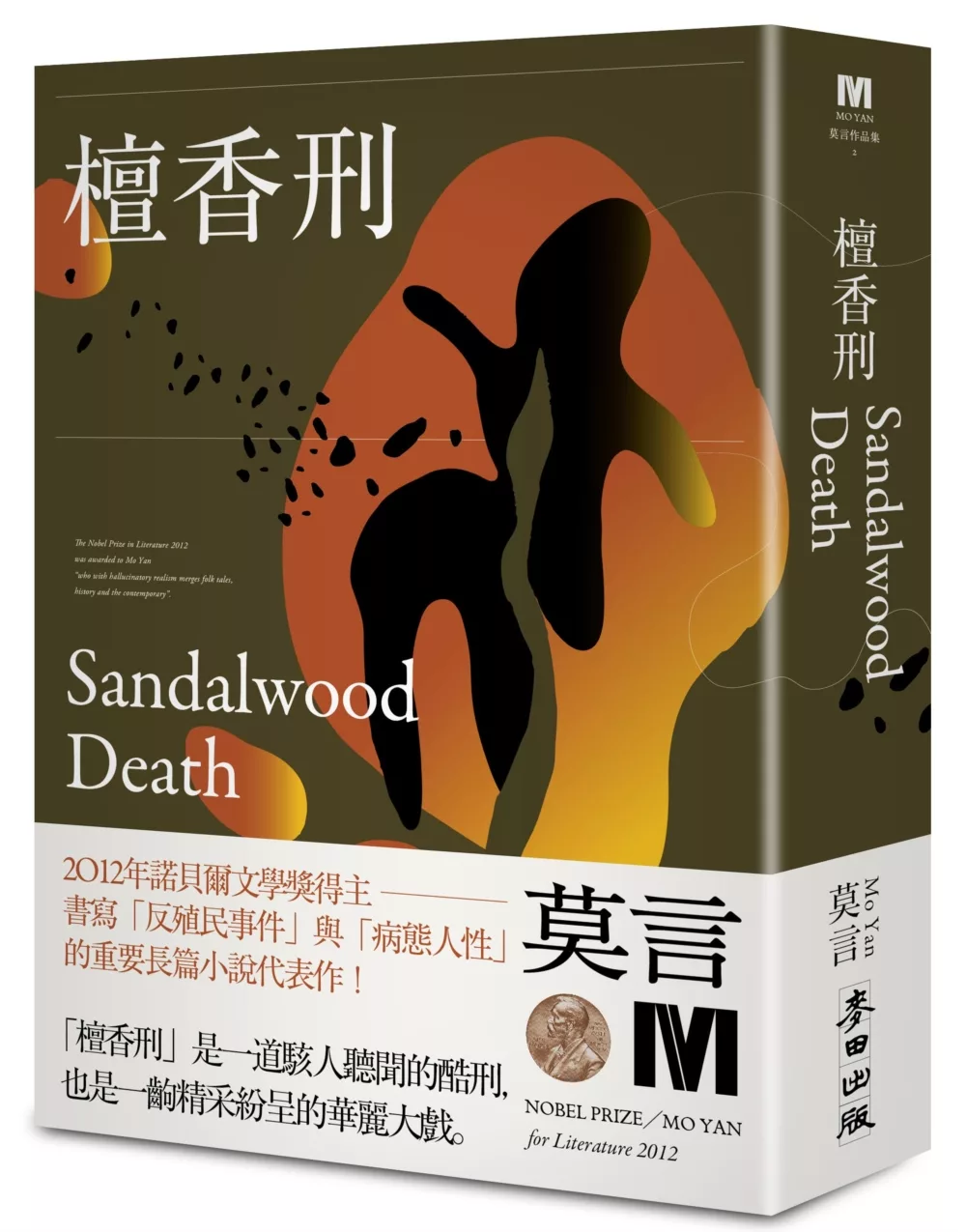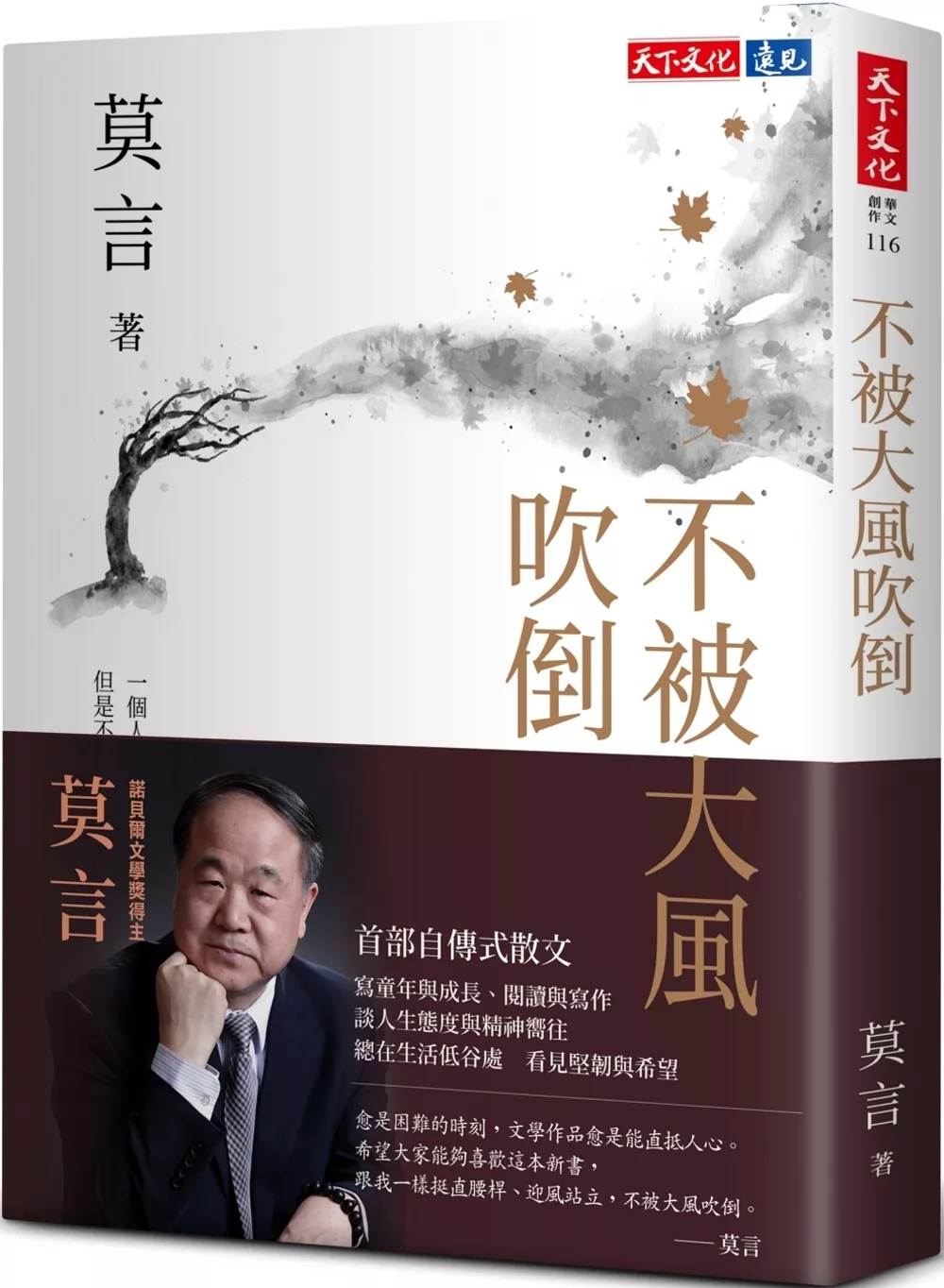代序
知惡方能向善
麥田出版社要改版《檀香刑》,我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是書能再版說明我在臺灣知音甚多,擔憂的是年輕人未必能完全理解我意,萬一誤導了青年,則我罪大焉,故而寫一個序言,簡單地訴說一下我寫這部小說的初衷,這很笨拙,但沒有辦法。
《檀香刑》看起來是一部歷史題材的小說,主人公趙甲是晚清的最後一個劊子手,因為執刑有功,被慈禧太后賞賜七品頂戴和龍椅告老還鄉。他的兒女親家孫丙,原是貓腔戲班班主,後解散戲班娶妻生子開茶館謀生。因家庭突遭變故,他成為抗德領袖,從義和團處學來法術,召集民眾和舊日班底,與修建膠濟鐵路的德軍對抗,兵敗被捕。為殺一儆百,德軍首領與山東巡撫袁世凱讓縣令錢丁搬請趙甲出山,設計一種能使人受刑但數日不死的刑罰,懲處孫丙,藉以警示民眾。趙甲設計了「檀香刑」。孫丙本來有逃跑的機會,但他沒有逃跑。他是唱戲出身,已經形成了戲劇化的思維習慣,每遇大事,他第一想到如果是戲中人物,遇到這事會怎麼做;第二想到,一旦這樣做了,會不會被人編到戲裡演唱而流傳千古。
魯迅先生在他的作品裡,批評了那些冷漠無情的看客,側面也表現了受刑人的表演心理。我是在他的這個主題上的進一步延伸和拓展。我認為劊子手、死刑犯和看客,是三位一體的關係。在這場轟轟烈烈的大戲中,劊子手與死刑犯是同臺演出,要求心領神會,配合默契。劊子手技藝不精,看客不滿意;受刑人表現不豪,看客也不滿意。所以這是一場喪失了是非觀念的殺人大秀。只要受刑者能面不改色,視死如歸,口吐豪言,慷慨悲歌,哪怕這個人殺人如麻血債累累,看客們也會發自內心地對他表示欽佩,並毫不吝嗇地把喝采獻給他。
我在這本小說裡,重點刻劃的是趙甲這個劊子手的奇特心理,當然也是變態心理。他不奇特不變態就活不下去。其實,變態心理人人皆有,那些斥責別人變態的人,他自己已經非常變態。所有心態,基本上都是環境產物,只是人人都在看別人,很少閉目看自心。
這部小說的內容,除了孫文抗德這個真實的故事內核之外,其餘的全是虛構。這樣的刑法,這樣的劊子手,從來沒有出現過。我一直悄悄地認為,這其實是一部現代小說,看上去寫的是長袍馬褂、辮子小腳,實際上寫的是現代心態。八十年代初期,當張志新1事蹟披露後,我受到了極大的震撼。我當時就在想,那個在執刑前奉命切斷了張志新喉嚨的人,那些以革命的名義,以人民的名義對張志新施以酷刑的人,他們當時怎麼想?當他們看到了張志新徹底平反,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時又會怎麼想?他們想懺悔嗎?如果他們想懺悔,我們的社會允許他們懺悔嗎?——後來,到了九十年代,我又知道了北京大學大才女林昭2的故事,知道了林昭故事中那個驚心動魄的五分錢子彈費的細節。我又在想同樣的問題,那些當年殘酷折磨林昭的人,那個發明了那種塞進林昭嘴裡,隨著她的喊叫會不斷膨脹的橡皮球的人,到底是怎麼想的?而更進一步,我又想,如果當時我就是看守林昭或者張志新的獄卒,上級下令讓我給他們施刑,我是執行命令呢還是反抗命令?更進一步想的結果使我大吃一驚,我覺得,從某種意義上,或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做劊子手,也都會成為麻木的看客。幾乎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藏著一個劊子手趙甲。
接下來我考慮的問題,就是用什麼樣的結構來寫這部小說,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寫這部小說。
在結構問題上,我想起了當年聽北京大學葉朗教授講《中國古典小說美學》時提到過的鳳頭——豬肚——豹尾的小說結構模式這種模式,為我的敘述,帶來了極大的便利,我認為也便利了讀者的閱讀。
語言問題,我想到民間戲曲,想到了我們高密特有的瀕臨滅絕的劇種茂腔——在小說裡我把它改成「貓腔」——同時我也想到了我少年時在集市上聽書的那些難忘的場景。
一想到戲曲,想到把小說和「貓腔」嫁接,便感到茅塞頓開。這不僅僅是個語言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小說的內在的戲劇性的結構和強烈的戲劇化情節設置和矛盾衝突。一切都是誇張的,一切都推到了極致,大奸大惡,大忠大孝,人物都是臉譜化了的。譬如孫丙,譬如錢丁,譬如孫眉娘,但唯有趙甲這個劊子手,是獨特的「這一個」,是《檀香刑》中唯一一個可以立得住,可以稱得上是典型的人物。當然,這有點王婆賣瓜。
《檀香刑》一書,從出版到現在,爭議很大。說好者認為是傑作,是偉大之作,說壞者貶為垃圾。其中的幾段殘酷描寫,更是飽受詬病。我之所以允許自己在小說中有這些殘酷描寫,是因為這部小說是一個獨特的文本。這是一部戲劇化的小說,或者說是一個小說化的戲劇。戲劇中的表演,假定性很強,有間離效果,這樣就為觀眾準備了心理空間,不至於過分投入。另外,我們人類,既是酷刑的執行者,也是酷刑的觀賞者,更是酷刑的忍受者,我覺得沒有理由隱瞞。只有知道人在特殊境遇下會變得多麼殘酷,只有知道人心是多麼複雜,人才可能警惕他人和自我警戒。我期望著在未來的社會裡,人人具有寬容精神,個個心存慈悲情懷,但是這一切,必以知道人類曾經犯過的罪惡為前提。
二○○六年四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