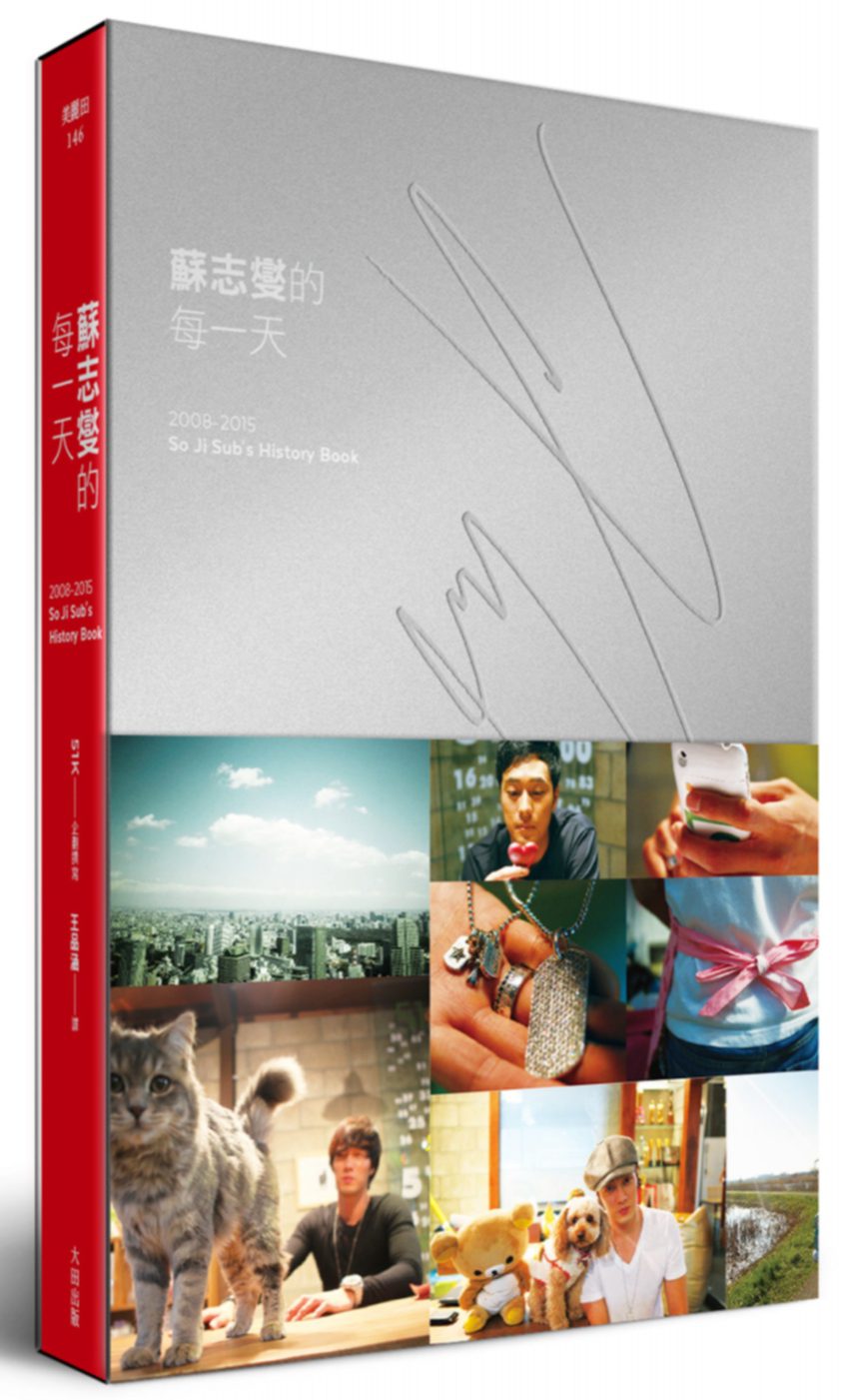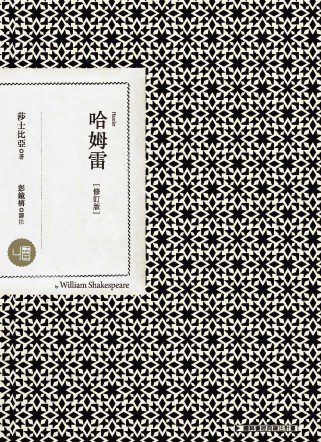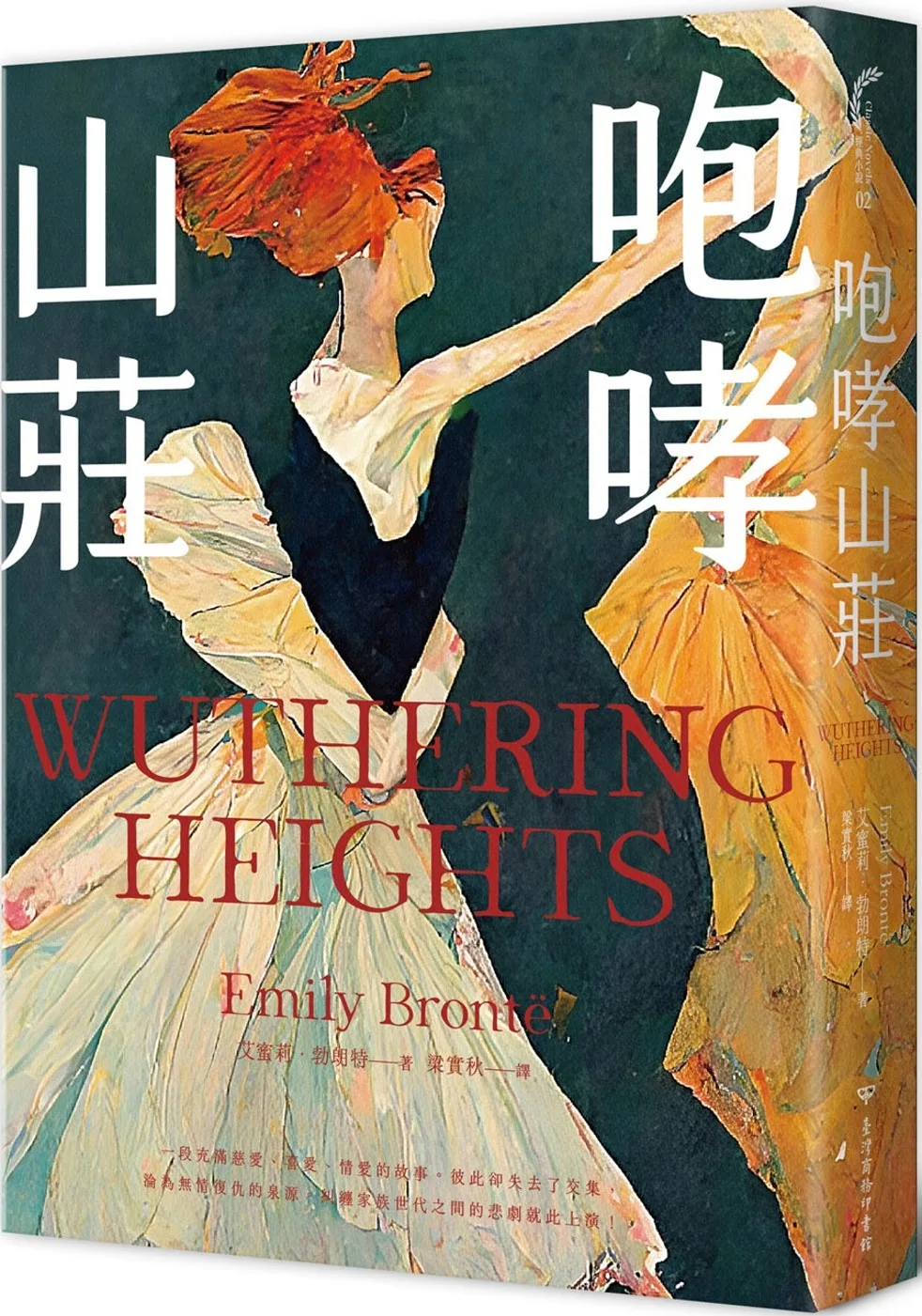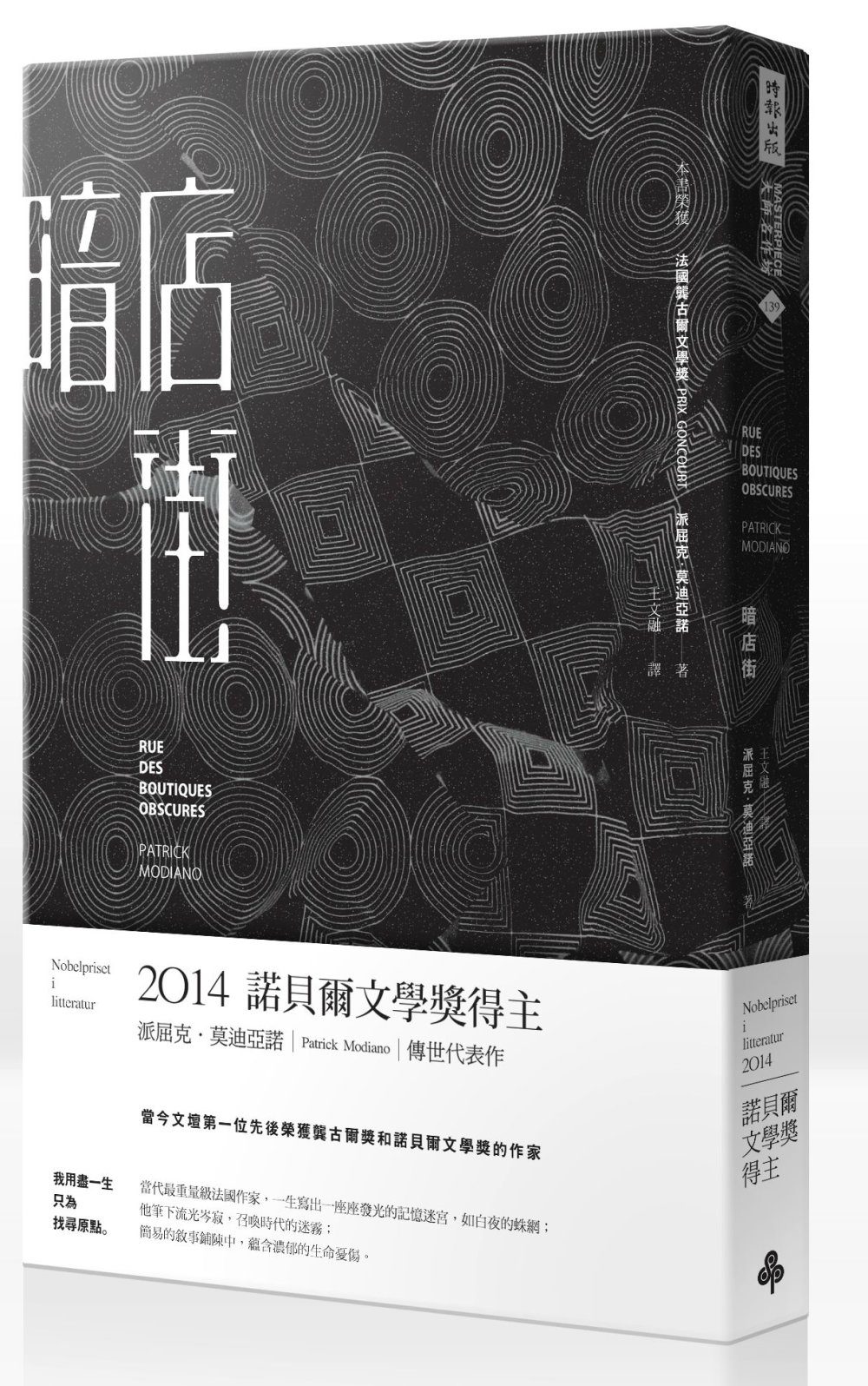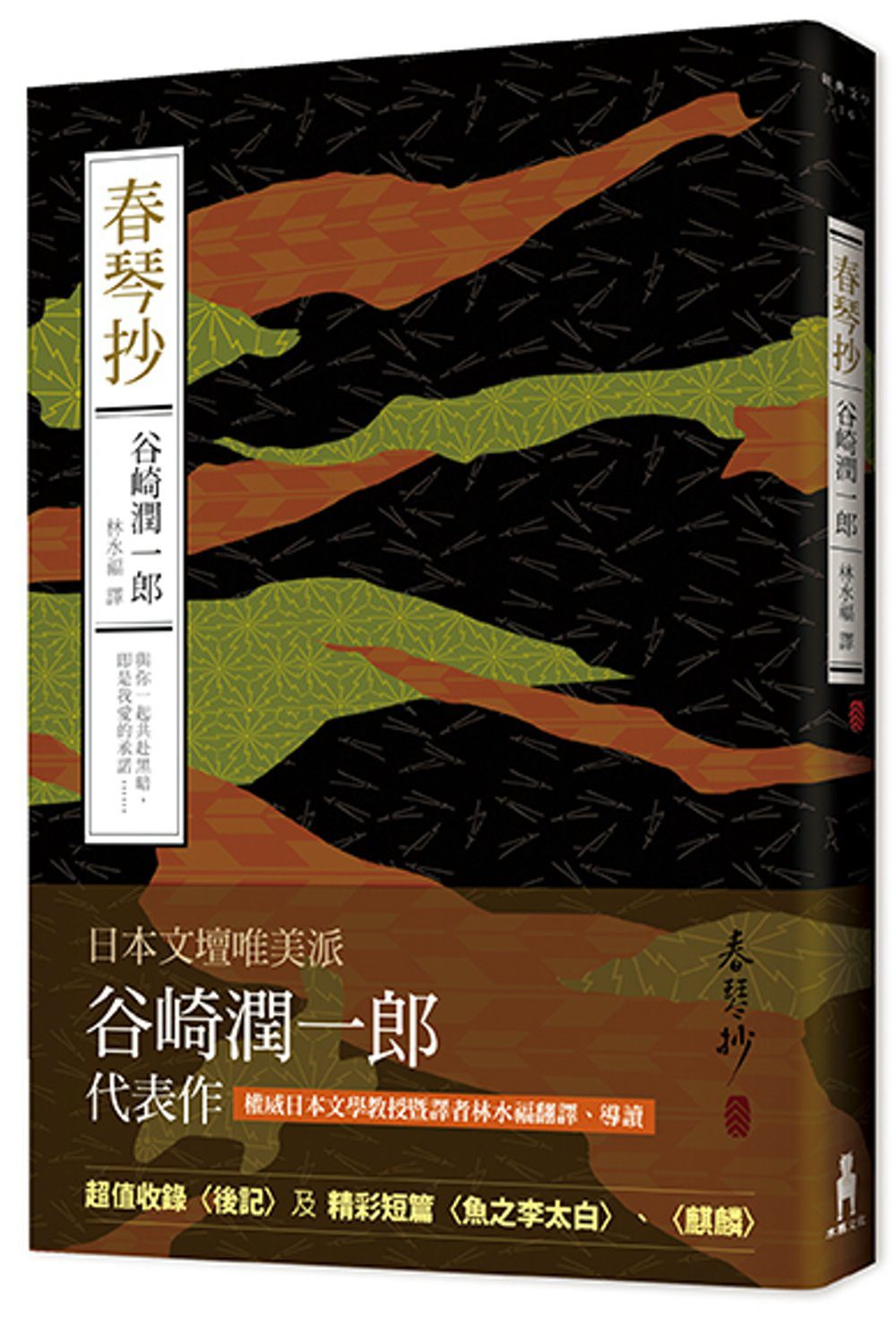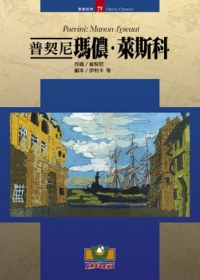緒論(節錄)
絕妙好辭︰語言與戲劇的結合
《哈姆雷》一劇情文並茂。劇中人物,從國王、廷臣,到演員、掘墓人都有;主線以外另設副線,大戲之中涵括小戲,不僅使結構多元,更增加了語言層次的複雜。單以哈姆雷一人而言,情緒即已變化繁多︰時而坦率真誠、時而隱諱曖昧、時而憂戚感傷、時而快樂振奮;有憤怒激昂也有抑鬱寡歡,有一本正經也有淫穢輕佻。而在莎士比亞筆下,各個角色、各式情緒、各種場景的描繪無不入木三分。
Kermode 討論莎士比亞的語言,認為1599年到1600年之間,他的文字技巧提升到新的水準,而轉捩點就是《哈姆雷》和詩作〈鳳凰與斑鳩〉(“The Phoenix and Turtle”)。《哈姆雷》正是波龍尼戲劇分類中那「無所不包的戲文」(“poem unlimited”),因為它包含了各式各樣的文體或風格(Kermode 96ff, Evans 131)。Inga-Stina Ewbank 強調文字在本劇的重要;她說,這齣戲「展露人類情境,具現於劇場整體的視覺語言與口述語言之中,如此強勁有力……;因此全劇的台詞具有為善為惡的力量,其複雜遠超過哈姆雷在幻滅時說的,『文字,文字,文字』。 」
以下首先簡單介紹莎士比亞擅長的無韻詩,再討論《哈姆雷》劇中若干片段,檢視莎士比亞這齣戲在語言方面的成就,特別著意於語言與戲劇的緊密結合。
無韻詩的靈活運用
以詩寫劇的傳統,在西洋可以追溯到古典希臘悲劇。莎士比亞的戲劇語言,形式上以「無韻詩」為主,摻雜了散文、韻文、歌謠等等。顧名思義,無韻詩的行尾不押韻,但它的詩行是「抑揚格五音步」(iambic pentameter),節奏相當齊整:每行十個音節,分為五個「音步」(foot),每個音步的重音落在第二個音節;因此每行讀起來是「輕重輕重輕重輕重輕重」。與莎士比亞同年出生但成名較早的劇作家馬羅(Christopher Marlowe,1564-93)慣用這種詩體寫作劇本,多半在行尾停頓,音調鏗鏘,號稱「筆力萬鈞」(“mighty lines”)。莎士比亞把這種詩體帶到更高的境界。他並不刻意在行尾停頓,反而經常利用迴行(run-on lines,亦稱跨行或接續詩行)和行中停頓(caesura),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他甚至不拘泥於每行十個音節。
詩劇的寫作中,另有所謂「分享詩行」(split lines,或稱shared lines),也就是同一詩行由兩個以上的劇中人對話組成。這種安排既能照顧到詩行格律的要求,又能凸顯說話者快速輪換(Preminger and Brogan: 1206,李啟範:163),從而戲劇化地表現出說話者內心的急迫焦慮或活潑機智。莎士比亞的無韻詩常見這種分享詩行;在他的後期作品,比例甚至高達百分之十五到二十(Preminger and Brogan: 1206)。
戲劇氣氛的建立
莎士比亞善於在劇首營造氣氛,早有公評(參見Willson)。前文曾提到《哈姆雷》這齣戲一開場的問句如何引發後人的興趣。Cohen認為詰問正是這齣戲的主要語氣,並且指出,戲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景次裡,頭一個說話人的台詞裡面包含了問句(135) 。
外表與內在
前文已經指出,莎士比亞的作品經常探究表裡不一的現象。《哈姆雷》這齣戲的眾多角色不遺餘力地抽絲剝繭,挖掘真相,其中以哈姆雷最為顯著。他的第一段長篇台詞就觸及這個主題。穿著黑色喪服的他,在宮廷一片喜慶的場景裡分外顯得格格不入。母后葛楚要他看淡父親的死,安慰他道︰「須知這事很尋常︰有生必有死,�走過塵世一遭,到達永恆」,他回答說︰「夫人,是很尋常」(1.2.72-74)。
在接下來的對話鞥,哈姆雷抓住母后「好像」一詞的語病,立即狠狠地搶白她一頓,刻意彰顯她的虛情假意。引文最後幾行以戲劇的隱喻強化表面與真實的差異︰「好像」、「扮演」、「動作」、「表現」、「裝飾和衣服」等等,都是悲劇演員用以製造哀傷假象的手法或戲服(Righter: 143-44)。他「好像」是說,他的真情不是外表所能顯現的。
然而,這一段話卻也可以說明劇作家莎士比亞和他所創造的戲劇角色哈姆雷一方面貶抑外表,揄揚無法實證之內在,另一方面又同時實證出了外表的風格(Willbern: 1) 。Thorne說得更明白︰哈姆雷既然講「不只靠我墨色的外衣……就能傳達我的真情」,則顯然認為外表至少還是能夠表達出一部分內在的感覺。哈姆雷自己這時穿的是黑色孝服,說起話來多的是雙關語和誇飾法。MacCary引述這一段台詞,指出引文除了後面三行的戲劇隱喻之外,還使用了「擬人法」(personification)、「誇張引伸法」(catachresis)、「連接詞省略法」(asyndeton),而從第五行開始,則連續使用了四次修辭學裡的「首語重複法」(anaphora),簡直可以說是在跟柯勞狄競賽修辭(86)。由此也可見,對造作虛矯的表達模式,他的態度其實頗為曖昧。固然哈姆雷譴責表演作秀,但是我們注意到這是出自一個演員之口──而演員,「照他自己的定義,缺乏本質或『內心』。因此,甚至在王子否認與外表有任何瓜葛的時候,我們警覺到他的作秀傾向,具體呈現在他『瘋瘋癲癲的模樣』」(Thorne: 112-13) 。哈姆雷內在世界的魅力不僅來自它的曖昧難明,也來自它的攻擊性,這段話是一個例子(Gross: 23)。
著名的獨白
顧名思義,戲劇角色「獨白」的時候,沒有──或是自以為沒有──旁人在場 (Maher: xiv)。《哈姆雷》劇中的獨白向觀眾訴說出角色的內心世界。根據統計,全劇共有十二段獨白,屬於哈姆雷的占了其中八段 。莎士比亞給了哈姆雷一個人200行的獨白,大大拉近了他跟觀眾的距離(Maher: xv)。也因此,「對其他的角色,哈姆雷打啞謎、拐彎抹角,甚至唇槍舌劍。獨白的時候,他的話誠實發自內心。何瑞修是哈姆雷的朋友,但觀眾可以成為他的親密夥伴」(Maher: xvi) 。獨白在本劇中的重要,由此可見。
Newell認為,總體說來,本劇獨白把意識範疇最深邃的人心加以「極度的戲劇表現」,也就是理智對意識的深入探究(18)。他說︰「揭示角色的心智(與感情)世界,當然是獨白這一戲劇手法的一種基本功能,但莎士比亞在《哈姆雷》進一步發揮這一功能︰他使用獨白的手法,前後相當一貫,使我們注意到心智本身,特別是心智之為人類特有的反思與推理工具」(18) 。不僅如此,他並且指出本劇獨白的安排具有結構性的意義,包括可以據而蹤跡主角的復仇經驗(28、 107、134)。
尖刻的文字遊戲
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反應敏銳、辯才無礙,喜玩文字遊戲。Ewbank認為這是環境逼人。她說,比起莎劇的其他主角,哈姆雷的情況特殊︰不同的說話對象對他有不同的算計;因此他必須時時注意,處處留神,以便掌握語言的先機;而這也製造了許多笑果(68)。Charney分析哈姆雷的語言,指出他的風格多變,至少可以區分為四種︰「(1)諧擬為主的自覺,(2)瘋癲時的機智,(3)獨白為主的激動,以及(4)敘述或特效的質樸」(Style: 258) 。文字遊戲具體表現了哈姆雷──以及莎士比亞──對文字的敏感與興趣。
風格繁複的散文
一、裝瘋賣傻
《哈姆雷》一劇不僅詩的部分多所變化,散文風格也頗繁複。根據Vickers的研究,哈姆雷使用散文的主要情景有二︰一是對國王以及他的爪牙裝瘋賣傻,另一則是當他需要放鬆心情的時候(Artistry: 248)。例如哈姆雷對國王非僅不假辭色,更時時嘲諷。國王遣送他出國的時候,哈姆雷跟他說︰「再會了,親愛的母親。」柯勞狄立即糾正他︰「是你慈愛的父親,」但是哈姆雷堅持︰「是我的母親。父母是夫妻,夫妻是一體。因此,我的母親。」弄得柯勞狄大為尷尬(4.3.52-55)。哈姆雷故意誤會別人的意思,這不是頭一回;鋒利尖銳的推理對他而言,是紓解強烈激情的一種形式(Doran: 56-57)。
二、輕鬆自在
從第二場第二景(羅增侃與紀思騰奉國王與王后之命,造訪並試探哈姆雷),柯勞狄派羅、紀兩人去跟監哈姆雷。哈姆雷剛見到久違的總角之交,不疑有他,立刻玩起文字遊戲,肆無忌憚的真心愉悅溢於言表。
三、散文詩
當然散文也不限於用來說笑耍嘴皮。緊跟著上面一段的對白,哈姆雷察覺他的朋友其實是國王的間諜之後,自述心境。這段文字以世間的美好明亮對照哈姆雷心中的抑鬱晦暗。譬喻鮮活、思想澄澈、節奏分明,稱得上佳妙的散文詩。Kermode甚至認為這可能是莎士比亞有意的安排,「表現散文可以用來複製詩歌」(111) 。同時莎士比亞也借哈姆雷之口,道出了文藝復興時代對人的最高禮讚,充滿了自信。除了表達了哈姆雷的情緒之外,這段話的遣詞用字也描繪了演出這齣戲的劇場。「『結構』、『穹蒼』、『天幕』令人想起伊麗莎白時代的劇場;劇作家常以『峽角』暗喻舞台;『鑲嵌了火一般黃金』聽來像是『天上』──塗了金星星的舞台屋頂」;等等(Cartwright: 101) 。這一來,提醒了觀眾注意演戲的實際舞台,引起他們的戲劇自覺,產生心理上的疏離效果,更能認清舞台上的演出(參見Cartwright: 101)。
四、插科打諢
插科打諢是丑角的本分。第五場第一景,掘墳者嘻皮笑臉,有許多精采的道白。掘墳者不僅取笑哈姆雷是傻瓜,更諷刺當年倫敦劇院裡看戲的所有觀眾──他們都是瘋子。引文最後兩句,哈姆雷說︰Upon what ground?是問失去理智的原因 (ground = 理由)。掘墳者不知道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把ground解釋成「土地」,弄得哈姆雷哭笑不得。一向伶牙俐齒,口不饒人的哈姆雷,在這一場文字遊戲裡,總算屈居下風,當了一次配角(Ewbank: 68)。
而在搞笑之餘,莎士比亞的雙關語似乎也別具深意。W. Kerrigan指出哈姆雷跟掘墳者的這一場戲在全劇發展中的關鍵地位。是哪裡出了問題呢?「盤據哈姆雷心裡的一切──姦情、謀殺、亂倫、鬼魂的指令、自殺的兩難──都聚合在『是哪裡出了問題呢?』這個問題裡。這齣戲、戲中的詩、精采的台詞、種種思想︰哈姆雷之所以為哈姆雷,《哈姆雷》之所以為《哈姆雷》,其道理都聚合在這個問題裡」(129) 。掘墳者的答案──「嘿,就在丹麥這裡嘛」──指的可能是他腳下的墳土,使哈姆雷的思緒轉到墳土,轉向死亡,以死亡結束一切痛苦,因為他接下來就問掘墳者︰「一個人躺在土裡,多久才會腐爛?」此後他跟何瑞修的一連串談話(幾乎是他自己的獨白)都環繞著死亡的主題,例如人死後會如何如何。「要生存,或不要生存」的難題,先前曾經令他長考,而今逐漸有了解答(W. Kerrigan: 128-51)。誠如W. Kerrigan所說,到頭來,「哈姆雷起初答應鬼魂要殺柯勞狄的諾言,成了上帝的諾言︰哈姆雷將會服從鬼魂,殺死柯勞狄」(146) 。這樣看來,前面四場演的是復仇觀念對哈姆雷心靈的影響;最後一場則是他的心靈對復仇觀念的影響(W. Kerrigan: 151)。
花了許多篇幅討論《哈姆雷》的戲劇語言,實在是因為戲劇語言牽涉到角色的性格刻畫跟劇情的推展。特別是在伊麗莎白時代,觀眾到劇場為的是看演員表演,聽演員念白。儘管後世演出可以在舞台設計推陳出新,可以任意搬動故事的時代背景,可以在特效上出奇制勝,對觀眾而言,要緊的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人物、語言與情節(Halio: 85)。要體會《哈姆雷》這齣戲的奧妙,尤其須先了解它的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