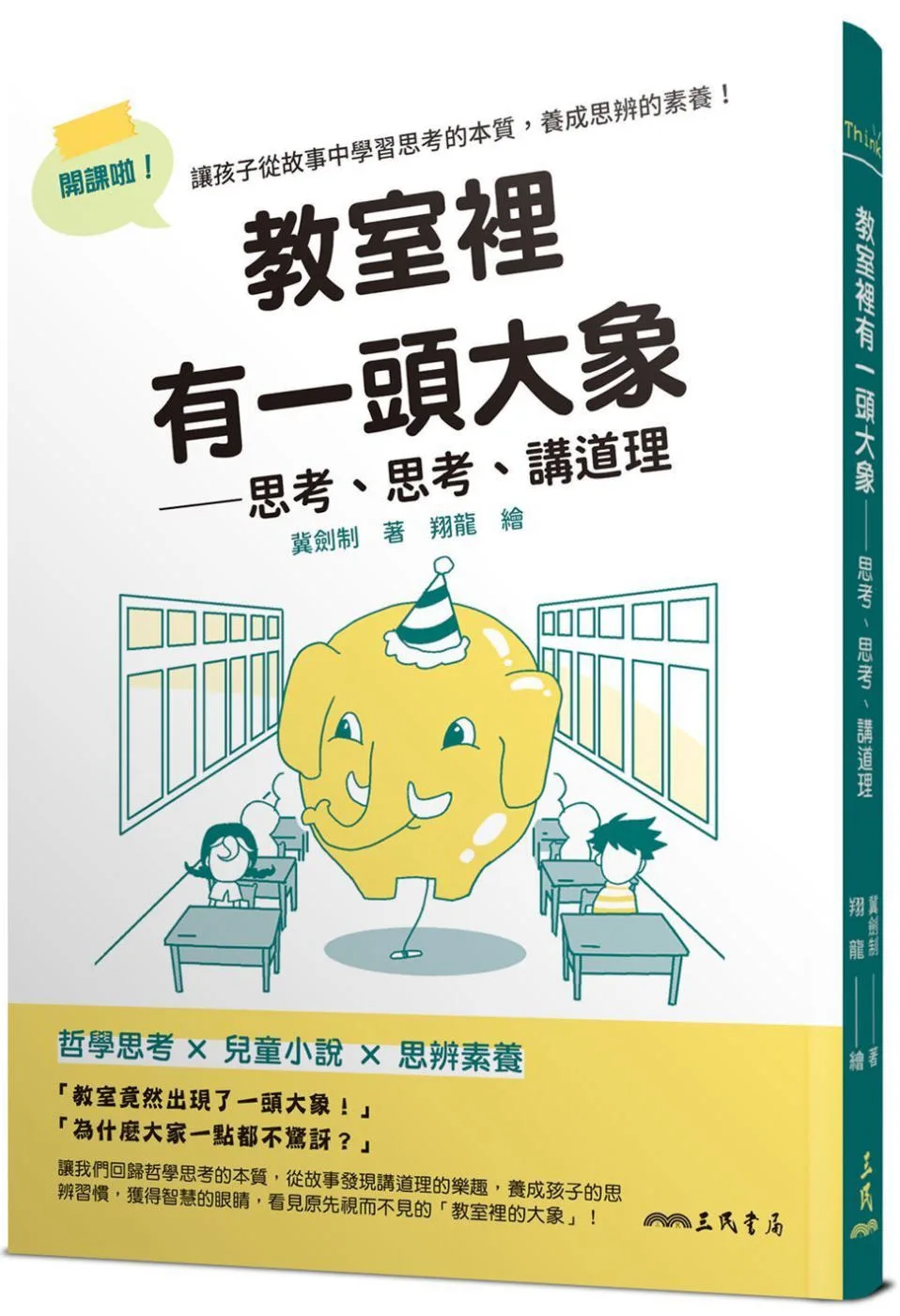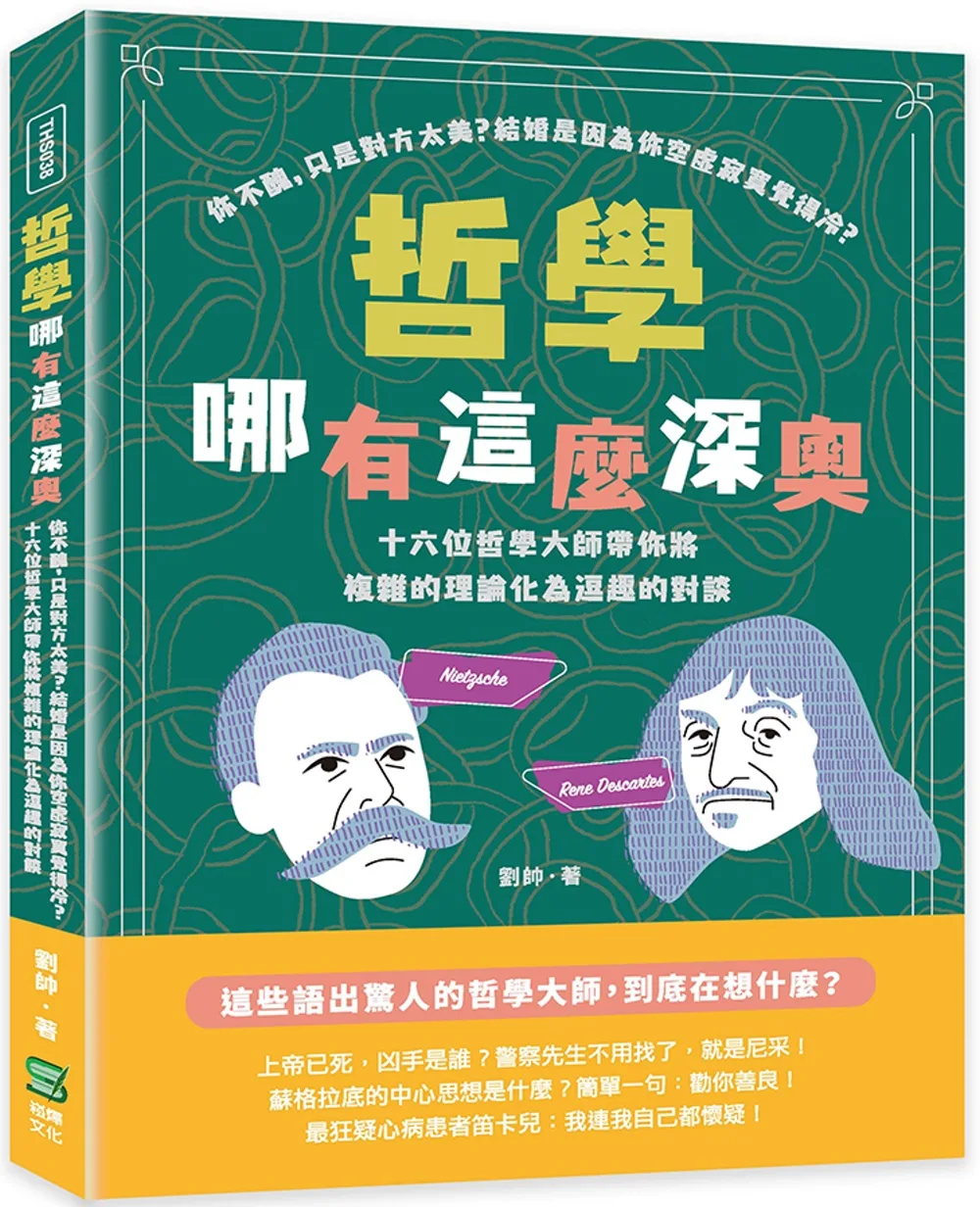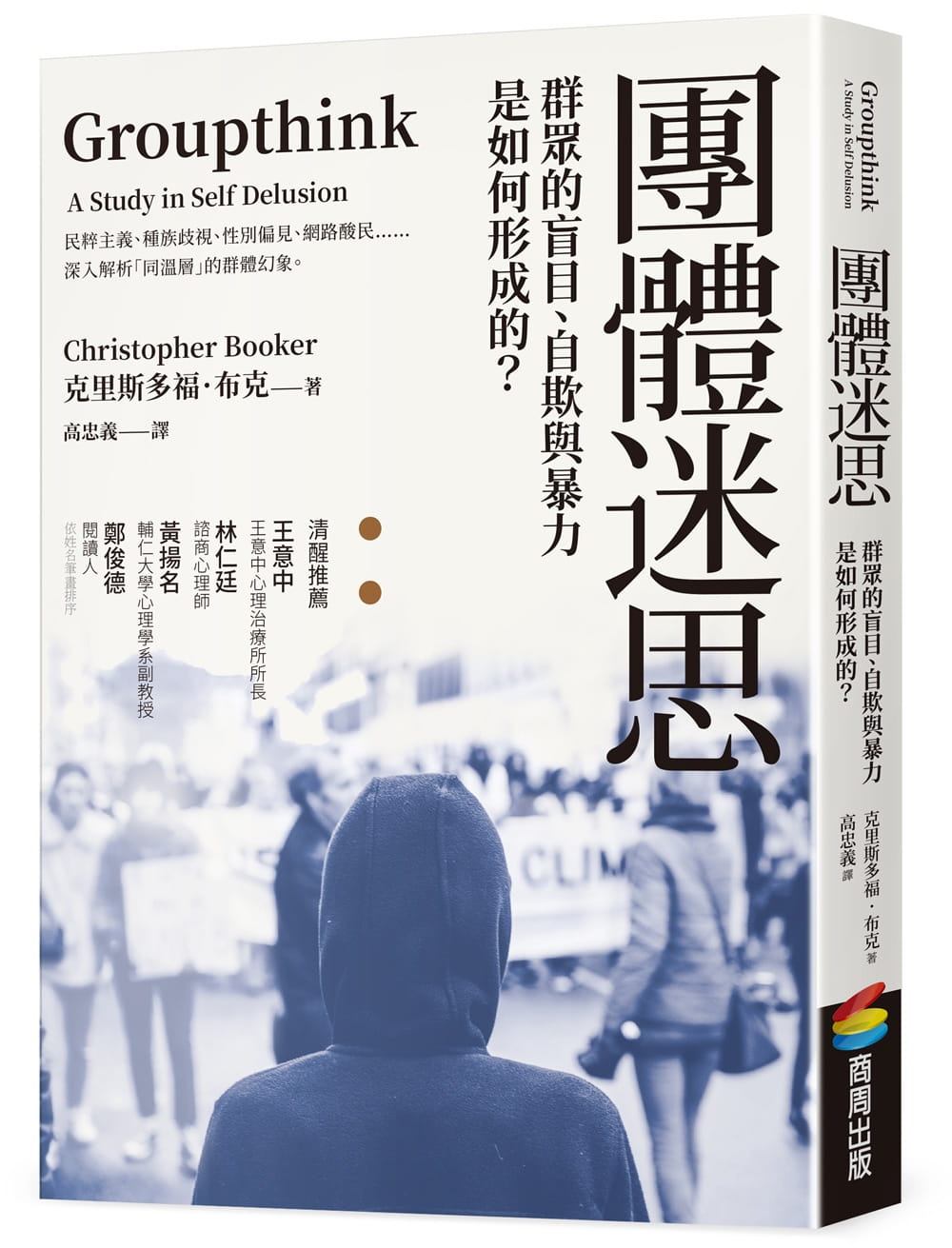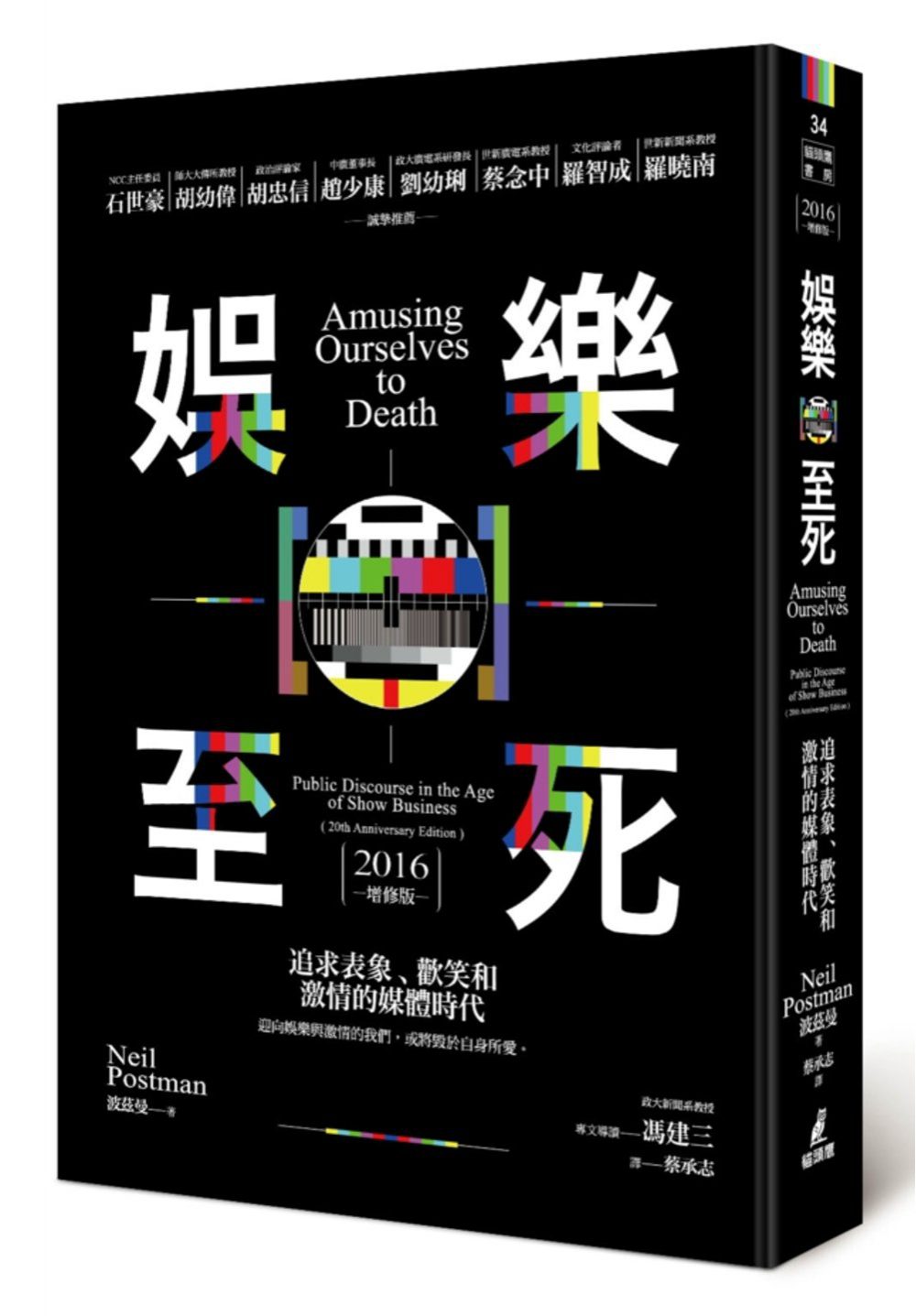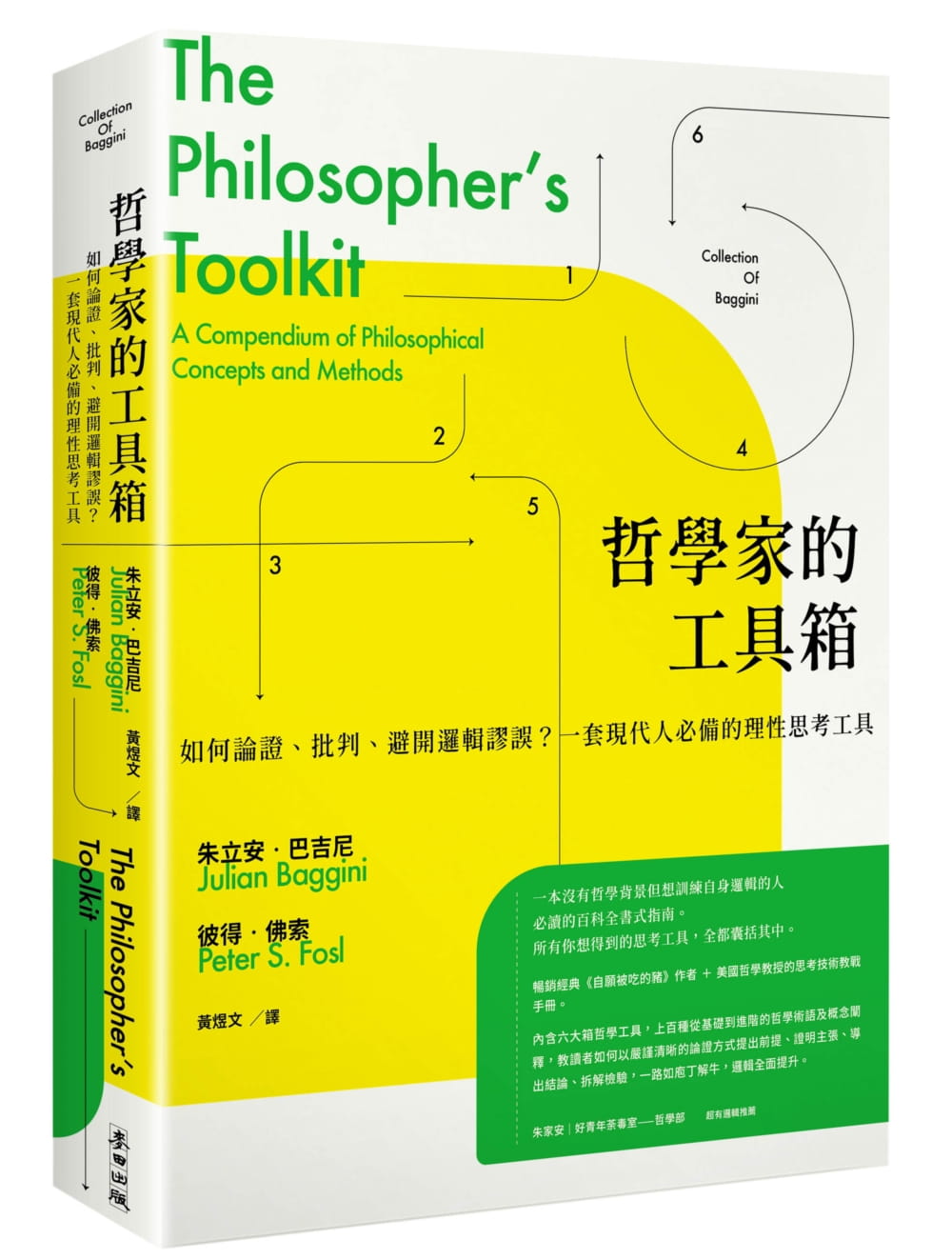自序
提問的本身,如同所有的研究,是生命迫切感的一個產物。—弗洛伊德,《孩童性理論》
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不是已經終結了嗎?自從冷戰結束以後,不同種類的「終結論」在知識圈中蔚為流行,「意識形態的終結」也是其中一個經常被觸及的議題。可是如果不健忘的話,將歷史時間稍微拉長,人們可以發現,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冷戰開始不久後,所謂的「終結論」就已開始甚囂塵上。如果冷戰結束時的終結論可以用福山(F.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作為代表,那麼冷戰初期的終結論就非貝爾(D. Bell)的「意識形態的終結」莫屬了。以意識形態的問題作為開端,中間配上「現代化理論」的福音,再用歷史走到終點作為結論,「三位一體」組成的神聖家族為整個冷戰過程似乎畫上了完美的句點。
面對冷戰剛結束後喧鬧的終結論,德希達(J. Derrida)當時一反潮流,令人意外地寫了一本討論馬克思的專書,其中不無嘲諷地說,歷史的終結、人的終結、意識形態的終結、形上學的終結等末日論的概念,毫無新穎之處,可以說從來就是當時他們那代人的哲學思考前提,甚至是他們「日常的食糧」(Derrida, 1993: 37)。然而,一樣米,養百樣人。與現在時髦的終結論高唱自由民主的勝利不同,經過二次世界大戰殘酷的洗禮,面對同樣的命題,他們所思考的方向卻正好完全相反,是西方啟蒙思想為何會從理性與進步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最終在內部出現了匪夷所思的種族滅絕,在外部發展為剝削掠奪的殖民帝國。因為打敗了納粹德國,並不代表同時就徹底理解了法西斯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放棄了殖民統治,並不意謂就真正清除了宰制他人的欲望。
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諾(T. Adorno)曾經說過,在奧斯威辛(Auschwitz)之後,不再有詩歌。因為這個地方所製造的恐怖,已經超出人類想像的極限,從而也超出文字可以表述的範疇。自從以前蘇聯為首的集團崩潰後,歡呼勝利的口號震天價響,反躬自省的聲音喑啞難聞。其實冷戰之所以結束,與其說是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毋寧說是蘇東集團自我瓦解的結果,並且其不戰而敗的速度與戲劇性,比諸1917年克倫斯基所領導的俄國臨時政府被布爾什維克所取代的狀況,二者實在不遑多讓。
如果事實勝於雄辯,冷戰之後,人們可以發現,最終可能並非是自由民主世界的勝利,反而卻是自身危機的開始。因為所有的制度都是歷史的產物,也終將被歷史所超越。當作為對手的邪惡帝國瓦解,在拔劍四望顧盼自得之際,彷彿道成肉身或是修成正果,自己成為了完美的代表,或至少是人類最高的演進階段。然而,魔鬼的對立面事實上並不一定就是天使。被勝利沖昏頭的帝國,依然陶醉於「彰顯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信仰,在沒有任何制肘的情況下,惟恐天下不亂,四處尋找敵人,與其繼續搭配演出牛仔與紅番的戲碼。對外一面高舉「永久和平」的旗幟,一面遂行「先制攻擊」的暴力。這廂宣揚「民主和平」,那處炮製「文明衝突」,聖經與利劍並置,胡蘿蔔與棍棒齊飛。對不願隨之起舞的國家,今天散播它「威脅」,明日詛咒其「崩潰」,恐懼與妒恨共存,高帽子與畫符一色。除了感到「天命」難測,人們或許只能自嘆雷霆雨露,莫非君恩。911之後,當美國人茫然問到「他們為什麼恨我們?」,聞之令人實在有「何不食肉糜?」之感。
冷戰結束後,已經不再有國家輸出革命,可是卻仍然有國家強行推銷民主,而且是以不民主的方式行之。然而無論是出於無奈或是真心擁抱,不管是直接引進或是平行輸入,有的地區雖然紛紛按照西方的模式打造自身,然而這一波山寨的民主化結果,往往不是先天不足,就是後天失調,畫虎不成反類犬,淪為所謂「不成熟」或是「失敗國家」的樣本。不成功其實並不一定是因為東施效顰,與原裝相比自己永遠是贗品,而是真貨本身也已弊病叢生。當西方世界不再有外部的壓力,不僅喪失了促使其改進自身缺陷的動力,從此也無法利用敵人威脅的藉口,作為凍結、轉移或是掩蓋自身內部矛盾的工具。縱使是冷戰拖垮蘇聯的經濟,西方世界其實也是透支殆盡。揮霍勝利的紅利後,在過度消費與盡享福利之餘,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經濟停滯、股票泡沫、地產下跌、失業高升、金融危機、債務危機……相繼地爆發,新貧階級開始出現,社會變為兩極分化,成了M型結構,或是單極增長,導致99%與1%的對立。
而所謂「負責任大國」應對市場失靈的方式,就是連續量化寬鬆,狂印鈔票。不同於之前鼓吹「霸權穩定論」時捨我其誰的豪氣,現在則是事不干己地兩手一攤,以近乎無賴的口吻表明,這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9。自認是發達的國家不僅肆無忌憚地使用武力與慷慨大方地外銷民主,當然也毫不吝嗇地輸出通膨,以鄰為壑,以他國百姓為芻狗,轉嫁傾銷自身的危機,導致蝗蟲般的熱錢全球亂舞,造成各地的物價飛漲。當某些所謂的落後國家在經濟上缺乏調控的能力,人民無法繼續承受生活的重壓,奮起反抗無力保護自身的政府,西方國家又搖身一變,倏然間禍首成了善人,以公平正義的好警察、清教倫理的金融家、拯救凡世的佈道者自居,指鹿為馬,將問題的焦點從經濟導向政治,以優美華麗的姿態站在正義與道德的制高點,精心地調配「顏色」或澆灌「花朵」的革命。「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畢竟誰掌握了話語權,即擁有主導遊戲與制定規則的能力。
然而被仔細包裝當作精品外銷的政治制度,其實在西方亦早已面臨「政治凋敝」的危機。從投票率的低落、腐敗的盛行、代表性的喪失,到民粹的興起、人民對政治的厭惡、對政黨的失望、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等。研究或關心這個領域的有識之士,紛紛憂心忡忡地開始「尋找政治」或是「回歸政治」、「論政治」。在《反自己的民主》這本著作裡,谷謝(M. Gauchet)表明,西方世界的人們基本上大致接受民主的統治;對來自反動的一邊或是革命的一邊的挑戰,民主確實是比這些長期以來的對手活得更久,然而現在民主卻遇見了最可怕的敵人,那就是它自己。在《為什麼我們不喜歡民主》這本書中,黑歐達?(M. Revault d’Allonnes)也指出,不再有「它者」的民主在失去了與極權概念的對比後,不再神聖不可侵犯,亦喪失了動能。民主體制雖然強調對權力的監督與制衡,可是它的構成與維繫也離不開權力的關係。
冷戰結束後,西方社會被某種所謂「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勢力所籠罩。源自「經濟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雖說是自由主義傳統的一個分支,可是實質上是一種「新保守主義」。這種新舊混和,自由與保守並存的政治經濟結構,在說著民主語言的同時,打造的卻是另一種新的治理模式,將民主的邏輯置於險境,使主體生存的不同領域化約為同一種樣態。傅科(M. Foucault)對現代社會的分析表明民眾得以狀似「自由自在」的生存,並非是從天而降的恩賜,而是經由一系列「主體性化過程」的機制,反覆灌輸與刻意建構的結果。存活在他所謂「生命政治」中的「民主人」,不斷地被要求去完成所有應盡的責任與義務。然而民主的目標並不在於將異質性的人們同質化,將其改造為「單向度的人」,而是使權力與自由二者之間能夠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理性導致民主之中出現「去民主化」的現象,社會喪失了確定性,相對主義盛行,生活的安適感不再,自認享有並掌控主權的人民,矛盾地卻不停地對自身認同產生危機。
朗西埃(J. Ranciere)於《民主之恨》一書中揭示,對民主的厭惡並不新穎,從柏拉圖以降雖然古已有之,可是卻於今為烈。任何政治體制不過就是對權力的一種安排,所謂民主亦不例外。就本質而言,民主政體其實是一種「寡頭制的法治國家」,選舉所保證的,只是不斷複製換過名字的同一類統治者。將這種民主放置在「超驗」的位置,然後當作偶像般頂禮膜拜,並不能掩蓋傳統政治模式的力量已經耗盡的事實,也無法減少全球化之下社會的不公不義,更不必說有效地阻止金融資本主義貪婪的發展或是暫緩世界生態危機繼續的惡化。
新自由主義式的「民主拜物教」並不能代表歷史已經走到終點,更不意謂意識形態從此結束。在《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政策》書裡,亨特(M. H. Hunt)表示美國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的國家,只是在個人層次上,他們自己沒有意識到而已。因為令人驚訝地,他們都一致地贊同相同的意識形態,並且視為天經地義而怡然自得。由於美國人將自己的意識形態當作理所當然,從而也自然地認為,其他不同的意識形態是異類或反常。更因為對此事的不自覺,美國人宣稱並且炫耀自身所擁有的並非是意識形態,而是一套完整的「價值觀」。如果仔細檢驗這種所謂的價值觀,它確實不能完全算是純粹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仙體凡胎與上下拼湊的科學怪人。因為與其他的意識形態相比,美國的價值觀事實上更落後與保守,它是宗教與意識形態的綜合體,是「前現代」與「現代性」交配的產物,是超驗與經驗同居的品種,是烏托邦與現實世界共處的結果。正因為是自然與人工的巧妙搭配,是神聖與世俗完美的結合,從而若有若無,似幻似真,如在眼前,與「美國生活方式」(American way of life)徹底地融為一體。冷戰後美國所推行的「新干涉主義」,其中所高舉的民主與人權,本質上依然還是早期「天命觀」在當代的延續與新的翻版。
我們現代所謂的意識形態概念並非自古有之,它的出現不是一個歷史的偶然,它是在18世紀末與現代西方民族國家同時誕生。重要的是,二者不但是同時,而且是同構,是同一現象的一體兩面。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作為最高主權象徵的民族國家取代了宗教的神衹,成為終極價值的來源。政體從神權、王權到民權,人民從教徒、臣子到公民。社會開始從超驗走向世俗,從他律變成自律,正當性與合法性基礎也從宗教變成了意識形態。如果說宗教的核心是信仰,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就是認同。信仰創造生命的價值,認同提供存在的意義。價值產生服從,意義導致信任。信仰的來源是出自團體的外在,垂直地從上降至下層,意識形態的來源是起自社會的內部,水平地由下凝聚而成。信仰的對象是唯一與固定的,而認同的對象可以是多元與可變的。
相較於傳統的封建社會,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就是一部藉由不斷的認同過程所創造的歷史。自從作為主權象徵的民族國家取代以往的宗教與教會,出現以民族作為單位的國家以及以個人作為單位的公民,二者其實互為表裡,屬於同一個認同過程所產生的結果。這個過程起初是由民族國家由上發起,從制度上主動將個人從舊式的封建社會連結關係中剝離,召喚至以民族為範疇的政治體制之內。換言之,個人化的過程是社會的產物,是政治領域自主性的結果。至20世紀中葉,社會個人化的趨勢開始轉變,認同的對象從國家逐漸轉換為個人,從此開啟了當代身分認同另一個新的階段。在一本名為《令人無法置信的對相信的需要》的著作中,克莉絲特娃(J. Kristeva)從精神分析的角度,闡釋對相信的需要其實是構成人類主體性不可或缺的部分。在《信任與統治》中,著名的政治學者蒂利(C. Tilly)在做了大量的調查與比較研究後,亦表明公共政治領域的成敗,涉及到信任關係網絡的存在。
最令人發噱與充滿歷史反諷的是,宣布歷史終結之後的福山,出人意料地推出《信任—社會道德與繁榮的創造》一書,也認為信任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社會「價值觀」。替明確的既存事實改頭換面或遮遮掩掩,正是標準的意識形態操作伎倆。或許是出於無知,要不就是如精神分析所謂「被壓抑的重新回覆」,福山替自己的終結論做了最壞的示範,可是卻對意識形態的運作做了最佳的展示。只不過以類似公開自我切腹的方式顯現如此簡單的道理,實在有些小題大作或是譁眾取寵。日後他修正了自己的立場,其實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早已有跡可循。或許他先前就應該接受來自他同行告誡。在一本比終結論早兩年出版的書中,亨特仔細分析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時言道:「他們和我們面臨的問題,都是要去理解意識形態,而不是表面上譴責並抹掉意識形態的某一種表現形式,而暗地裡又接受另一種表現形式。」
意識形態不是射向對手的一支利箭,將敵人定在恥辱柱上作為罪惡的化身,自己就立刻成為光榮榜上真理與正義的代表。它也不是某種政治體制所獨有,只要民族國家存在一天,就不會消失。意識形態連結觀念、召喚理想、填補政治裂痕、縫合社會矛盾、熨平歷史皺摺。但是同樣地,它也製造分裂、產生對立、提供錯覺、沉溺激情、逃避現實、鼓動暴力。意識形態是個人或團體形成的一部分,它是「生之驅力」與「死之驅力」的綜合,從而宣告意識形態的死亡等於否認自身的存在,這即是為何在宣告之後它又立刻復活,重複不斷地發佈它的訃聞,反證了它的無所不在。否認意識形態真正所想要表達的,其實不是對自身生命的否定,而是對死亡的焦慮,不敢面對它存在的事實。
在西方,伴隨著民族國家與意識形態同時出現的另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康德的批判哲學。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將人對外在認識的方式從宇宙論或本體論轉向知識論,為現代人文社會科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如果說法國大革命在政治上開啟了一個世俗的與自律的社會,康德的哲學體系則在思想上為這個新出現的體制提供了知識上的保證。然而康德哲學主要是建立在人具有先天綜合能力的假設之上,從而將人看作既是認識的主體,同時又是知識的對象。其所開啟的現代人文社會學科的知識,事實上是建立在一個悖論性與不穩定的基礎之上。
這種既先驗又實證式的人文社會知識體系,以東方的帝國作為外在他者,以不證自明的理性作為內在原則,替西方民族國家的同質化過程提供合理化的依據。然而在啟蒙進步價值的光照中,尼采重估了意志與真理的關聯。在學術客觀中立的表象下,弗洛伊德發現了欲望與知識的糾結。在現實利益衝突的身後,馬克思指出了觀念與權力的共謀。意識形態的作用正是在遮蔽或是掩飾無法被當代(西方及我們自身)知識體系所涵蓋的裂縫或缺口。它不但將這個知識體系中暗藏的激情與權力披上合理的外衣,並且也將西方本土的價值包裝成普世性的真理。然而在想像層次運作的意識形態,雖然如幽靈般穿梭於各個學科之間,或是暫留在某個學科中的一個邊緣角落,卻無法抹除自身經過時遺留下的痕跡,在掩蓋社會矛盾過程的同時,也暴露了自身的矛盾,從而亦可以作為理解現代社會連結形式的一個重要節點,透過這扇窗口重新理解觀念與權力、知識與欲望、真理與意志的關係。
本書是一個長期的寫作計畫,基本上是圍繞著一個中心議題,按照次序陸續地完成;主旨不在探討意識形態的類型或內容,亦無意於從事歷史性的分析,而是嘗試研究意識形態的運作機制與功能。寫作的時間起於上世紀90年代,最早一篇〈主體性的建構與國族的文化想像〉,源自於1994年6月「『南進論述』的批判:資本國族-國家與帝國」的會議論文。這篇短文簡單地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南進論述」,目的在凸顯「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與認同過程的關聯。撰寫此文後,開始動念想要進一步徹底釐清意識形態中主體性的形成機制。然而深入這個領域後發現,如果無法進入構成意識形態的根基,思考意識形態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這個根基涉及與構成了社會與精神過程背後最深的底層,正是在這個厚實無聲與難以辨認的實體之上,矗立著宗教、道德、信仰、政治,以及由此而來的各種社會制度。由於語言是人類再現世界的工具,從而也是構成思想與意識形態最基本的元素。人類對語言的認識不僅反映出人類是如何認識世界,也包含如何認識自身的主體性。本書理論的部分即是從作為意識形態物質基礎的語言開始,直至主體性機制的形成。可是實際的書寫過程是以台灣的政治認同為起點,進入一系列的理論研究,止於當代中國大陸自我認同的議題,中間夾雜一篇與此相關討論法國68年事件的文章。不同於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從「精神」到現實,再回到「精神」;本書是從具體到抽象,再返至具體,從現實到理論,再重歸現實。
這一系列文章的寫作持續時間與台灣解嚴後民主化的過程正好吻合。猶記得2004年正在撰寫理論研究部分的最後一篇文章,當時正值台灣政治最動盪的時刻,大選的狂熱橫掃全台,每位政治人物無不聲嘶力竭地吶喊,從握手拜託、鞠躬下跪,到抹黑造謠、發誓詛咒,各政黨無所不用其極地動員自己的支持者。不管是平面報刊或是視聽媒體,每日鋪天蓋地的宣傳與報導,馬路田間旗海飄揚,公司住家處處文宣,幾乎絕大部分的人,上至清流士紳、知識分子,下到平民百姓、民間藝人,皆陷於激情的躁動之中。二顆子彈事件後,全台更是幾乎長期陷入無政府的狀態。
人們以為將這些病灶簡單地歸因為「民粹」,似乎就可以解釋這些現象,並輕而易舉地將問題消解於無形。然而正好相反,「民粹」只是一個替罪羔羊,事實上它並不與民主對立,亦不是民主的派生物,或是一個有瑕疵的產品,而是內在於民主之中,是民主的一體兩面,是民主之所以存在的前提,是構成民主的可能性條件。「民主內戰」中,在政治人物高唱仁愛與溫情的說詞裡,其實每一句話都潛藏著憎恨與暴力,皆意謂著對立與撕裂。過往的歷史以及本書的研究表明,仇恨遠比仁愛更能持久地凝聚自己一方的力量,以及增加消滅對方的動能,所謂的「博愛共同體」根本上是建立在妖魔化對方的產物。書寫〈意識形態中的主體性形構〉一文的過程時不禁感嘆,在批判「南進論述」中,自己最初對台灣民主所表達的不安與憂慮不幸成真。或許已無需再以「威瑪共和」的現代性歷史作為樣本,去理解盧卡奇所謂「理性的毀滅」,以及施米特所揭示的民主體制之中所存在的結構性悖論。因為文章裡描述的情況彷彿出現在此時此地,理論與現實已經合而為一,自己在文中分析的對象被「意識形態的幽靈」附體,活生生地從筆下跳出,奔走在台灣的大街小巷。
為了清楚明瞭起見,故將全書分為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論研究,第一章在認識論上替意識形態問題做一個歷史的定位。第二章在起源上分析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中存在的問題。第三章是對第二章所引發問題的回應,目的不在批判對方,而是藉此補充馬克思意識形態理論的內容。第四章進一步深入討論構成意識形態基本物質元素的語言。第五章與第六章分別處理巴赫金與阿爾杜塞二人有關意識形態物質性的理論。第七章以精神分析的理論闡明語言的物質性及所涉及的主體性。第八章從精神分析的理論說明意識形態中的主體性如何形成。第二部分現象研究,收入三篇討論台灣,大陸與法國的文章,內容皆涉及現代性與自我認同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