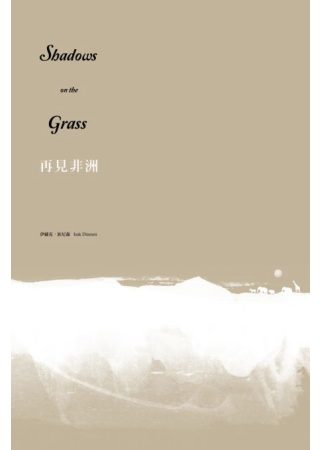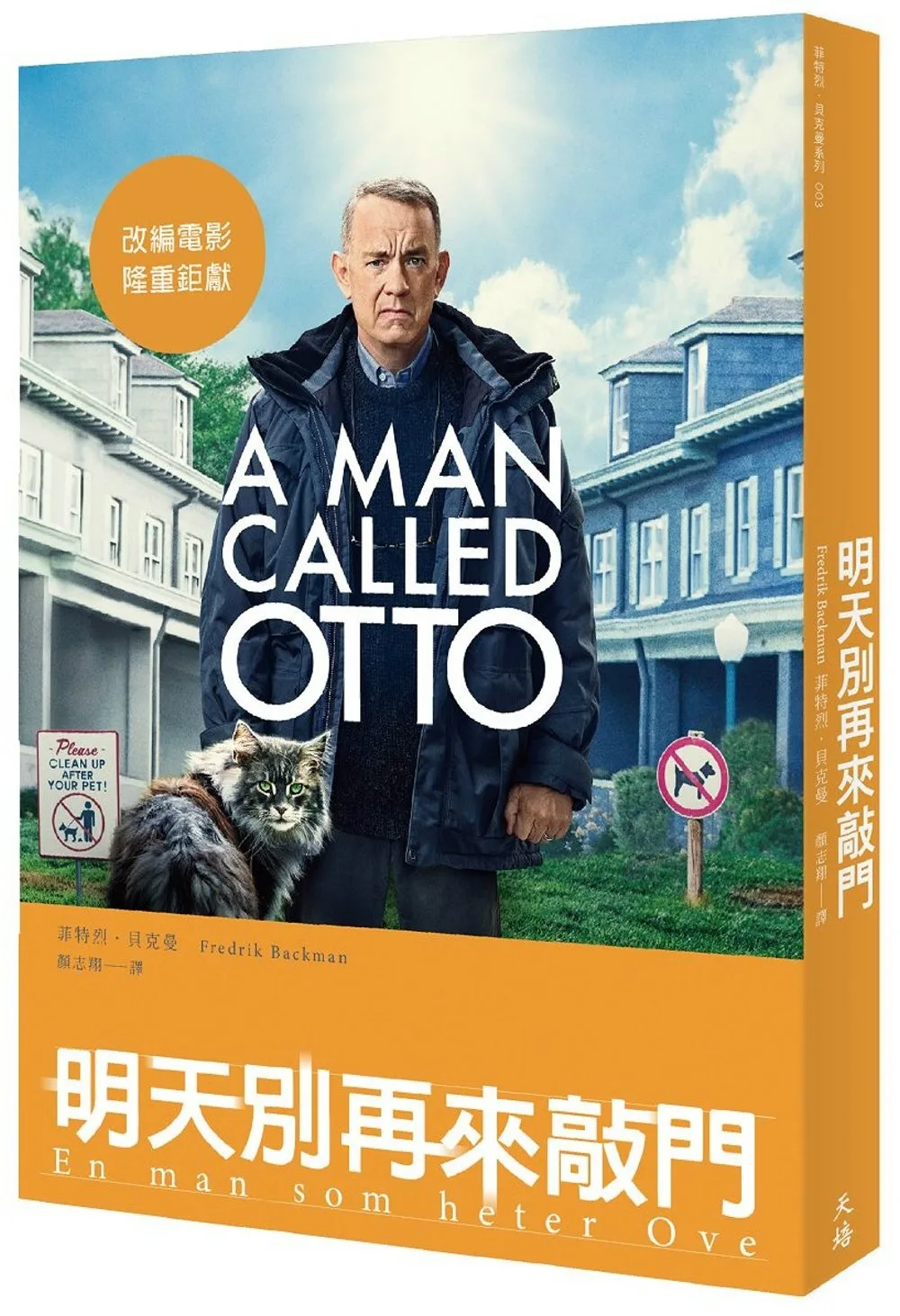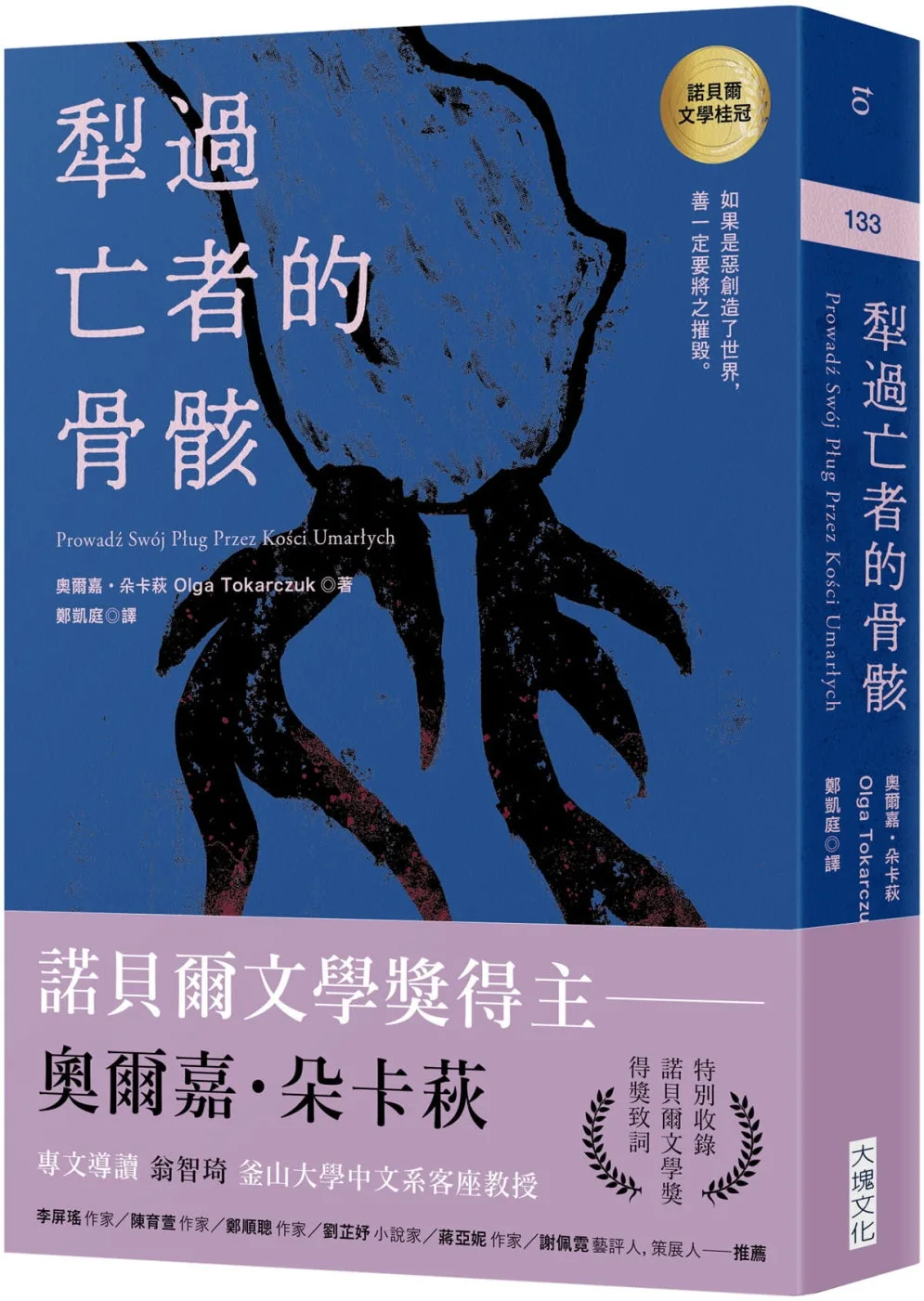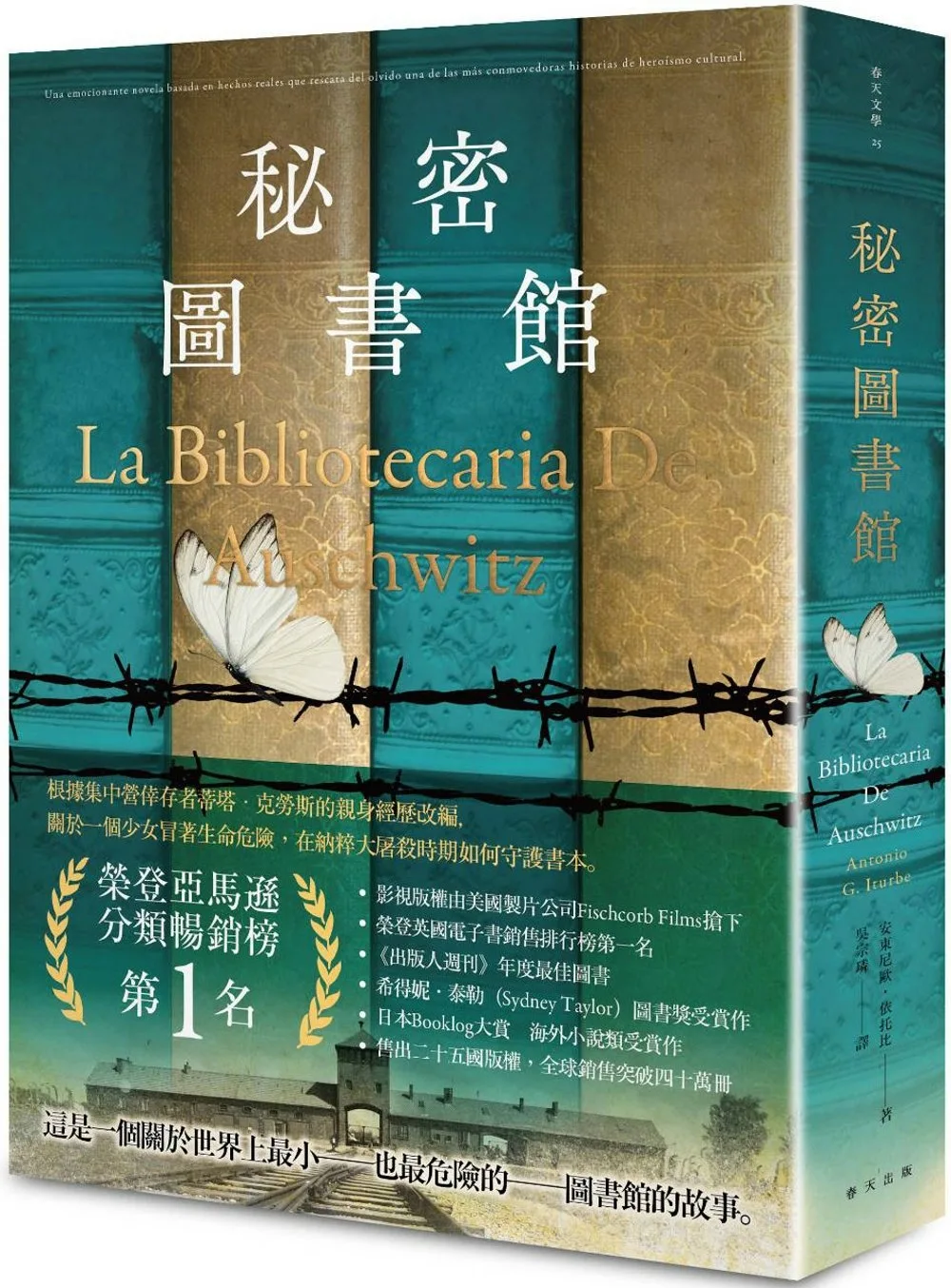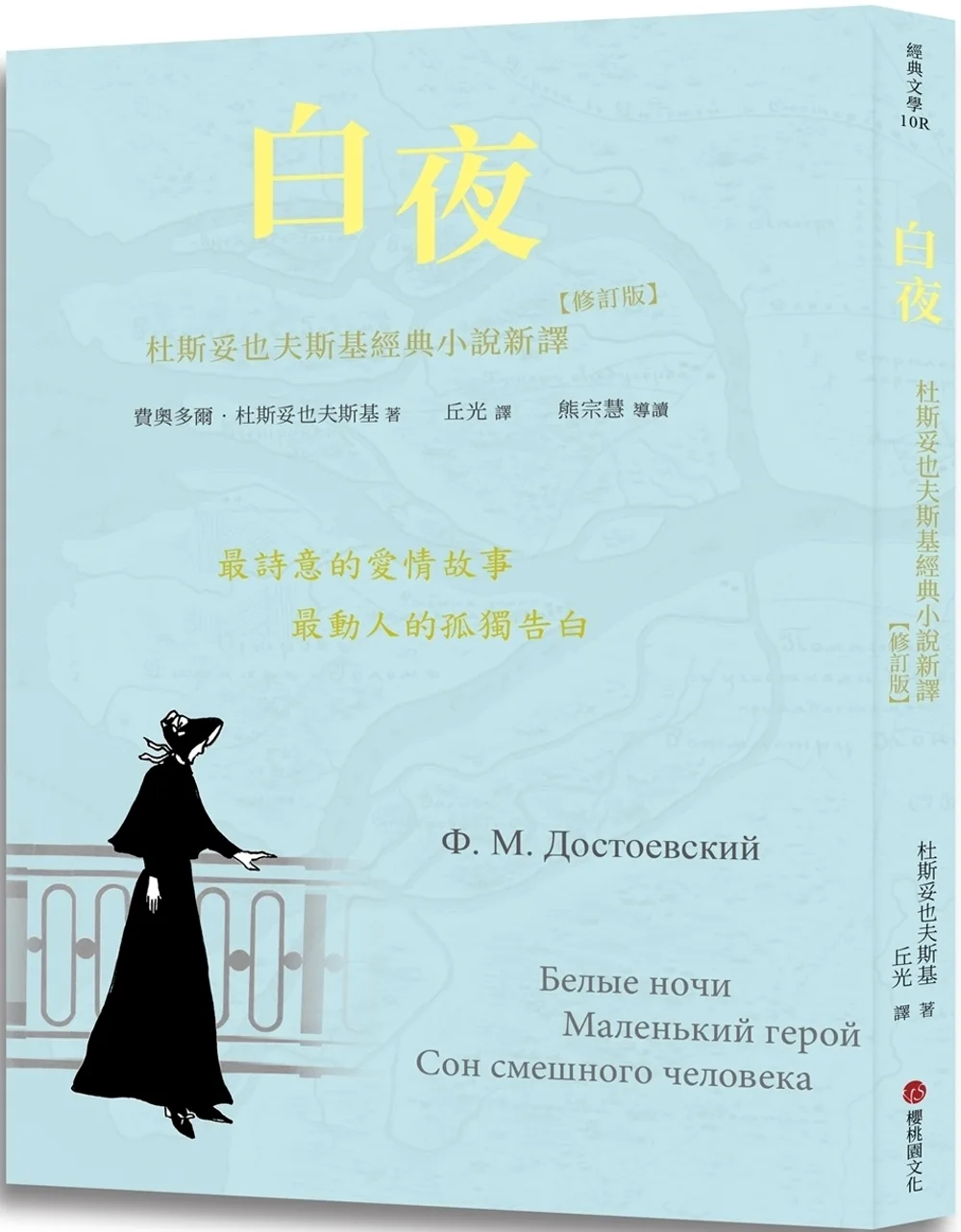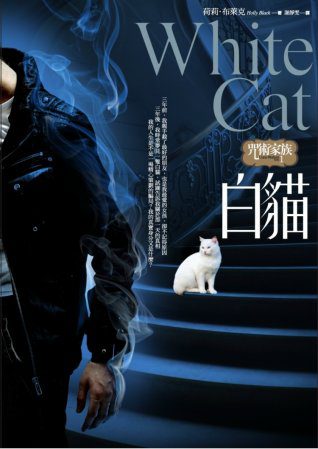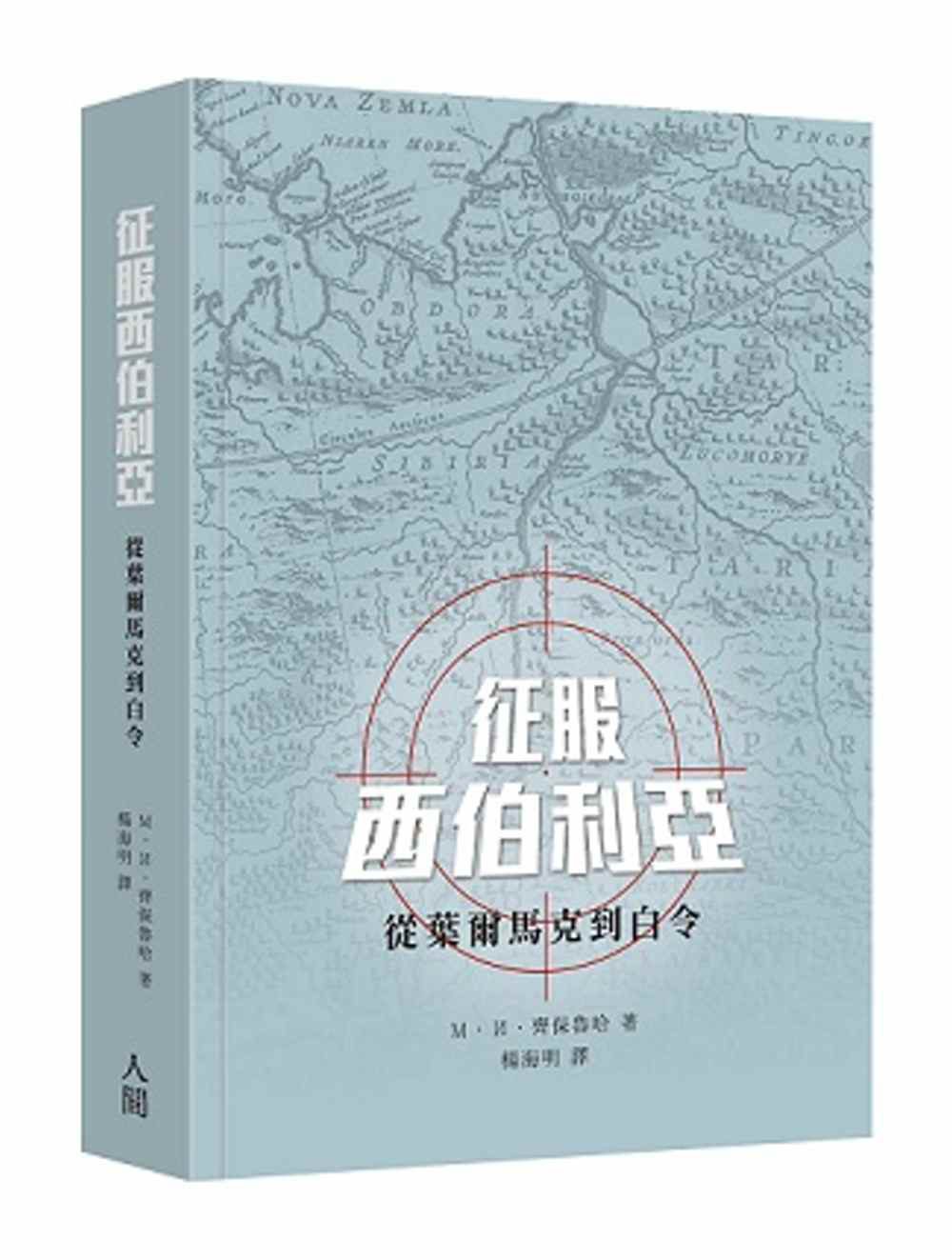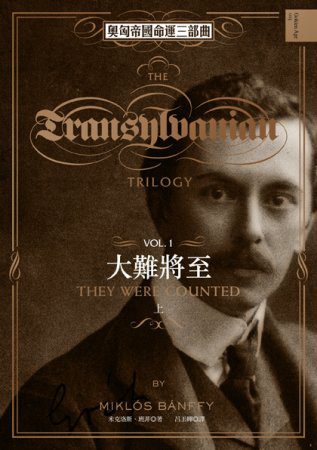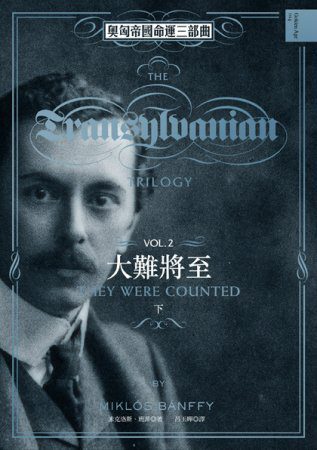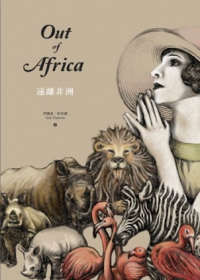序
更多的,是沒有說出來的事──我所誤讀的伊薩克.狄尼森
我常常想起伊薩克.狄尼森與海明威、卡繆活躍於同一個時代。那是西洋「現代文學」的年代,還有費茲.傑羅、西多妮—加布里葉.柯蕾特、畢卡索,眾多文學家、藝術家在此穿梭遊晃,要紅不紅或萬眾矚目。他們(還)不知道,那些從自我角度出發,省思或反叛社會的創作,將把世界推移出原本進程,前往未知。
我們皆被現世社會價值框架所局限,不管政客或素人,文學家或革命者,無論選擇反抗抑或信仰。那麼,起先我自《遠離非洲》裡讀到的那點不適,倒實實在在反應出我某種假知青的傲慢。
狄尼森以半生在非洲的所見所聞為藍本,創作了《遠離非洲》與類似補遺的《再見非洲》。她的寫作筆法詩意、輕盈,用字簡潔、乾淨,雖難免透露上層階級式的優越自覺。當狄尼森細數生活於非洲期間難忘的人與事,我很難不將「受惠於殖民」的疑慮納入對她作品的認同或分析。然而,我此刻所在意的自由價值與性別平等,在她存在之處才剛發酵。
非洲系列這兩冊書,敘事方法獨特,閱讀者幾乎不受文化或國籍差距干擾,如同她認為自己是「說故事的人」,狄尼森也的確將故事完美陳述,引人隨情節於那座落非洲的宅院間走動、拜訪黃漠遠處的部落,跟著她一步步在貧瘠土地上孤獨而堅定地建構家園,與膚色不同的陌生人成為相互信靠的同伴。
我這才反省,一位文學家於作品中展現對社會的關懷與想法,從來不止於字面,就狄尼森來說,更多的,是沒有說出來的,那些以私我關懷、實踐的事。於是,在看見殖民主義所築起之高牆的同時,我也感受到,她情感的溫柔、深邃,如何消融人們與土地、與身分間的邊界。那力量很強大,來自同理心,一種對人類情感的信任與著迷。
後來,我習慣以「名字」誤讀她的創作。
有些創作憑藉時間凝結記憶;有些藝術倚靠物品備註故事。就身為一位喜愛伊薩克.狄尼森的讀者來說,我會跟著她,在書頁間以名字召喚出所有景物背後濃縮進的隱晦情感:「喔,這是跟她離婚的人。」「欸,是那個丹尼斯.芬奇—哈頓。」試圖從她「什麼也不說」的字裡行間,體會她對愛的看法。這點偷窺式的誤讀,成為我所自以為,作者那創作生命,完整而迷人的體現。
我想伊薩克.狄尼森是自私的,她阻止愛的感受遺失、盡力深刻留下感受的方法,就是「不告訴任何人」。當我們於閱讀時不斷湧現疑惑,甚至開始往外探尋這些名字之間的關聯,我們已然成為她的信徒,感染了那股「同理心」,那種「對人類情感的信任與著迷」。
《遠離非洲》出版時,她已離開非洲七年;兩本非洲著作的出版時間,相隔二十二年,筆法與口氣卻沒有多少變化,她始終是那個在非洲咖啡園裡,蠻橫卻體貼、聰慧的女主人。非洲是狄尼森唯一的歸屬,縱然她離去,但始終沒有走開。我當然懷疑過,她是否故意將那片土地寫成美好樂園,若我們曾經稍微探知這位作家不怎麼平順的一生;但如此一來,我們也已同時將自我交付給了她,感同身受地隨苦痛的陰影俯瞰已然遠離的非洲,而在我們心裡逐漸成型的柔軟眷戀,不就是那個非洲真切存在的證明?
郭正偉
?
跋
用一輩子,寫給非洲一封情書
狄尼森的確是一種典型,無與倫比的存在,她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如此私密而自我,在內在反思中揉捏出溫柔的風景,一個虛實交錯、遺世孤立的地方。
她並不把自己當做世界的主宰,她明白,神才是世界的意識,對世界所感而生的想像,是神所賜予的禮物——
讓我們如山風般自在,不受行動、決心、責任的束縛。
她以想像的自由穿梭時空,拋開貴族的身分、一身的病痛、失去摯愛的痛苦,將對非洲的思念重組,濃縮成晶瑩剔透的文字,如蜂蜜、如琥珀的絕對、黏稠、無有瑕疵。宛如《一千零一夜》裡為國王把故事說個不停的少女,在那裡,愛情永遠飽滿、靈感永遠富足。
狄尼森離開非洲,形單影隻回到宏斯特莊園,悠悠忽忽過了五年,寫畢《遠離非洲》,在二戰爆發之際出版,奠定她在當代文壇的地位。之後,納粹勢力在歐洲蔓延,丹麥被占領,外在壓迫險峻的情勢讓她再次深深遁入想像世界。她並非迴避,而是將那軟弱、黯淡的人性,以文字柔和;將人類不可解的行為與醜惡,以故事安詳。
即便又回到昇平的年代,她的健康狀況仍是每況愈下,沒有非洲大地的空氣與陽光滋養,她愈顯蒼白瘦削。割去了三分之一的胃後,進食只是為了維持肉身的基本運作。然而肉體的脆弱無法將她囚禁,她的精神總是好,因為夢裡總是又見非洲。醒來再寫,夢裡又與故人相見:
我有時會遇見卡曼提,他狀似矮象或是蝙蝠;也會遇見法拉,他宛如一隻警醒的豹,在房子四周低沉地吼著。但是這些偽裝騙不了我,每次我都能認出他們每一個人。等到早晨醒來,我會知道我們已在夢裡相聚,在林間路上相會,或是一起去旅行。但我卻再也無法確定,他們是否依舊存在於我的夢境之外,或他們是否真的在這世上活過。
她仍不寫自己,或編纂故事,或訴說過去小事,至多出現的,是她的影子——她把對回憶的信仰,寫成那些隱晦如影般的字句。爾後,這些回憶的碎片又拼湊成一幅風景畫,從遙遠的地方,輕輕地迴盪著思念的曲調,宛如天空飄過的一朵雲抑或飛掠的孤鷹,浮光掠影,幻化成草原上淺灰色的陰影,這是《再見非洲》。
狄尼森在非洲住了十八年後離開,從登上開往法國馬賽港的船開始,就知道自己的後半生只能以思念牢記非洲,無法再靠近了這個屬於她的應許之地。如此度過往後的三十一年,直到再也嚥不下任何食物,吞不下一滴水,才替這封寫不完的情書作結。趁著肉身崩解前,打包了對世界曾有的愛,循著神的意識通向自由,她放手,將回憶包覆成的珍珠,投入時間的流。
劉粹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