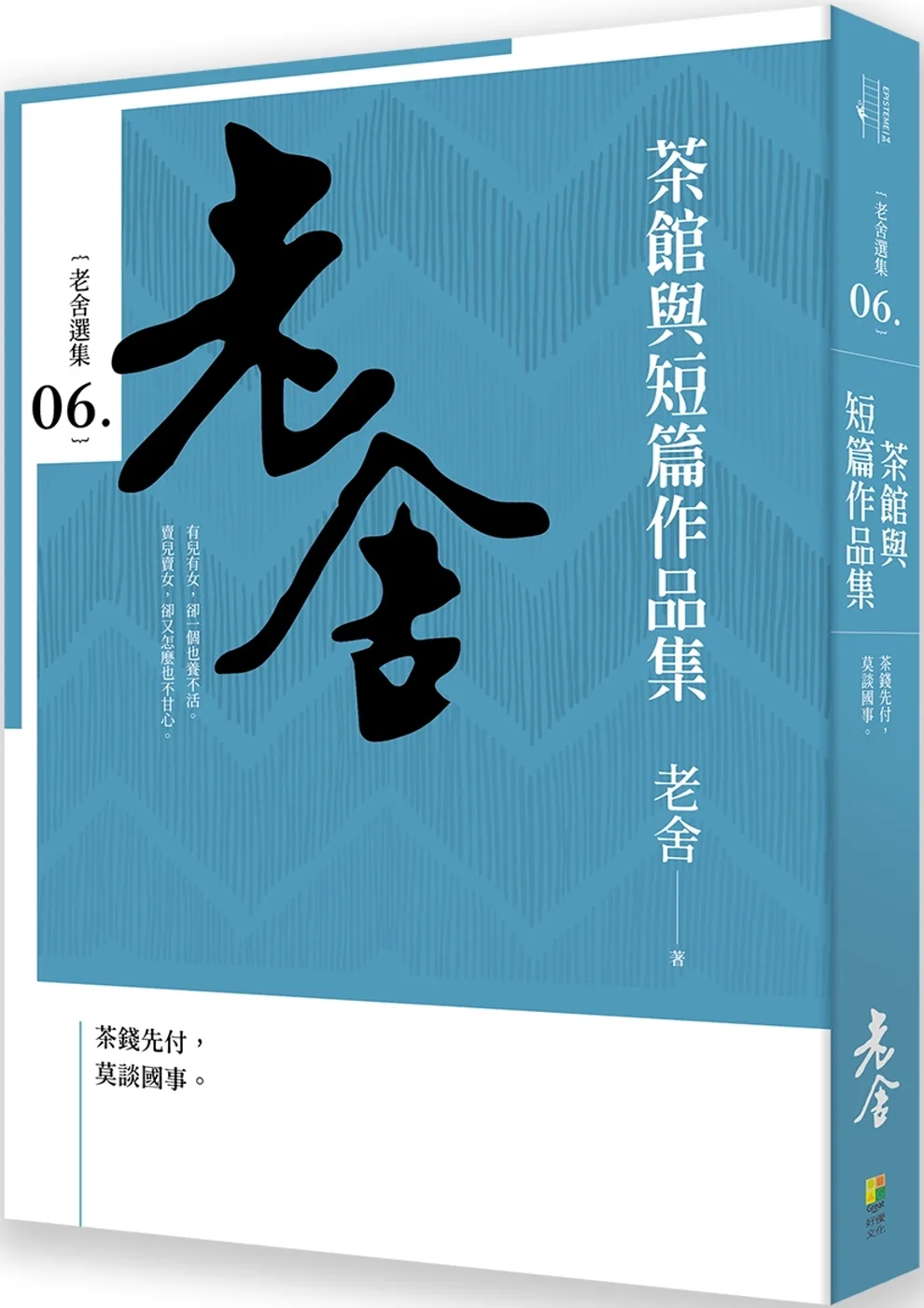序
河流與人間�黃錦樹
房慧真的散文,從她的第一本集子《單向街》(遠流,二○○七)就幾已確定了方向:關於身世,自童年以來的種種經歷,父親母親—這是抒情散文的「傳統領域」;對寫作者而言必須藉文字來清理,自我省視。文字的簡勁讓她的文章沒有多餘的水分。但在房慧真的世界裡,總是挺立著一個巨大陰影般的父親,及苦刑般的熱帶之旅。再則是成年以後她對處身的世界的微物觀察。與及,旅行所見。
《小塵埃》(木馬,二○一三)亦復如此。當細心的讀者發現〈小塵埃〉一文其實出於《單向街》時,可能會發現這兩本書其實是一本展開中的大書的兩個局部—它們相互補充著開展,隨著作者的生命旅程與寫作活動,自己的河流。
散文預設的自我同一性(敘事者我沒有權力更換身世、更換父母)讓她的寫作一定程度的必然被規範在特定的方向,這不止凸顯了散文寫作本身的困難度,也凸顯了需要寫作的生活本身的困難。
假如恪守散文的界限,不藉由虛構想像來做敘事的飛躍,寫作者勢必要克服經驗的侷限。或許我們可以觀察一下這本《河流》相較於前者,到底有怎樣的開展。
那個在前兩本書裡還是敘述者恐懼的核心的,來自印尼加里曼丹的父親,終於消散至只剩下他的故鄉婆羅洲本身(〈黑暗之心〉);童年經驗裡的傷害,也滌盡剩下童年的世界本身((汀州)、〈劍潭幻影〉),文章轉而藉由知識性開展那世界本身的歷史厚度或精神意義。但也許僅僅是把那些傷害暫時隱藏起來,來日再慢慢重新處理。
於是《河流》裡清晰的凸顯了兩個世界,一是廢墟一般的底層台北,一是台灣之外的世界—旅行所見:印尼、印度、中國,但作者的觀照點還是相似的,若不是底層的人,就是人間卑瑣的微物,世間的幽黯角落,某個瞬間。後者有賴於旅行,也是散文寫作者最常用以克服題材侷限的方式。以她受過攝影機訓練的眼睛,映現細節,兩個世界之間終歸會是互喻的關聯著。
底層的觀察,在近年的台灣文壇就比較少見了,那需要有顆柔軟的心,也需要一雙勤快的腳。有的文章近乎人類學式的鉅細靡遺的描繪—且在「賦比興」這三種手法中偏向於賦,敘述沿著對象空間的不同方位展開。如極具代表性的〈大河盡頭〉寫基隆河、新店溪沖積扇上「多中南部移民」的社子島,都會底層世界的縮影,那與垃圾、汙染、被大水沖走的無根的、卑渺的存在。〈大橋下〉、〈水上人家〉、〈河岸生活〉、〈大河之歌〉都是〈大河盡頭〉人類學視野的延伸。那是人類最古老的生活場域之一,幾乎可以說是極其接近生物本能的選擇。是「逐水而居、傍水而生,最低限度的生活」,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其他任何有河的地方,底層的人的掙扎總是相似的。
賦體又如〈夜市,人生〉,這是全書最長的一篇,細寫夜市這一獨特的世界,各色的攤販及遊客,衣食住行與奇淫巧技。在她筆下,那是一處溫暖明亮的所在,帶著若干奇幻的色彩。如其言:「夜市是夜不拔營的馬戲團,夜夜上演著都市傳奇。」〈流浪藝人〉、〈江湖在哪裡〉可說是這〈夜市,人生〉的延伸,猶如〈彼岸〉是它的變奏。
但有的篇章則如廢墟考古一般的,如〈邊城〉中敘述者進入歸綏街一帶性產業遺址,那周邊衰疲的市井民生;彷彿看到一種啟示:「再找不出任何一個地方若此,彷彿人生的縮影公園,不出幾條街廓,便可將生、老、病、死一網打盡」,也「一網打盡」各種原料、各種行業、各種沒落,無言的喘息著。那是個廢墟般的世界,昔日繁華遠去,惟餘憑弔而已。
又或重心也許並不盡然在於那些景象,而是一種溫柔的凝視,在近乎絕望的世界裡辨析出底層的人相濡以沫的情感、活著的理由。如〈浮島森林〉裡萬華「蝴蝶蘭大旅舍」墜落人間底層的眾妓的「守望相助」的情感,敘事者溫柔的理解她們的處境。或如〈彼岸〉,在熱鬧的夜市攤販的巷弄裡,尋找不尋常的一隅,「一家隱蔽於深巷的精神病院」。這種獨特的觀察角度,讓她會特別去關心各種生意冷清的攤子,為箇中生態寫出觀察報告(〈冷攤〉),也找到一種不尋常的認同感(「寒夜裡的冷攤,實是心底一道炙燙妥貼的熱風景。」)這也標出了敘述者的位置—她身在其中,並不是局外人。
這樣的寫作取徑,彷彿要一探人間的邊界似的。
作為散文寫作者,房慧真的優勢除了對底層角隅異於同代人的熱情關切、文字的精準刻繪之外,就是她的博覽雜書,與及對電影的熱愛熟稔。這讓她的寫作,常常可以縱向橫向的調動不同文學作品、影像裡的關聯場景或細節、情節,以對所見所歷做比較印證。這一特色在之前的兩本書也有充分展現。
《河流》裡諸如〈流浪藝人〉、〈江湖在哪裡〉、〈水上人家〉、〈劍潭幻影〉、〈黑暗之心〉、〈看不見的城市〉等都有盡致的展現。大抵可以分為兩種型態,一是從個人經驗出發,互文似的延伸開去(〈水上人家〉、〈劍潭幻影〉、〈黑暗之心〉);一是純粹知識性的引文牽連(如〈流浪藝人〉、〈江湖在哪裡〉)。
它的長處是可以增加個人體驗的文本的厚度,縱橫印證,而帶有學術筆記的趣味。但如果個人經驗占的篇幅很小,彷彿就是純粹的筆記叢談了。
在這樣的寫作中,父親不在場的婆羅洲之旅應該有其獨特的位置。〈黑暗之心〉的婆羅洲溯河之旅,已是父逝後女兒的尋根。敘事者調動非洲、南美洲那兩塊飽受殖民蹂躪的大陸來對應婆羅洲;調動剛果河、亞馬遜河來對比卡布雅斯河。在這樣的對照裡,婆羅洲其實是世界史裡相對被忽略的小老弟。在這父亡後的熱帶原鄉,除了眾所周知的奇花異果、怪獸詭禽之外,借來做對比的洲與河讓她可以較自由的調動系列鏡映交錯的文本,以幫助她理解那陌生地,就像邀請熟人伸以援手。《黑暗之心》。《陸上行舟》。《天譴》。《奧邁耶的癡夢》。《一掬泥土》。而結以《大河盡頭》。家族史裡的錯亂倫常,狂悖的生殖意志,被代以尋根女兒的「經血反哺」,那象徵生殖已然失敗的血,「溯流而上,直抵生命之源、黑暗之心。」
這裡最直接的關聯文本當然是李永平兩大卷的近著《大河盡頭》。
身為婆羅洲人的女兒,在寫作的精神淵源上,李永平理應是那父親(如果女兒寫作……)。她那一心想返鄉且費盡心力為女兒辦了印尼護照,絲毫不認同中華民國,對中文甚至頗為憎惡的,絕對認同那不斷排華的印尼的土生華人(peranakan)父親,晚年因執意返鄉而徹底失去自己。對比於那因為對大馬政府打從心底的畏懼而三十年不敢返鄉,對中文和中國有著狂熱的愛的新客的兒子李永平,認同上的對照像斑馬的黑白線條那麼分明。他們同樣來自婆羅洲,但那土地因殖民分割及後續的效應而分屬兩個國家。出生於民國台灣的房慧真,以中文寫作,她的婆羅洲之旅將是李永平人生旅程的顛倒,以未來式的時態。
《大河盡頭》中的敘事也是鬼月,但那敘事其實是過去完成式的,敘事還未開始故事就已經結束了。是死者尋找自己死因的敘事。但婆羅洲女兒的故事才正要開始,還在試音的階段。
整體的看房慧真這三本書,為逃離恐怖的父親,少女時期主人公曾在台北都市的迷宮巷弄裡遊蕩,幾幾乎就是個稚齡的漫遊者(流浪漢、人)了。無怪乎她對都市底層的人有著一種異乎尋常的親切與愛,對城市的隅角熟稔如家。而那雙健壯的腳也常不知不覺走到都市盡頭的河岸、河沿、沙洲,那畸零人與廢棄物匯聚之地。作為都市的孩子,她其實老早就走進她喜愛調動的文學作品裡了。不止常與小鎮自私自利有時還會性騷擾小女孩的亞茲別們(〈小鎮畸人〉)擦身而過(俐落的閃開那突然伸過來的髒兮兮的鹹豬手);在她遊蕩的八、九○年代,在那個以海棠地圖命名的台北大街小巷,她應該會多次與《海東青》裡那傻乎乎愛掉書袋、喃喃唸著國父的名字的靳五相遇。有時,她幾乎就是那個蹺家的小女孩朱鴒了。還好她並沒有迷失在《海東青》那詰屈聱牙灰暗的變態成人慾海裡。對書及電影的愛好或許讓她早早的找到一條逃離荒涼的此在之路,也避免成為戒嚴國民教育裡的又一隻乖順的填鴨。她常光顧楊索筆下悲愴的夜市,對她而言那有著超乎家庭的溫暖;駱以軍《月球姓氏》裡的外省畸零人幾乎就是她街巷裡的親朋了。《第三個舞者》裡的暗巷她一定經常穿越,遇見的不是空娩的母親,而是流浪的貓與狗與翻找垃圾的人。那時婆羅洲對她來說還只是謎樣空洞而燥熱的灰色符號,一如生身父親漂泊生命裡難以言說的傷害。
那時她或許就已經知曉,有一天她會找到自己的路徑,用語言文字更為飽滿的重建自己的世界。
二○一三年九月二十日中秋次日,埔里牛尾
(本文作者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