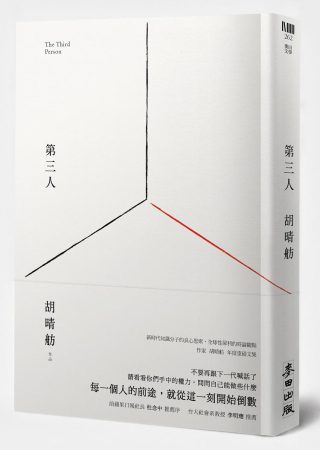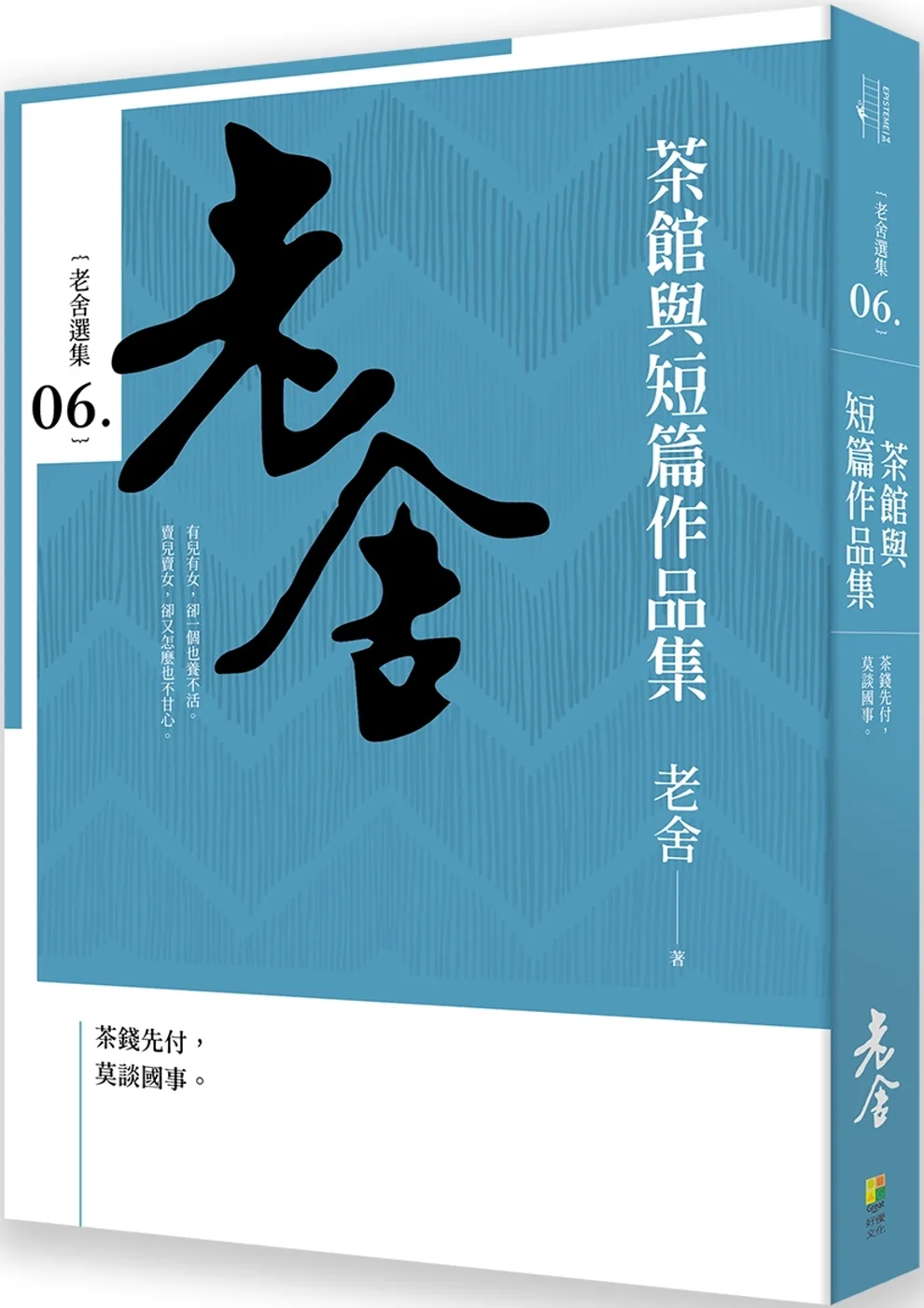推薦序
現代阿特拉斯 杜念中/資深新聞工作者、《蘋果日報》前社長
認識胡晴舫少說也有十幾年了。不過記憶中,這十幾年來晴舫似乎一直居無定所,她不是在香港,就是在上海,有時在巴黎,現在又在東京。其實「居無定所」並不是一個恰當的描述,因為它多少意味著流離失所,或者出於不得已的原因被迫漂泊。但是晴舫並非如此。她反而更像是上世紀末期開始被嚴肅定義的「新游牧族」。
有人說,新游牧族應該這樣的:從一個國際機場到另一個國際機場、一個酒店到另一個酒店間的不停游動,隨身配備著新而輕便的通訊設備,永遠不會因為快速切換地理位置而失去與世界的聯繫。也有人說,新游牧族終止了對他們國家民族的忠誠、切斷了與家庭社群間的臍帶。從各種有形無形的羈絆解放出來,新游牧族比絕大多數的人更更自由,更能享受世界主義的情感樂趣,和知識高度。
晴舫是不是新游牧族,恐怕她自己,她的朋友,尤其她的讀者都會有不同的答案。不過假設這個族群真的存在,而晴舫又真屬於這個族群,那麼晴舫在從一個和大家一樣安土重遷的定居族,轉變成新游牧族的過程中必然備嘗艱辛,也必然經歷了情感上的反覆糾葛。這些大概都是別人難以體會的。
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即使天賦神力如阿特拉斯,在背負起整個地球時,也需要找到支撐點。那麼一個在各種空間快速移動的作家如何去找她的施力點呢?缺乏適當的著力點,她又如何觀察從自身周圍到遙遠地區的大小事務呢?
這個問題有它的正當性,也有其褊狹處,隱藏在它背後某些簡單的假設尤其嚇人,那就是:一個作家/批評者至少必須認同一塊土地、一個民族、一種對歷史的觀點,甚至一些對這塊土地、這個民族未來的期望。換言之,這種對特定忠誠的要求,就是對新游牧族虛無主義的否定。
當然對新游牧族的各種定義,往往都失之過簡,很容易變成僵硬教條,變成鞭斥無根者的武器;從另個角度來說,這樣那樣的定義,充其量只是用以衡量世界的一種理想形態,一個分析工具,這個族群在真實世界中並不存在,存在的頂多是「類」新游牧族。
類新游牧族在不同程度上的確摒棄了相對簡單的民族觀與地域觀。這個族群習慣多層次、多角度、多重身分的思維方式,比較能夠洞穿表象,看出許多雜亂無章現象之間的關聯性,同時也能輕易指出表面上相似的事情卻不適合類比的理由。憂國憂民的我們老喜歡問「為何某某國能,台灣不能?」但是類游牧族會質疑,為什麼我們不能停止這種幾十年來從來沒有進化過的問題,為什麼我們沒有能力變得更周全嚴謹,為什麼我們不能站在更堅實的基礎上提出更繁瑣的問題。
如果類新游牧族還有母社會的話,他們容易對母社會毫無關聯的事務表示強烈的興趣,對母社會的觀察往往更坦率,更不留情,這種坦率與無情,總會造成忠誠者難以笑納,這樣的例子在晴舫的文集中俯拾皆是。
晴舫文章令人叫絕的地方在於,她總會給意見與興趣太容易趨同的台灣,帶來一陣陣錯愕。晴舫的意見未必人人同意,她對自己提出來的問題也未必有答案。但長期習慣以相同思維和共同意見彼此取暖的台灣社會,不正需要晴舫的震盪治療嗎?
序
胡晴舫 背德者的咕咕鐘
我個人向來偏愛「社會」這個詞彙勝過「國家」。
國家暗示了界線。一道邊界,將世界一分而二;要不在裡頭,要不在外頭。裡頭外頭,以意識型態砌高牆,拿文化偏見當盾牌,用政治語言當射箭,箭頭裹上種族主義的毒液,射擊每一名企圖越界的非我族類──不管由外入內或從內向外,任何一個方向都禁止。人類史上各種形式的衝突、鬥爭、戰爭與壓迫,大多為了捍衛那道劃分敵我的有形無形邊防。
社會卻像洋蔥。大社會包在小社會之外,小社會含在大社會之中,大小社會互相層層包裹,既獨立分瓣,又彼此依賴,形成一顆完美的圓球,像我們共生共存的地球。
超過兩人,就形成一個社會。而社會的成員可多可少,規模可大可小,組成方式可永久可臨時,種類各式各樣,不介意交集。家庭是一個社會,學校是另一個社會,教會是一個社會,公司行號是一個社會,張愛玲書迷俱樂部算一個迷你社會,每週固定騎車的單車車隊也是一個小型社會,坐在同間餐廳吃中飯的食客在那個時空之下臨時組成一個社會。一棟樓是一個社會,一條街是一個社會,有街有樓的城市是一個包含了這兩個社會的大社會;島嶼是社會,大陸是社會,一塊洲際是一個同時涵蓋了島嶼、大陸及海洋的廣大社會。網路社交媒體的小社會繁如眾星,有時為了某種議題,機動結合成為一個巨大的虛擬社會,從而改變實體社會。
社會像水,形狀不定,尺寸能大如海洋,也能微小如清晨玫瑰花瓣上的露珠,功能不斷變化,既能像寧靜無波的池塘,鎮日靜靜蓄養魚群,也能像萬馬奔騰的瀑布,擁有無所不摧的力量,即因它的組成分子是宛如水滴的一個人。這個「人」,會思考,會有多重興趣,會逐漸建立信念,會抉擇,會行動,因為利益、興趣,和共同價值,主動或被動加入以及退出某種社會,結果他身上便掛了許許多多不同社會,而這些大小規格不一、利益動機不同的社會便通過他產生關連,互通聲息。地表上看似分離的湖泊、水池、河流,皆來自源泉不絕的豐沛地下水,最終匯流奔向大海。
一個人可以是台灣某大學畢業,開二手書店,時常去北京出差,日日騎腳踏車上下班,關心兩岸事務,德布西樂迷,平時酷好攝影,因為妻子的緣故加入宗教慈善組織,因為兒子們同班而與銀行家成為好友,時時上網與住在非洲肯亞的三十歲印尼青年討論蝴蝶種類,念念不忘四十歲那年夏日的土耳其之旅。當他每天起床,便與大小不同社會發生關係,校友會、出版業、單車族、政黨、古典音樂界、攝影團體、家長會、宗教組織、網路社團以及印尼、中國、肯亞社會等等 。他流動於各個社會之間,遭遇其他水滴,有的與他類似或迥異,有的認同他,有的反對他,有的很快接納他,有的始終懷疑他。有他亟欲參與的組織,也有他勉勉強強加入的團體。當你把許許多多水滴灑在一面平滑如鏡的桌面上,然後轉動桌子,觀察一滴水如何滑過來滑過去,與其他水滴相撞相容相離,在我的想法裡,就像現代人典型的一天。
社會是人。利益會衝突,興趣會區隔,價值會對抗,其實也是人在衝突、區隔、對抗。然而,社會的形狀容許改變,邊界能夠移動,社會與社會之間互相重疊,因為作為社會最小單位的人會改變、移動,會跨界,身分重疊。水生性就會流動,發現道德的複雜往往是率先流淌過界的那個人。
一旦跨越邊界,便會發現道德的難處。當現代人的生活型態帶領他每日開門便必須穿梭於各個包含了他的不同社會,不斷越過有形或無形的界線,何謂道德,何謂不道德,與其他水滴如何相處,聯盟或分離、或若即若離、或互不相容但做到安然共生,便成為現代人一輩子的道德功課。
道德,其實就是如何正確生活下去這件事。雖然世上再沒有所謂的「正確」之「道」,然而,「道」意指道路,所有上了路的生命過客皆是未帶地圖的旅人,每遇上一個路口,都面臨抉擇。康莊大道,深林小路,車水馬龍的商業街,還是罕無人跡的密草原野,向左轉向右彎,看似簡單的個人念頭,卻是一個個深重的生命決定。而個體的生命決定,便匯集為集體的社會決定,就像桌面上的水珠終究都會融成一大灘完整的水。
道德在現代之所以困難,因為邊界消融,人類流動,單一社會的倫理習慣時時遭到挑戰,再也無法不經辯證,便理所當然強硬制約每個人。
你的道德,未必是我的道德;我欲堅持的道德底線,正巧踩在你的紅線上。資訊流通,權威不對等於威權,大小社會密密包纏,互重互疊,傳統文化習慣已不足以支撐新的社會倫理,事情已經不再是「他們」和「我們」那般單純,因為我既是他們也是我們,「他們當然就是邪惡的一方而我肯定是那個正義的代表」的道德邏輯根本行不通,一個人隸屬於不同社會,不同社會都對他提出一套道德期待與倫理要求,這些道德標準未見得統一,時時衝突,甚至對立,好人壞人的界線不再只是通過個人對團體的忠誠度來解決。當世界由神性過渡到人性,再沒有人全然純潔無瑕或道德完全正確,陣營分壘變得可笑。外在的自由勢必要通過內在的自由,一兩句詞彙漂亮的道德口號只會煽動無謂的情感,淪為彼此迫害的新理由,無法有效解決現代人的道德困境。
道德應該複雜,某些時候根本無解,因為道德其實是髒的。當你把一大堆來源不同的水滴全集在一起,你得到的並不是一桶清澈見底的純水,卻是顏色渾濁不明的汙水。人們帶著各自的欲望、生存的掙扎,在社會這塊公共區域打滾,就像河水奔流向海總免不了夾雜泥沙,大雨落到街面一定會混雜灰塵,從來不可能純淨,也不該純淨。
所以,混沌之世,究竟如何安身立命。
道德的變化,讀出人類的思想史,記載了歷來人類想要正確生活的努力。我們透過思索,去形塑道德,進而建造社會倫理,企圖在眼前迷霧中辨識出一條可行的道路。一個人只要活著,就無法放棄思索。因為無論活在任何時代,思想都是唯一的道德羅盤。
當回頭看我自己的寫作之路,我發現我也只不過在做一個「人」的本分,那就是思考。我思,故我在;我在,故我思。
而我每天在想的,無非僅是這麼做道不道德。亂丟垃圾,道不道德;使用核電,道不道德;官商勾結,道不道德;家族壟斷,道不道德;資本遊戲,道不道德;同性婚姻,道不道德;廢除死刑,道不道德;網路爆料,道不道德;尤其,道德霸凌,道不道德。
當道德不澄淨時,其實是渴望活得道德的正直之人最焦慮。無論是眼見傳統道德崩解而擔憂世界墮落的衛道之士,或認為世界始終沒太大長進而心焦如焚的新道德鼓吹分子。自認道德正當,會讓人正氣凜然,願意勇敢衝鋒陷陣,對他眼中的缺德者決無憐憫之心,欲除之而後快。因為他覺得他正從事一件偉大的社會工程,他在捍衛文明,像一名警察在維持秩序,不惜代價,願意採取任何手段,只為要求對方按照自己的道德規章。法西斯主義就是這麼開始的。所有的法西斯主義信徒骨子裡都是堅貞的道德分子。
我喜愛的英國小說家格雷安.格林(Graham Greene)從小接受傳統天主教教育長大,因而痛恨道德教條主義。他一輩子寫了五十幾本書,無論故事背景發生在越南、墨西哥、土耳其還是英國,每次主題都在辯證道德。在他的小說裡,自認終生道德的人會行為不道德而毫無自覺,一向活得不道德的人在緊要關頭卻做出最符合良知的道德決定。我從他的小說學到了最多道德教訓,譬如,愛會讓人不道德,因為愛本身就是一種道德。有時候,為了道德,你必須背德。
二戰終結時,格林寫了個劇本《第三人》(The Third Man),由好萊塢才子奧森.威爾斯飾演的角色「哈利」詐死,變成消失的第三人。好友來到維也納,卻只發現他失蹤了,仍鍥而不捨追訪他的行蹤,過程中逐漸發現這個從小熟識相親情同手足的老友竟然是一個壞事幹盡的惡徒。當好友終於找到了他,當面質問哈利為何轉行當壞蛋,哈利一派輕鬆微笑:「別發愁,其實事情沒那麼糟,義大利在波吉亞家族統治下,發生了戰爭、恐怖、謀殺及流血,但產生了米開朗基羅、達文西和文藝復興。在瑞士,他們有手足之愛、五百年的民主與和平,結果他們製造了什麼?咕咕鐘。」哈利的嫉俗觀點看來,道德的結果就是一只無聊的咕咕鐘,而人們口中的道德不過是一種假意清高的自私,隨時能遭金錢及求生本能所收買。
在善惡二元對抗之中,人們很容易感到厭倦不滿,受到哈利這類似是而非的魅力辯證所勾引。但我認為,格林又幫我上了一堂道德:世界的創造力源於人類的善惡掙扎。在群魔飛舞的亂世之中去堅持善的價值,在眾人流俗的盛世之中去拒絕善的教條。所謂的惡,就是不善,因為善不夠徹底或太過徹底,失去了檢討的能力,僵於形式,因此淪為惡的助力。不僅掙扎於善惡之間,善本身就是一種掙扎。
如果第三人就是置身道德之外的那個人,我以為,不是為了為求刺激而無事生波,而是為了不讓道德變成國王的新衣或權力的藉口,化身咕咕鐘裡那隻固定跳出來報時的咕咕鳥,提醒道德不是習慣,而是不放棄省思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