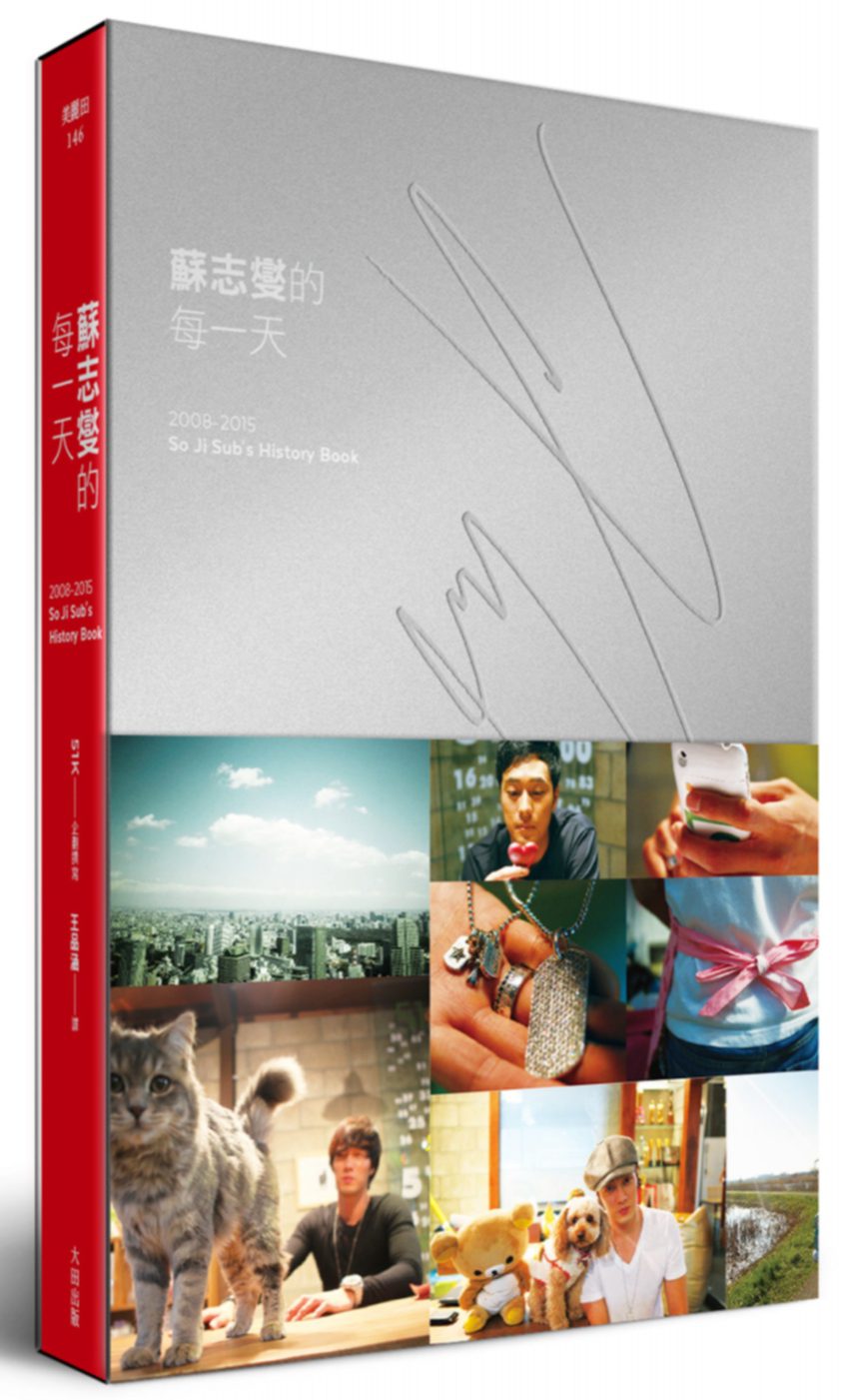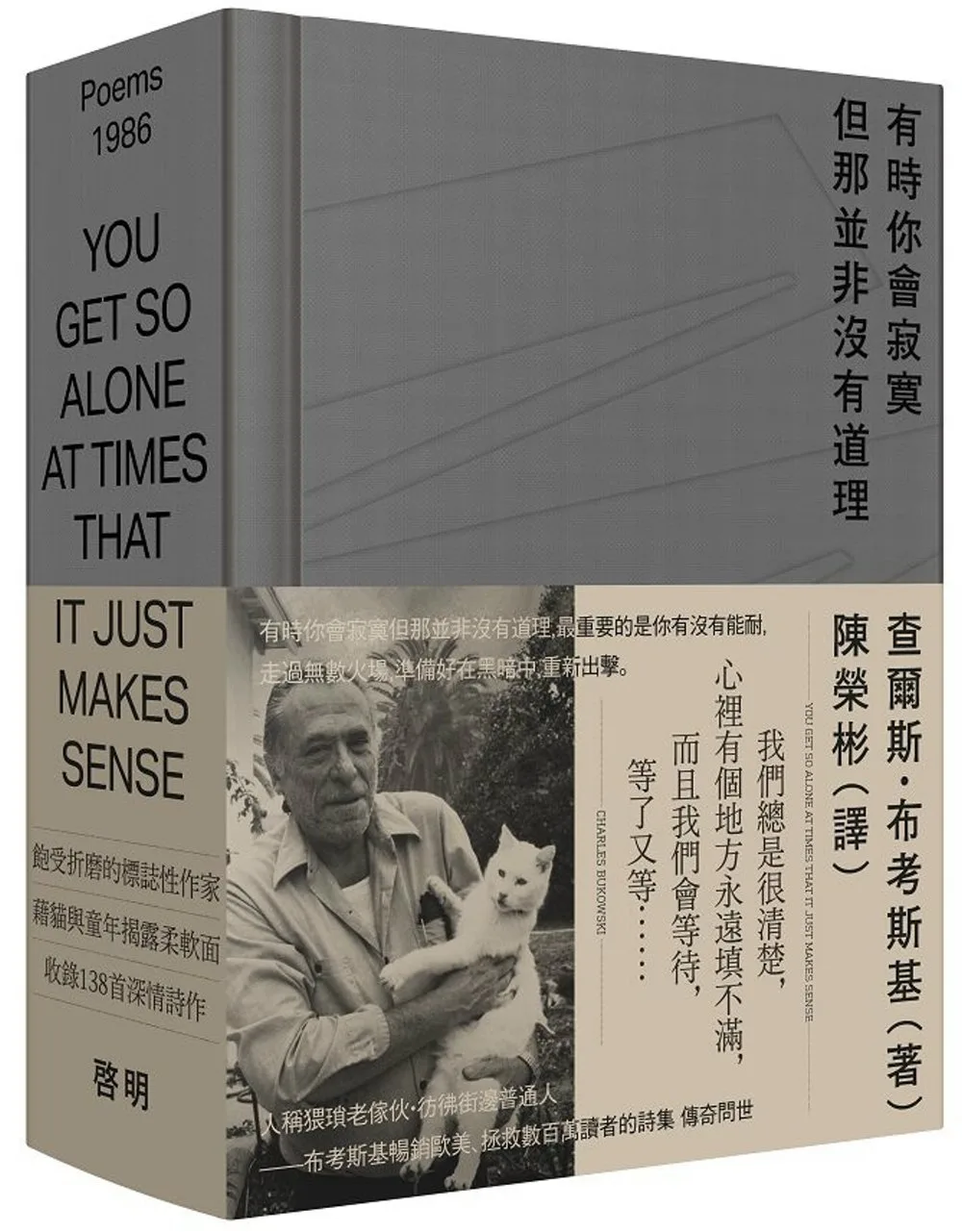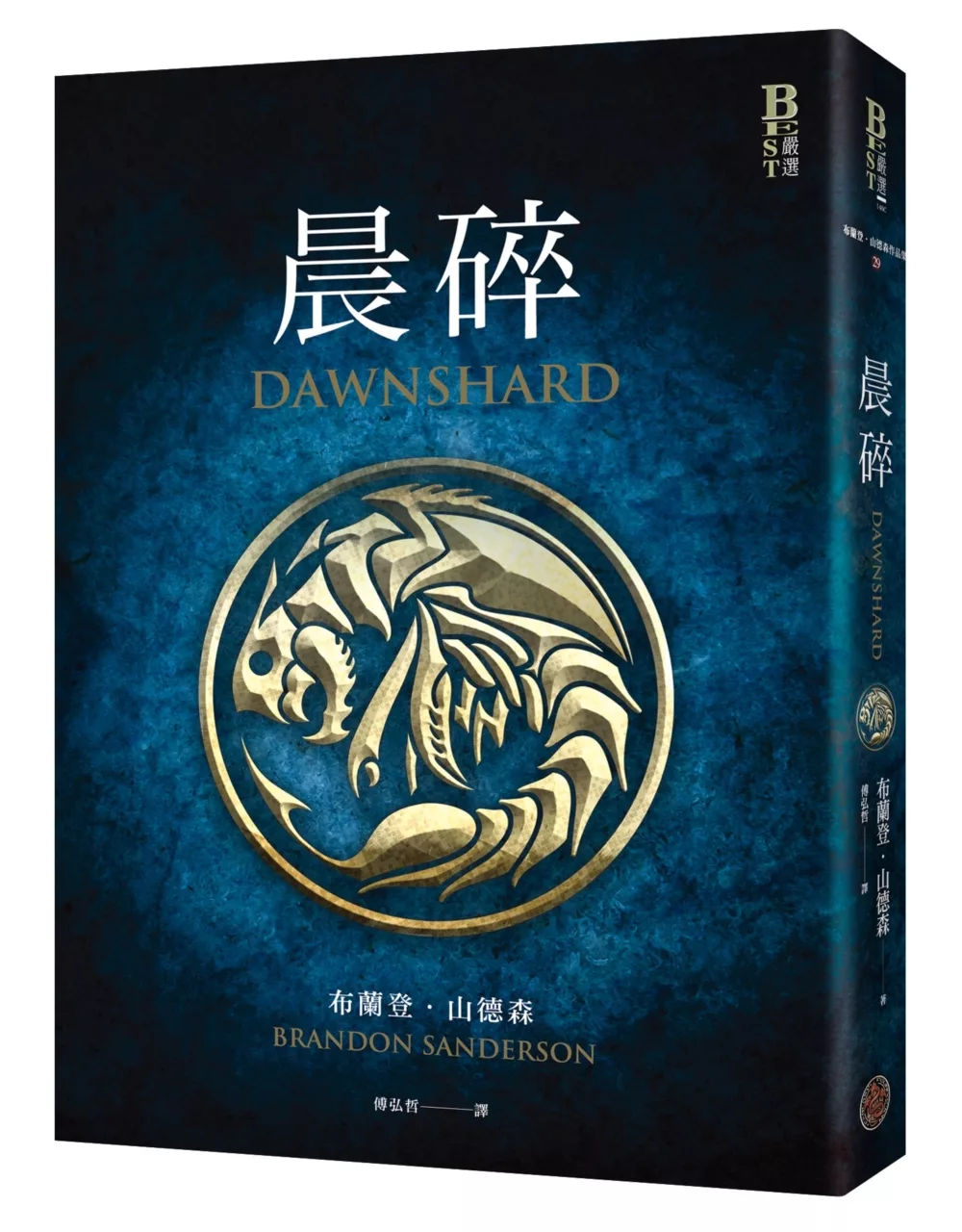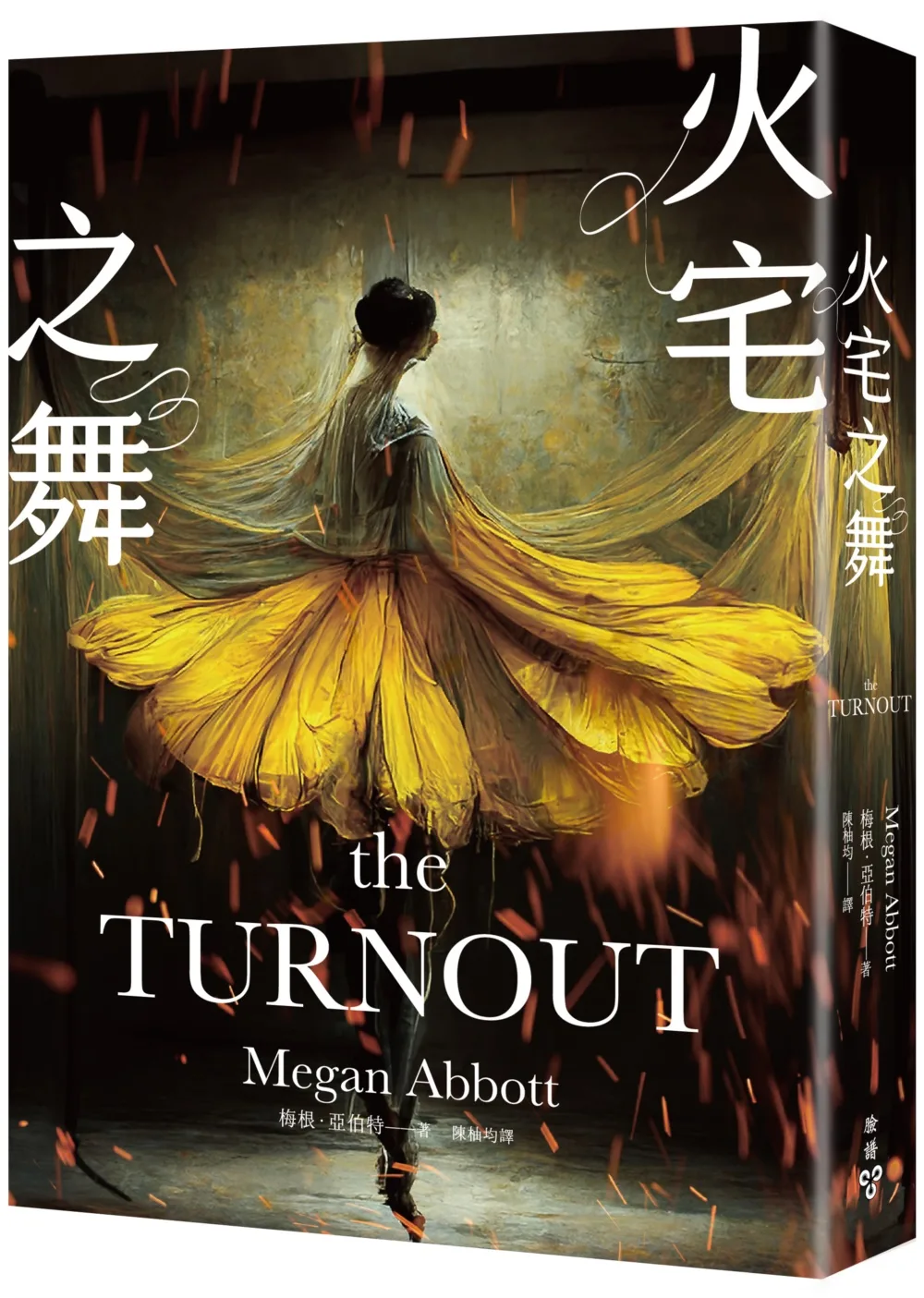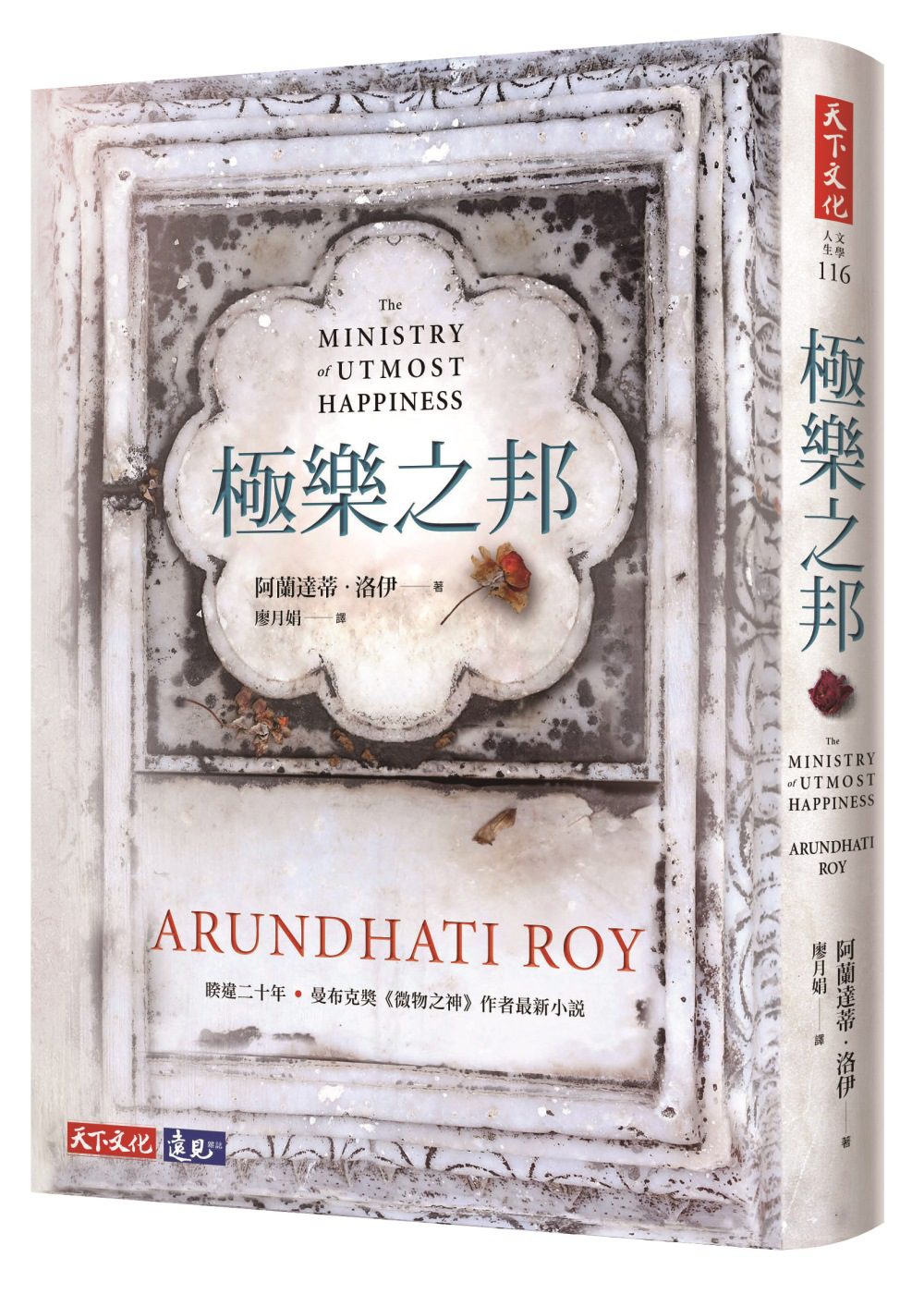導讀
禁忌之愛:《微物之神》的後殖民成長敘事
馮品佳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
一九九七年,是印度獨立五十周年的重要歷史時刻。阿蘭達蒂.洛依的處女作《微物之神》,也恰巧在一九九七年獲得英語文壇諾貝爾級的布克獎(Booker Prize),締造了印度文學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成為第一位獲得布克獎的印度在地女作家。洛伊因為《微物之神》在世界英文文學揚名立萬,而南印度克洛拉(Kerala)特有的地理人文風貌也隨著小說的暢銷呈現於世人眼前。《微物之神》最吸引讀者之處,在於洛伊以詩化的語言,將兒童與女性個人的創傷經驗與殖民主義所造成的創傷歷史並置討論,精確地再現後殖民女性懸宕於成長與反成長之間的矛盾與掙扎,透過後殖民的稜鏡折射出印度的種姓、性別與種族主義傳統所造成的歷史瓶頸。
《微物之神》的情節與敘事手法相當複雜,作者洛依雖是初試啼聲,卻嫻熟地透過層層環扣的情節,精確地表達各個角色的愛嗔慾望。小說以探討禁忌之愛與踰越禁忌所造成的後果為基調,出身基督教家族的阿慕為了逃避父權式的家庭與父親的家暴,貿然嫁給了相識不深的印度教丈夫,在生下一對雙胞胎艾斯沙與瑞海兒之後,無能的丈夫為了討好白人上司,企圖強迫她獻身給上司,導致她憤而離婚,走投無路之下只得回返娘家,受盡歧視。隨後阿慕又再度打破種姓制度的禁忌,與賤民階級的維魯沙發生戀情,造成姪女溺斃的「恐怖」事件(the Terror)降臨,導致整個家族的崩解。最後維魯沙被警察打死,阿慕失去戀人與兒女,含恨而終,而雙胞胎則自小即硬生生地被拆散,艾斯沙從沉默寡言到一言不發、自我消音,瑞海兒則事事不順、婚姻失敗。文本開始已是「恐怖」事件發生二十三年後,艾斯沙因為父親移民被送回外婆家,瑞海兒為此由美國回到印度,與失散多年的哥哥見面。
雖然洛依採用全知的第三人稱敘事手法,然而瑞海兒的成長故事顯然是小說文本的核心,文本一開始記述瑞海兒回到家鄉,試圖重新與艾斯沙建立默契、尋求雙胞胎身、心的重新合一。而《微物之神》中成長敘事的獨特之處,在於作者著意刻劃瑞海兒與艾斯沙這對異卵雙胞胎作為一體之兩面的重要。只有兩人心靈再度契合,否則兩者的心靈皆停滯不前,全無成長之可能。這種「雙重成長小說」(double Bildungsroman)的寫法,不僅是洛伊嘗試以文學手法探討雙胞胎之間奇異的靈犀相通,更可視為她對於印度社會男尊女卑之父權傳統的反動。儘管克洛拉因為特殊的基督教背景,女性較印度次大陸一般婦女來得獨立自主,文本中仍然處處可見父權淫威下男女不平等的發展。阿慕的母親是長期婚姻暴力的受害者;她自己更代表印度社會因為離婚導致喪失「法定地位」(Locusts Stand I)的女性。阿慕雖然個性剛強,卻無法逃出沒有地位的不安全感。她為了追求自由莽撞投入不幸的婚姻,離婚後更受盡冷諷熱嘲,最後甚至因為姪女之死被哥哥逐出家門。阿慕無法開展、青年折損的生命是許多印度婦女的悲劇寫照。然而透過七歲的艾斯沙在戲院遭到猥褻一幕,作者也讓我們意識到在不平等社會結構之下,弱勢族群難以倖免,即使是男孩亦難逃暴力的侵襲。
在《微物之神》眾多悲劇故事中,艾斯沙與瑞海兒這對雙胞胎兄妹被迫分離的情節最動人心弦,他們互相依存的心理情境,近似英國女作家與女性主義者吳爾芙(Virginia Woolf)所提出的「雌雄同體」(androgyny)理想。這對雙胞胎兄妹在童年創傷發生之前,雖然外貌各異,但是在內心深處兩人有如彼此融合的完整個體。誠如全知的敘事者所言:
他們是異卵雙胞胎,醫生稱他們為「雙胚子」,這是由兩個分開,但同時受精的卵生成的。艾斯沙——艾斯沙本,比瑞海兒早十八分鐘出生。
艾沙斯和瑞海兒不甚相像……。
混淆藏在更深入、更隱密的地方。
在早先那未定形的幾年,當記憶才剛剛開始,當生命充滿了開始,沒有結束,而一切都是永恆時,艾斯沙本和瑞海兒認為:在一起時,他們是「我」;分開時,他們是「我們」。彷彿他們是罕見的一對暹邏雙胞胎,身體分開,但本性卻相連。(10)
但是在小說敘事現在式的時空中,這種完整性早已喪失,童年的「樂園」因為外在時空的移轉而成為分裂狀態的「失樂園」,洛依也巧妙地透過瑞海兒成年後的觀點表達這種分離的狀態:
不管怎樣,現在她認為艾斯沙和瑞海兒是「他們」,因為分開時,這兩個人不再是以前的「他們」,或他們曾經想像過的「他們」。
曾經。
現在,他們的生命有了一個尺寸和形式。艾斯沙有他自己的尺寸和形式,瑞海兒也有她自己的尺寸和形式。
邊緣、邊界、分界線和界限,在他們個別的地平線上出現……。(11)
各種界線的出現,不僅喻示著「曾經」完整的個體在現實世界中橫遭分離,也表達出阿慕追求踰越疆界的失敗。作為阿慕的兒女,艾斯沙與瑞海兒默默承受這打破禁忌失敗的後果。
因此,就心理層面而言,雙胞胎的成長狀態始終維持在童年受重創的時刻,艾斯沙甚至表現出退化性的失語現象。至於瑞海兒,誠如修院學校的老師對她的評語:「她似乎不知如何當一個女孩子」(27)。即使結婚赴美,瑞海兒仍以空洞的眼神保護著分裂的自己,等待著「我們」的重新結合。文本中的成長敘事因此呈現一種懸置、延宕的狀態。唯一可以化解僵局的方式就是讓兩個曾經共存於同一母體子宮的身體透過肉體的接觸,讓心靈重新結合。因此在極端暗示性的寫法下,洛依選擇以另一踰越禁忌的行為——亂倫式的肉體結合——讓他們重逢。
雖然是驚世駭俗的亂倫之舉,洛依寫來卻格外溫柔。就某種層次而言,瑞海兒與艾斯沙的亂倫其實也可視為紀念母親的一種生命儀式。小說中的成長敘事呈現強烈的戀母之情,雙胞胎雖然想念父親,但是母親的愛才是他們生命的重心。《微物之神》中父母離異的情節是洛伊自身的寫照,而父親的曠缺也極具作者的自傳性。對於父母自幼離異的洛依而言,父親是個她不願提起的話題。同時,這樣自傳式的情節安排,也使得雙胞胎將對父親的渴望轉移至舅舅恰克身上。失去母親也是瑞海兒與艾斯沙成長停滯的重要原因。在他們以肉體重逢之前,他們一起在寺廟裡像童年一樣觀賞南印度傳統的卡沙卡里舞(the Kathakali),在充滿儀式性的表演中看到印度神話世界裡愛恨情仇的搬演,彷彿預示人世間的傷痛恩怨也應有一了結。敘事者告訴我們那一晚他們「所分享的不是快樂,而是可怖的憂傷」(393)。藉著再一次打破印度禮教所規範的「愛的律法,那種規定誰應該被愛,如何被愛,以及得到多少愛的律法」(393),艾斯沙與瑞海兒重蹈維魯沙與阿慕禁忌之愛的覆轍。這對「在生命開始之前……就相識」的三十一歲雙胞胎兄妹(392),以他們緊緊相擁的身體紀念享年僅三十一歲的母親。他們的身體重逢,也彷彿是以另一次禁忌之愛召喚母親、完成母親未竟之心願。
海瑞兒與艾斯沙驚人的亂倫之愛,反應出他們成長創傷之深刻劇烈,更反應了家族與國族歷史上的創傷。第一章結尾時,洛依指出這個小家庭悲劇實際上深植於印度的階級制度與殖民歷史。她用一段短短的文字回溯了數千年的印度歷史,以倒推的方式讓讀者回想社會主義,各種殖民勢力與宗教傳統,對於印度次大陸的層層衝擊。透過雙胞胎曾經留學牛津的舅舅恰克之口,「歷史」以極為具體的形象出現:
恰克告訴雙胞胎,雖然他不喜歡承認,但他們都是親英派,他們是一個親英家庭,朝錯誤的方向前進,在自己的歷史之外被困住了,而且由於足跡已經被抹除,所以無法追溯原先的腳步。他向他們解釋,歷史就像夜晚中的一棟老房子,一棟燈火通明的老房子,而老祖先在屋裡呢喃。(65-66)
恰克所言的「足跡已經被抹除」指得是印度賤民必須自毀足跡,以免汙染了其他高種姓行人的習俗。但是在恰克高度自覺的修辭話語中,自抹足跡的操作成為印度人民被英國殖民統治的轉喻。此處,洛依不避諱地指出印度之於英國,就如同賤民之於其他種姓。
但是年幼的雙胞胎卻對於恰克矯飾的比喻另有體認,而以他們兒童豐富的想像力在鄰近地區找到一棟真正的「歷史之屋」:
艾斯沙和海瑞兒完全相信,恰克所說的房子是河對岸,位在他們不曾去過的荒廢橡膠園中間的那棟屋子、卡利賽普──「黑薩伊」──的房子。「黑薩伊」是一位「本土化」的英國人,說馬里亞勒姆語,穿芒杜,是阿耶門連的寇茲,而阿耶門連就是他個人的「黑暗之心」。十年前,當他那年輕戀人(一個男孩)的父母拆散他們,並送他的戀人去學校時,他便朝自己的腦袋開槍了。「黑薩伊」自殺後,他的廚子和他的秘書為了他的地產不斷地對簿公堂。房子荒廢了好幾年,很少人看過它,但是雙胞胎可以想像它的模樣。(66)
「黑薩伊」代表的是同化的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發生了不見容於社會規範的同性戀情。此處「黑薩伊」的悲劇故事與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著名殖民主義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互文指涉,南印度的阿耶門連也在這文學性的指涉裡成了非洲那樣的「黑暗大陸」。
洛依的「歷史之屋」可謂鬼影幢幢。本文中的愛與死以及雙胞胎成長中的創傷皆源於這幢「歷史之屋」。在那棟屋子裡,阿慕與維魯沙「身體力行」他們的禁忌之愛,雙胞胎與來自英國的表姊蘇菲也想在那兒尋找避難的庇護所,結果蘇菲不幸在渡河時溺斃,而維魯沙因為阿慕家人的誣告被警察毆打成重傷致死。二十多年之後,「歷史之屋」成了五星級渡假勝地,改名「遺產」(Heritage)。對於雙胞胎而言,他們必須學習面對歷史的「遺產」,正是創傷造成的失語與空虛。洛依並藉由感官的知覺描畫這個歷史的教訓:
當和他們一樣大的孩子,還正在學習其他事物時,艾斯沙和海瑞兒正在學習歷史如何議定它的條件,並向那些違反其規則者徵收它應得之物。他們聽到它令人作嘔的沉重腳步聲,聞到它的味道,而且永生難忘。
歷史的味道。
就像微風中即將凋謝的玫瑰的味道。
那味道將永遠潛伏在日常事物之中,潛伏在掛外套的鉤子上,潛伏在番茄裡,在路上的焦油中,在某些顏色裡,潛伏在餐廳的盤子上,在沒有話語的靜寂中,潛伏在空茫的眼睛裡。(68-69)
這棟「歷史之屋」/「遺產」即是克洛拉的「黑暗之心」,作者透過沉重的反諷檢討印度殖民的歷史傳承以及這「遺產」對於印度子民的重大影響。就此層面而言,雙胞胎創傷的雙重成長敘事,更可作為印度兒女生命故事的換喻。洛依以雙重成長小說的方式,刻畫印度女性的社會地位與殖民歷史的痕跡,文本雖然不是專注女性,卻也為女性成長敘事開創新局。
《微物之神》以雙胞胎童年的創傷開始,小說結尾卻回到阿慕與維魯沙第一次在「歷史之屋」相會、相愛的時刻。從童年開始,維魯沙巧手做出的小禮物安慰著阿慕寂寞、壓抑的心靈,也使得維魯沙成為她生命中的「微物之神」。這兩個種姓懸殊的戀人在肉體結合之後,清楚地知道他們必須面對社會與傳統的撻伐,因此他們只能「直覺地抓住渺小的事物」,因為「龐大的事物永遠潛伏在他們裡面。他們知道他們沒有地方可去,他們什麼也沒有,沒有未來。因此,他們緊緊抓住渺小的事物」(406),把希望寄託在明天再見這渺小的願望上。短短兩周的禁忌之愛,造成蘇菲與維魯沙喪生以及雙胞胎二十三年的生命懸置——「兩條生命,兩個孩子的童年」(404),代價不可謂不高。但是這樣以愛結束小說的方式卻帶來一種普世的希望,讓我們感受到在殖民歷史、社會階級等等各種現實層面沉重的壓力之下,能夠把握「渺小的事物」即是幸福。這種超越國界、謙卑卻又理直氣壯的追求幸福,也正是《微物之神》能夠打動全世界讀者,成為印度當代英文書寫經典之作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