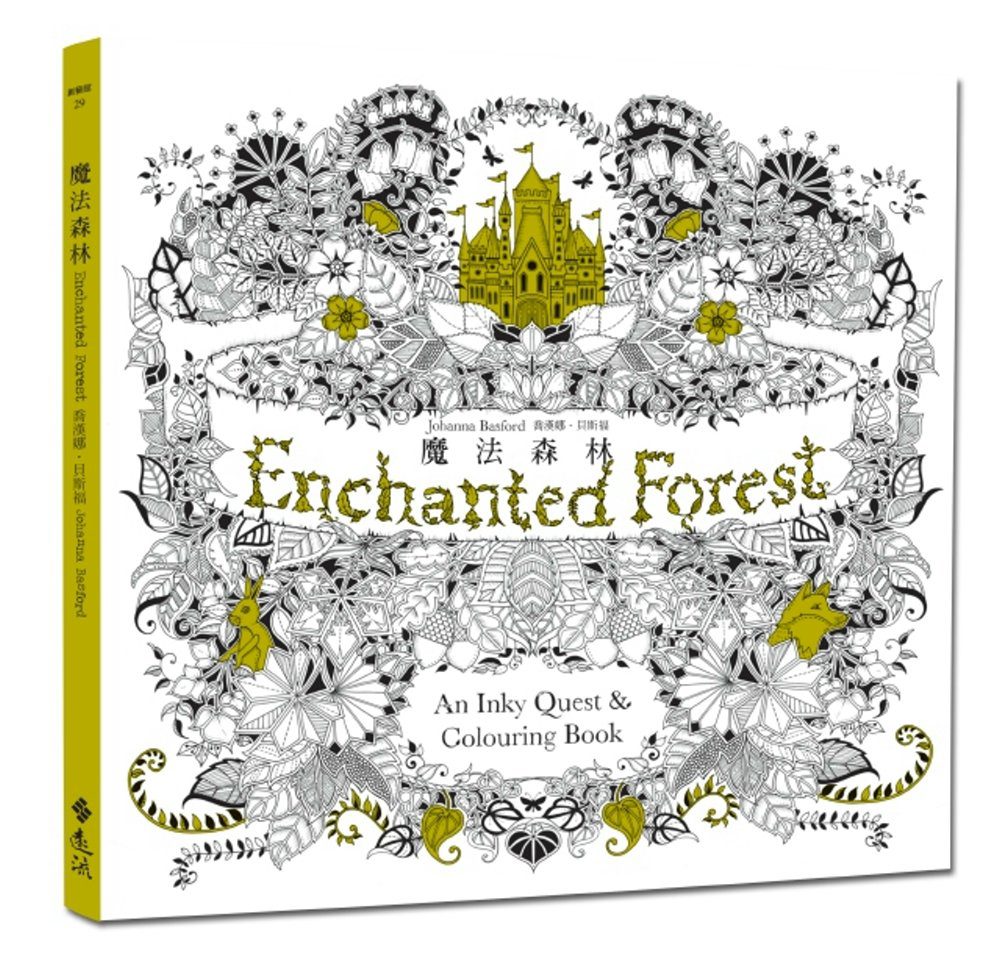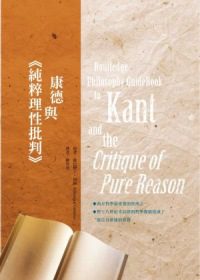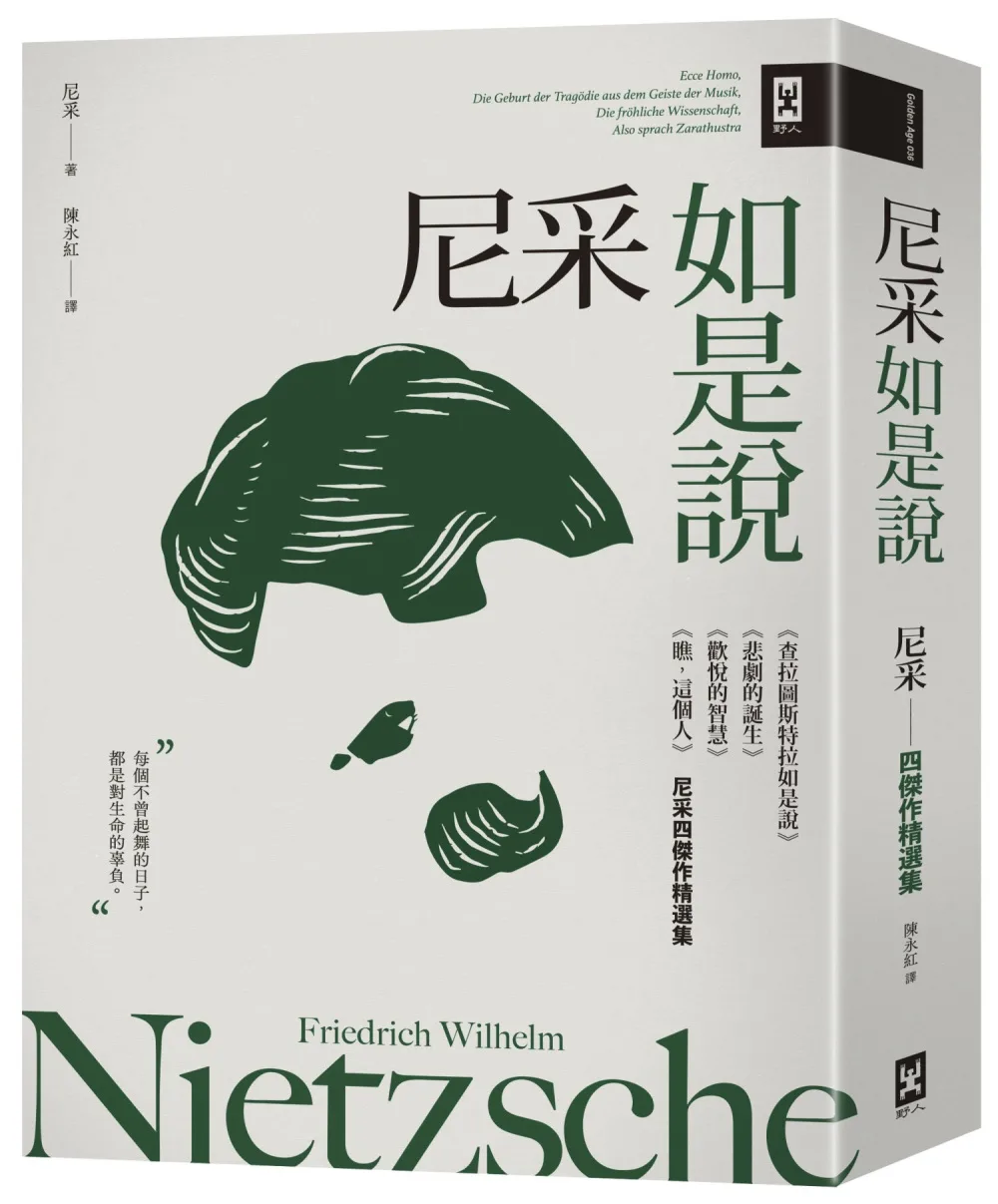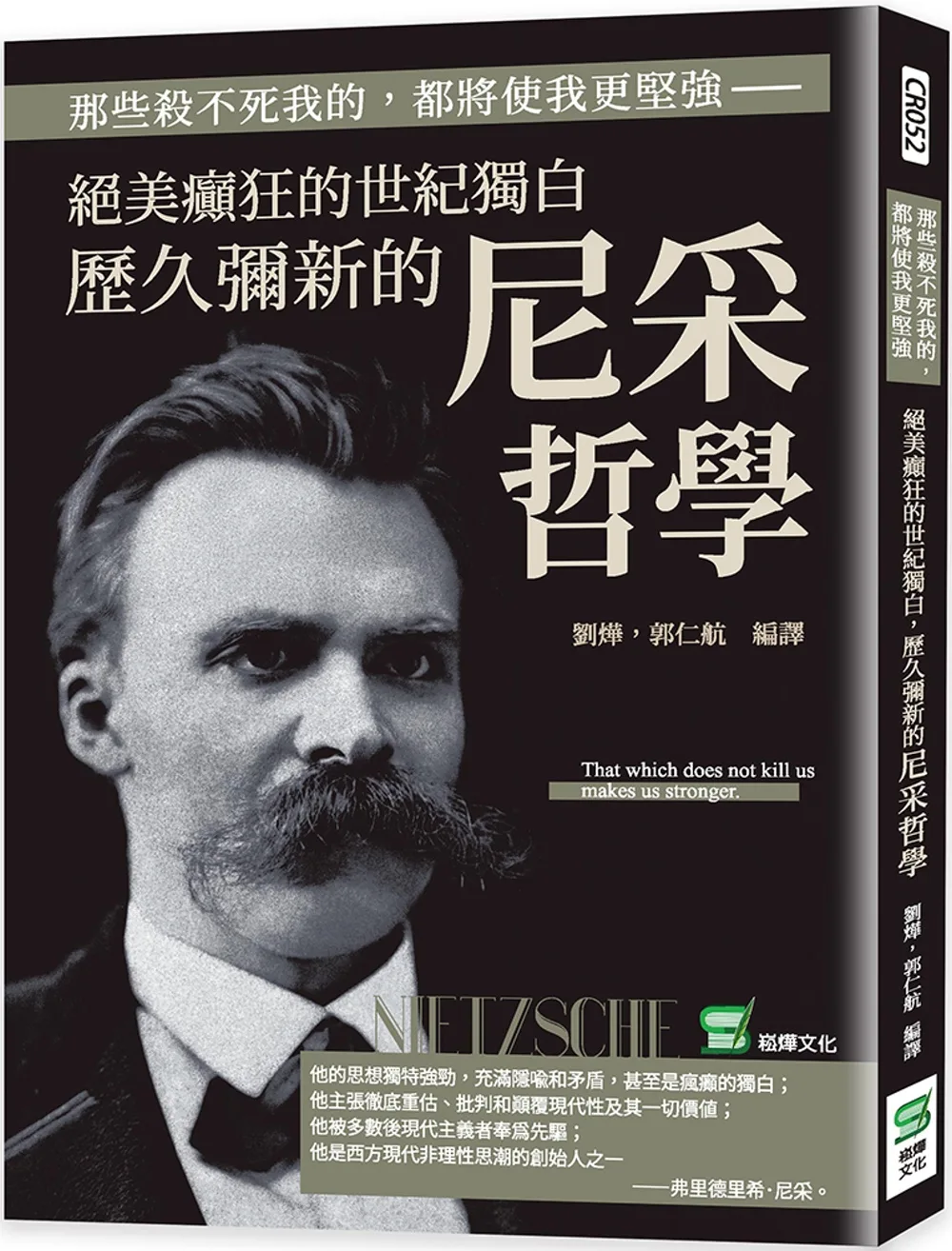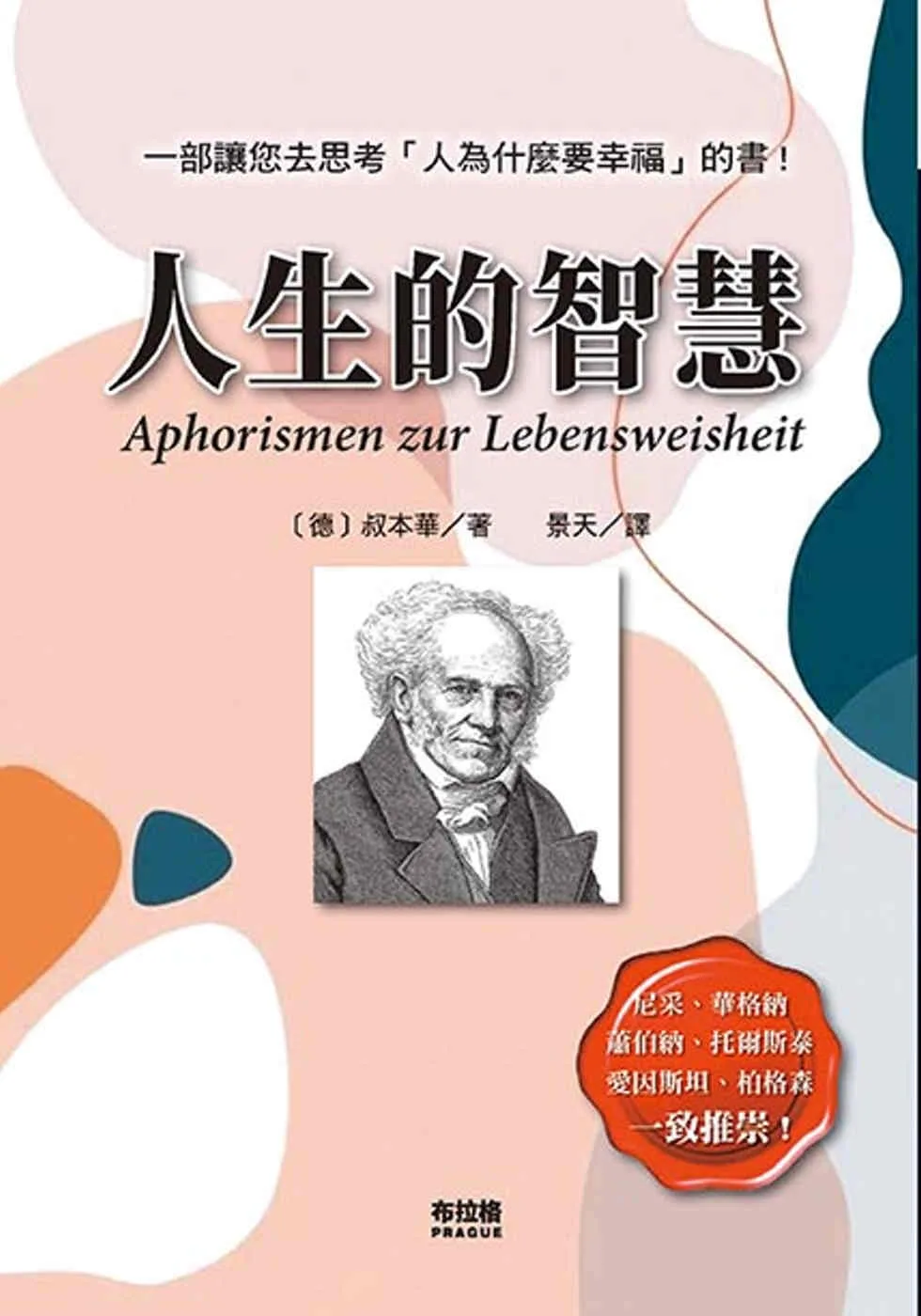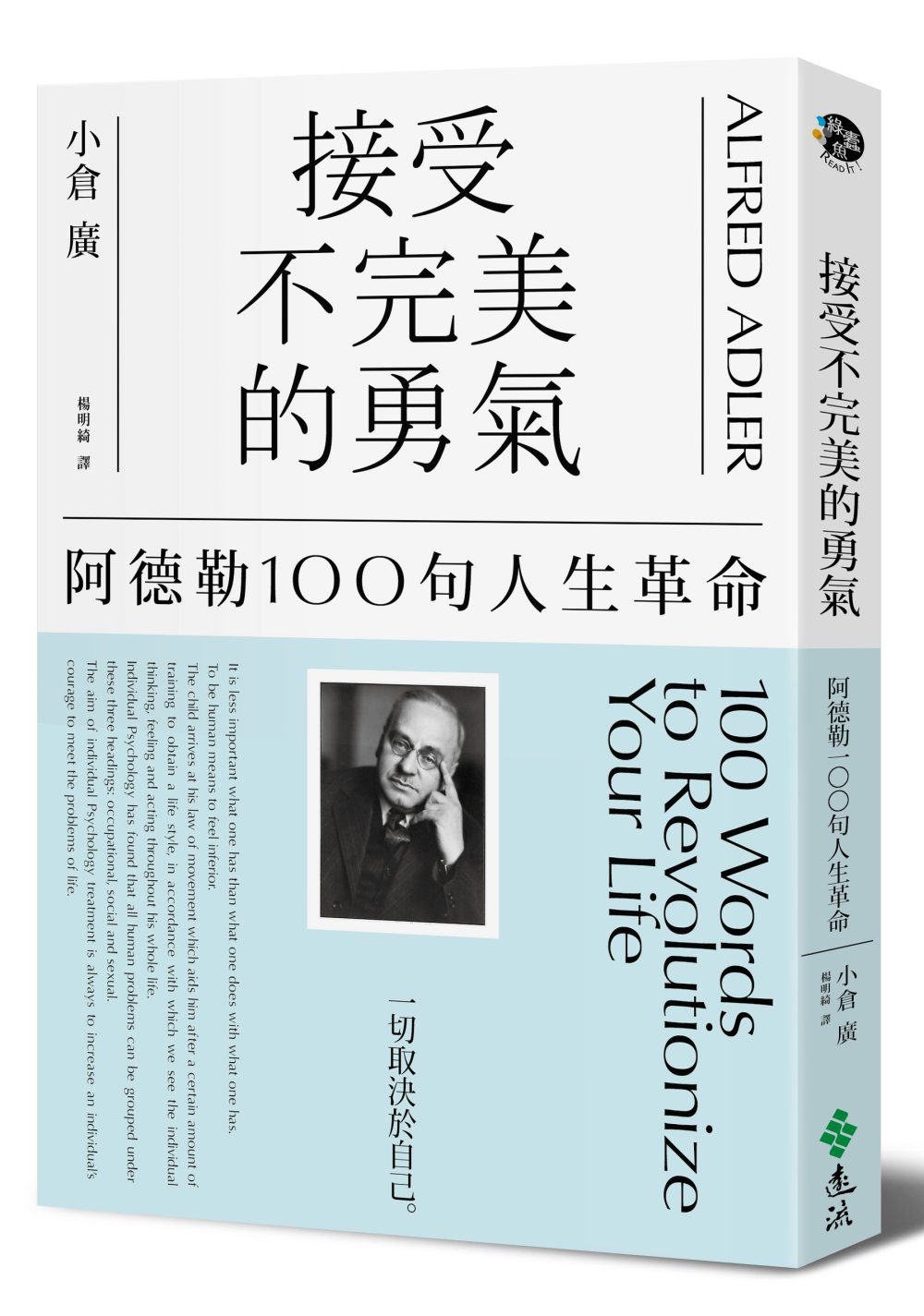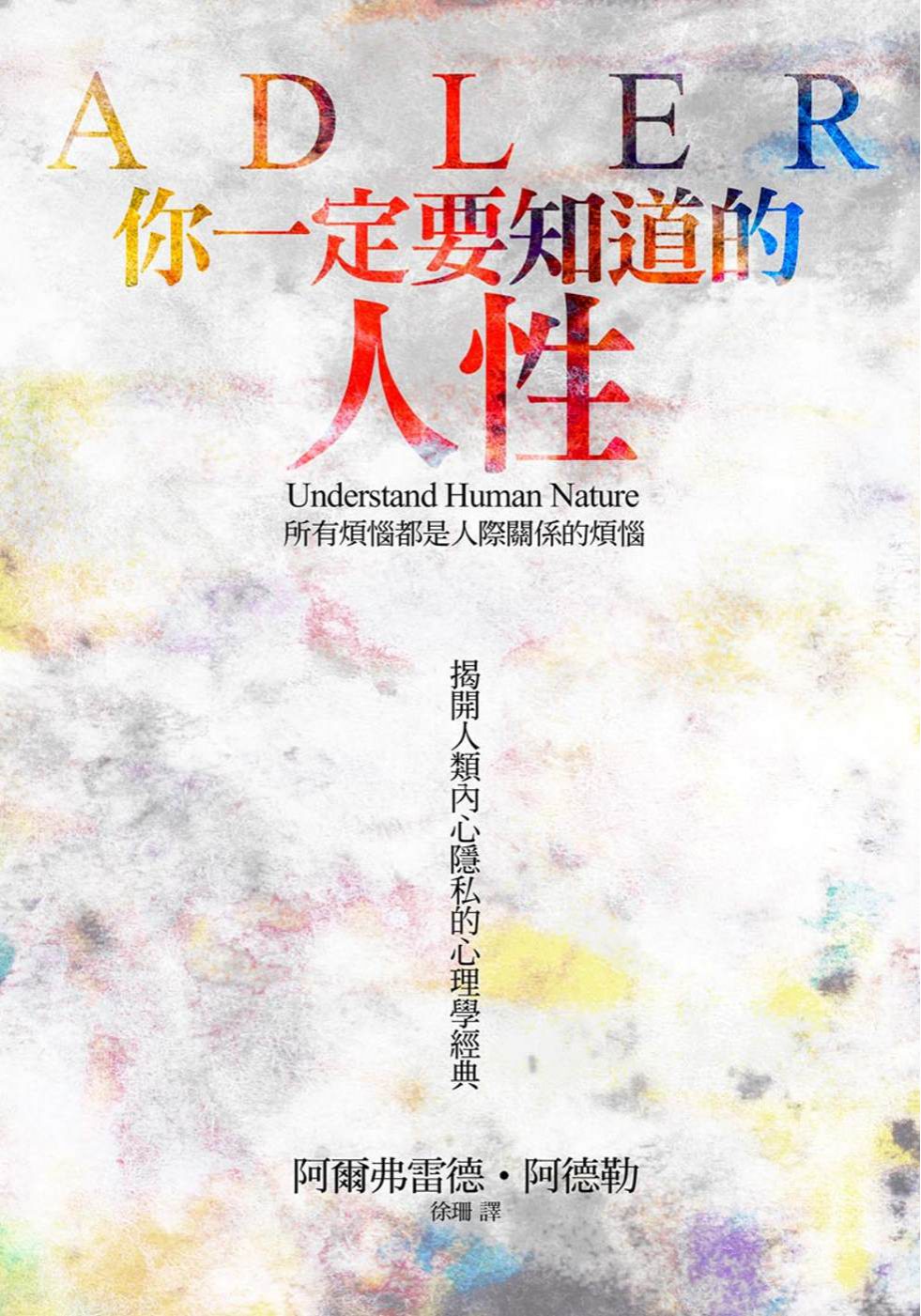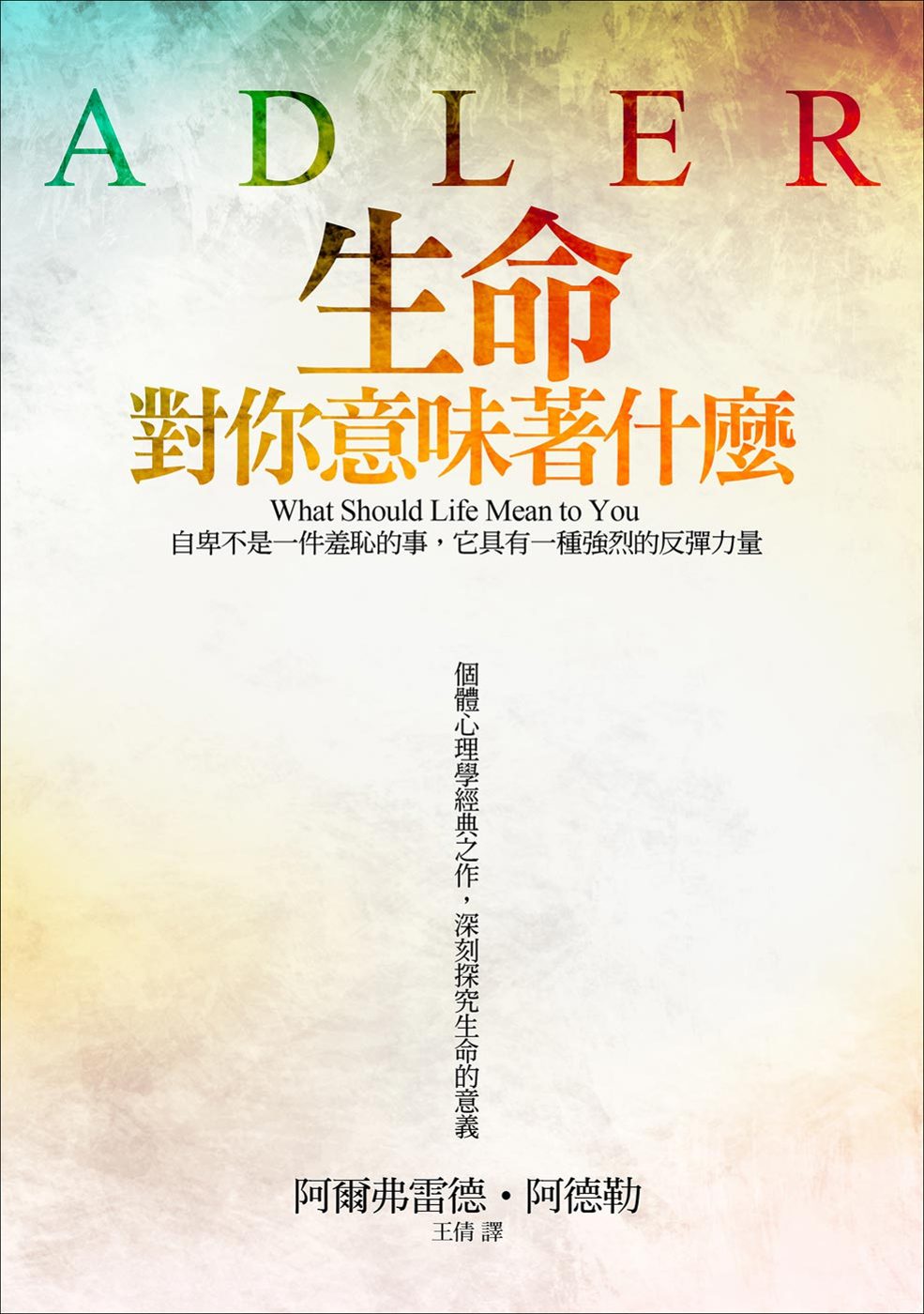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後文簡稱《批判》)出版了兩個版本,而兩者之間有些重大的差異。在N. Kemp Smith的譯本(第二版,London: Macmillan, 1933)中,兩版本是交錯在一起的,其中頁緣「A」編號的部分是指第一版,而「B」編號的部分則指第二版,兩者都對應到德文原文的頁碼。本書的引文便是出自這個譯本,它至今在英文的康德評註中已被當作標準本來使用。近來則有兩本《批判》的新譯本問世,一是由W. Pluhar所譯的(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另一是由P. Guyer和A. Wood所譯的(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本書也引用康德的《未來形上學之序論》(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簡稱Proleg)(J. Ellington譯,Indianapolis: Hackett, 1977)、《實踐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簡稱CPracR),以及《道德形上學的基礎》(Gr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簡稱Gr)(由M. Gregor翻譯和編輯,收錄在康德的Practic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判斷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簡稱CJ)(W. Pluhar翻譯,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以及康德的《哲學書信集》(Philosophical Correspondence, 1759-99)(A. Zweig編輯和翻譯,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本書從這些著作中所引用的材料是取自於這些版本,而所有的引用都按照頁緣的頁碼。康德著作的德文標準版本是普魯士學院版的,由普魯士科學院編輯的《康德全集》(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Berlin: Georg Reimer,後繼者是Walter de Gruyter, 1900- )。此著作的引用形式是在Ak後加上卷數和頁數。關於像是〈第一個類比〉、「第四個誤推」這些康德的術語,當指《批判》的章節時,會用大寫字母,而當指該書在那所給出或討論的論證時,則用小寫。
我們無法假裝《批判》的散文體對我們會立即產生很大的吸引力,正如詩人海涅所說的,它有著「平淡無趣、枯燥,如包裝紙般的文體」以及「生硬、抽象的形式」。康德自己也曾敏銳地意識到這部著作的文體限制,而以《批判》所包含的東西需要十分專門的術語為由來替它辯解。康德的哲學遣詞造句是繁複且令人感到陌生的。它不完全由新的術語所寫成,因為康德所使用的種種術語都是取自先前的哲學來源和其他(數學、法學的)來源,但我們卻無法在康德的文本之外去尋求那些術語的意義。對於《批判》的文體和術語所呈現出的困難,唯一的解決之道就是再三摸索。
我應該在開頭稍微說明一下本書對於康德哲學所採取的進路,但願這麼一來,不熟悉《批判》與對它的評論的讀者就能了解,此進路和許多其他可能採取的進路有什麼不同。
這本書反應了Henry Allison、Karl Ameriks、Richard Aquila、Ermanno Bencivenga、Graham Bird、Gerd Buchdahl、Dieter Henrich、Arthur Melnick、Robert Pippin、Ralph Walker、Wayne Waxman和其他人對康德的理論哲學的研究,其中大部分是近二十幾年來的成果。這些作者並未表現出一種對康德哲學的單一觀點,但他們卻分享了同一個看法,那就是他們都同意康德先驗觀念論的形上學絕不只是一件哲學史中的珍奇古董,而(至少)是一項極為有趣的哲學計畫。為了提供一個把這些近來研究納入考量之對《批判》的導論,本書強調先驗觀念論學說的基本部分、具體內容以及種種涵義,並且也試著突顯出它的長處。於是應加以強調的是,我們在對康德的評註中可以發現一條全然不同的路線,據之先驗觀念論並不是一個融貫的學說,《批判》的成功之處在於一組在形上學上是中性的,但在知識論上是強而有力的論證,這些論證帶著或多或少的困境,而可與它們觀念論的環境孤立開來。這派學說的經典著作是P. F. Strawson的The Bounds of Sense: An Essay on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London: Methuen, 1966)。最近Paul Guyer也替類似的結論辯護。我已注意到這種進路,但這主要是為了對照,而沒有要呈現出所有的說法。
本書採用這種閱讀《批判》進路的另一個理由是基於這種進路的導論特性。《批判》的每個句子幾乎都對讀者帶來困擾。許多人曾試圖提供註解以全面說明該著作的每個個別部分,但其中由於有些註解分散在幾本書中而未達到其目的。一個簡要的註解希望做到的頂多是傳達康德在《批判》所說內容的概略圖像,它將對個別部分的研究提供一個架構,更重要的是,它將使這個任務似乎成為值得繼續進行的。強調先驗觀念論這個主題似乎也符合這個目的。
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書無法追究其他一些詮釋上的問題。我略去了大家熟知的拼湊理論(patchwork theory)。在一些評註者(最著名的是Norman Kemp Smith的英語評論)的看法中,《批判》的文本應被視為集康德哲學發展中不同階段所撰重要部分之大成,康德成熟的「批判式」觀點的結論需要一種詮釋學式的考古學。本書這種解讀文本的進路在現今不太受到支持。更為冒險的是,我沒有將焦點放在我們有可能辨認出《批判》的兩個版本是迥異的、不一致的哲學圖像上面,而是在《批判》並非如此的假定上來進行評註,這個假定也應被認為是可受到挑戰的。
關於這本書的架構有一點要加以指出。正如目錄所示,本書以兩個不同的章節論述先驗觀念論。第一個章節(本書的第五章)旨在給出該學說的內容,及康德對它的辯護;它所討論的唯一重要議題是有關〈感性論〉的那些論證。至於那些沒有掌握〈分析論〉就不能思考的其他詮釋性與批判性的問題,則在討論先驗觀念論的第二個章節(本書的第八章)著手進行,這部分更為複雜,我在其中也對如何理解康德的立場提出了一些建議,儘管我不希望給人一種如此簡短的討論就能充分了解那個主題的困境為何的印象。
我對《批判》的說明大部分是彙集上文所列作者著作中,讓我覺得最具啟發性的內容而形成的,特別是Henry Allison的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與Robert Pippin的Kants Theory of Form: An Essay on the?ritique of Pure Reas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這些研究本身作為一種哲學探究的形式,對於哲學史極有助益。本書的形式導致它不可能鉅細靡遺地記錄我受惠於他人的部分;最後面參考書目中的這些著作是從提供讀者一條進入二手文獻途徑的觀點而選出的,不必然對應到我的討論中所利用的材料。
我要感謝 Jo Wolff 邀我寫這本書,Maria Stasiak 和 Routledge 的編輯人員在準備階段的幫助,以及柏貝客學院(Birkbeck College)哲學系提供我研究假期讓我能夠完成它。我很感激Mark Sacks 對完稿提出詳細的評論,而給我去除許多哲學上的錯誤並試著改正許多缺失的機會。我也要感謝 Graham Bird、Eric James 和 Tim Crane 的評論和建議。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在我撰寫一本沒有圖畫的書的期間始終予以支持。
中文版序
在我寫本書的時候,英語世界哲學家之間對康德的一波興趣顯然沒有減弱的跡象,如果我藉此機會記錄這過去十年間問世的一些出版品,或許對讀者會有所助益。
劍橋大學出版社即將完成多本英文翻譯的康德作品全集;每本都包含了編輯者所提供的充分資料。它將包括所有康德已出版的著作與他未出版的著作選集,包括康德的《遺著》(Opus Postumum)、講稿、書信以及遺稿札記(Nachlass)。
有一個對搜尋非常有用的助手是可以從InfoSoftWare(Karsten Worm)取得的Kant im Kontext II: Komplettausgabe 2003這個光碟,其中除了所有已出版的康德著作外,還包含了康德的書信與遺稿札記。
由Georg Mohr, Jurgen Stolzenberg和Marcus Willaschek所編輯的三本 Kant-Lexikon(Berlin: Walter de Gruyter),其中包含了許多國際康德學者的苦心成果,現在正準備出版中。它將會取代Carl C. E. Schmidt的W顤terbuch zum leichten Gebrauch der Kantischen Schriften(1786)與Rudolf Eisler的Kant-Lexikon. Nachschlagewerk zu Immanuel Kant(1930; 1977由Olms重新印行)這些較舊的辭典。新的辭典也有電子書的形式可供利用而使我們能輕易查閱康德的文本。
對整個康德哲學的新的傑出導論有兩本,分別是Paul Guyer的Kant(London: Routledge, 2006)和Allen W. Wood的Kant(Oxford: WileyBlackwell, 2004)。Graham Bird所編的那本A Blackwell Companion to Kant(Oxford: Blackwell, 2006)中則包含了對康德哲學的論點與系統性方面幾篇精簡的論文。
Henry Allison第二版和修正版的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修正且在幾個方面擴展了第一版的範圍。Allison同時擴充了議題的範圍並詳細檢閱了第一批判的文本章節,且說明康德的先驗觀念論如何是他看待知識論和形上學論點所不可或缺的。Allison對〈先驗分析論〉的討論含括了範疇的形上推證和〈第三個類比〉,並增加〈對觀念論的駁斥〉和先驗觀念論兩者關係的說明(這個主題使Allison與Paul Guyer交手,對Guyer來說,〈駁斥〉代表康德把他的哲學帶出先驗觀念論的種種桎梏之最後成果。)此外,這本書以兩個新章節作結,一是關於〈純粹理性的理想〉,另一是關於理性的規制性角色,這反應出Allison對辯證幻象看法的轉變,他承認這是受到Michelle Grier的Kants Doctrine of Transcendental Illus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的刺激所致。
隨著Rae Langton的Kantian Humility: Our Ignorance of Things in Themselv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一書的出版,關於先驗觀念論可能採取的立場範圍業已擴大了。Langton把先驗觀念論的關鍵之處視為是一個論點,即我們關於顯象的知識乃是關於物自身一組種種關係性質的知識,物自身的種種內在性質對我們來說是未知的且不可知的;這是一種讓康德與洛克和萊布尼茲有密切關係的詮釋。
Karl Ameriks重要論文集Interpreting Kants Critiques(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3)替一種對康德意圖的審慎詮釋加以辯護。Ameriks的著作在下列這個深刻且困難的問題上特別有價值,這個問題是關於最終引進康德哲學所努力的形上學:康德的批判哲學是否意味著形上學的終結,它為老的、理性論式的形上學微幅修正的版本提供了一個新的基礎,抑或形上學也許是以一種新的形式重生。Ameriks傾向於第二種看法。這個問題與康德的實踐觀點的構想,以及其中可使用的「實踐認知」(practical cognition)密切相關,我已在Bird編輯的A Blackwell Companion to Kant中(第259-274頁)以「實踐理性的優先性」來闡明過這個連結了。
對核心的康德式論點的一個著名的且在哲學上雄心勃勃的看待方式是由Mark Sacks的Objectivity and Insigh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2000)所提出的。Sacks在該書第二章中提出一個關於康德的嚴密歷史討論,那本書整體來看是對先驗觀念論以及〈先驗感性論〉和〈先驗分析論〉的先驗立論加以辯護和重建。Sacks替先驗觀念論所作的辯護或許可以富有成效地與Adrian Moore在Points of Vi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對於該學說那種負面的、維根斯坦式的評價作對照。
Beatrice Longuenesse在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Sensibility and Discursivity in the Transcendental Analytic of 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 Charles T. Wol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對〈先驗推證〉的核心論點提供了深刻且精細的說明。Longuenesse的種種觀點在Kant on the Human Standpoi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有進一步的闡述。
我在第十章所提出的對康德理論哲學和德國觀念論和後康德廣泛承繼者關係的思考,不僅提供了一個有高度歷史興趣的領域,也提供了一個引起關於康德知識論和形上學種種最深層系統性問題的架構,這已在英語的哲學世界發展為一個豐富的研究領域。在此領域特別值得關注的晚近研究成果包括有Karl Ameriks的Kant and the Fate of Autonomy: Problems in the Appropriation of the Critical Philosoph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Frederick Beiser的German Idealism: The Struggle Against Subjectivism, 1781-1801(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aul Franks的All or Nothing: Systematicity, Transcendental Arguments, and Skepticism in German Idealis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以及Dieter Henrich的Between Kant and Hegel: Lectures on German Idealism(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Terry Pinkard的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則對直到德國觀念論和超出德國觀念論的後康德哲學發展提供了一個詳盡說明其歷史且具有哲學系統性的看法。
位在康德歷史發展的另一端,我們對於康德前批判時期的幾本著作,以及它們和《純粹理性批判》的關係和連續性的理解已經透過晚近的研究成果得到深化了,尤其是Martin Schonfeld的The Philosophy of the Young Kant: The Precritical Projec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和Eric Watkins的Kant and the Metaphysics of Caus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