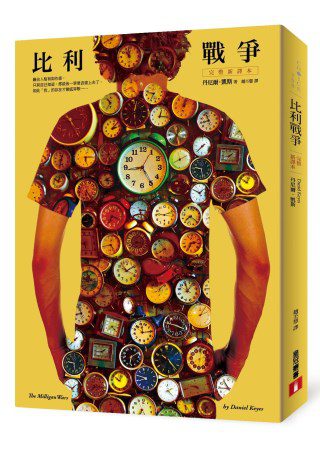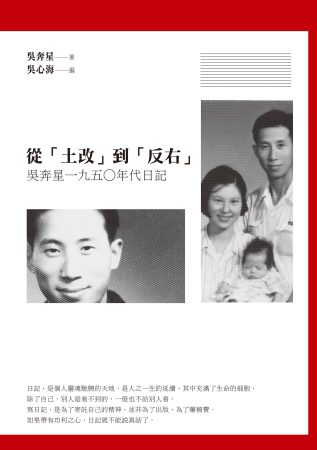理解現實中國的鎖鑰
──讀『毛澤東最後的革命』
文/楊照
麥克法夸爾教授在『毛澤東最後的革命』的自序裡輕描淡寫地說:
「......我到哈佛任教,一位非常傑出的歷史學家要我在哈佛核心課程的『歷史研究B』門類中,開設一門有關文革的課程。......這門課出人意料地受到了歡迎。」
麥克法夸爾話說得真低調,完全沒有提到他在哈佛開的「文化大革命」,一度是全校註冊上課人數最多的課程,多到什麼程度呢?多到要讓所有學生齊聚一堂聽講,只能動用學校裡平常辦音樂會、上演舞台劇的「山德斯劇院」!即使扣掉必然會有的翹課學生,每當「文革」上課時,「劇院」門口總還是有幾百個學生必須耐心排隊等候入座。
還不只如此,八百個修課的學生除了聽講,依照規定還得分班定期討論,一分下來至少得分三十個討論班,每班需要一位助教,於是那幾年,「文革」課是哈佛中國史研究生的重要財源,大家都可以到麥克法夸爾教授班上謀個助教教職,靠助教薪水支應生活費用。
八○年代後期,我在哈佛見證了「文化大革命」課程驚人的轟動程度,也就不斷地在心中疑惑:為什麼?為什麼發生在中國的一場動亂,在這些學生出生前開端,而且也結束了十幾年,卻能夠吸引這麼多美國大學生爭先恐後登記聽講?
麥克法夸爾教授當然有其風采,但光靠他上課的表現,不足以解釋這個現象。有一年,通識核心課程排出了一門不可思議的「夢幻卡司」課程,找了生物系的顧爾德(S. J. Gould)、哲學系的諾奇克(R. Nozick)和法律系的德蕭維茲(A.
Derschwiz)三大全國知名的明星教授一起對談上課,然而這門課的註冊人數,竟然還是贏不了「文革」。
一度我以為真正吸引學生的,應該是「文化大革命」這項課程名稱。學生或許是以為課程?的是文化如何發生革命性變化的觀念,以及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文化革命現象,他們並不明白其實課程從頭到尾解釋的是再具體不過的一段中國當代歷史過程?
然而,「文革」年年吸引大批學生,光是課程的筆記影印就在校內滿天飛,加上學長學姊口耳相傳,後來的學生怎麼可能繼續誤會上當呢?
接觸過一些修過「文革」課的學生,慢慢地,我的疑惑有了些比較具體可靠的答案,或至少是接近答案的方向。吸引這些學生的,是「文化大革命」內在不可思議的強烈戲劇性。「文化大革命」要用革命的手段,一時之間打破一切既有的秩序,這樣的想法何其激烈、何其天真!多少兒童、多少少年,在某個天真的時期,面對外在世界加諸在他身上的層層管制,都曾經幻想──如果能夠把這些討人厭的權威通通一掃而空,多好!成長過程中,他最終必須慢慢學會放棄如此的天真幻想,可是他不會真正忘掉那種砸掉整個世界,按照自我意志予以重建的衝動,怎麼也想不到,這樣的衝動,竟然曾經在中國真正被付諸實現過。這裡面就有了讓年輕學生不能不好奇的戲劇性。
這些年輕學生們也都還記得,自己有過的另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望。如果這個社會,甚至這個世界都沒有了大人,多好!真正「小鬼當家」,讓小孩、少年可以不受大人干擾地追求他們要的,包括玩具、冰淇淋、愛情、報復、正義乃至於暴力破壞帶來的快感,他們好奇渴望的,總是被大人阻止,因而也就總是刺激著「沒有大人」想像。他們從「文革」的課程中驚異地學道:在中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共產黨控制最嚴格的國家,竟然曾經以整個國家的規模,試驗讓學生,高中甚至更小的學生,組成「紅衛兵」為所欲為,這是多大的印象落差,又是多讓人難以接受卻又不能不接受的戲劇效果!
「文化大革命」吸引那一代美國學生的一部份理由,也曾經吸引過他們的上一代,那些參加過胡士托音樂狂歡、留長頭髮、吸大麻吃LSD、主張性解放的嬉皮們。嬉皮身體力行的理想生活,核心部分其實也就是一種「反大人」的童真夢幻,反對「大人」的勢利、虛偽、拘謹、管控,相對熱愛自由、真實與脫離現實的境界。透過他們自己的價值信念,他們看到的「紅衛兵」是同樣理想熱情發散的中國同類,更重要的,他們看到了中國領導人毛澤東跟自己國家的「大人」形成在遙遠不過的極端對比,自己家的「大人」想盡辦法打壓年輕嬉皮,毛澤東卻鼓勵、發動「紅衛兵」來鬥爭「大人」。他們怎麼能不崇拜毛澤東?
那個年代,六年代後半延續到七○年代初,西方青年反叛文化發展到最高峰。參與其中的人數最多,卻也因此有了最複雜的路線與派系分分合合。反叛青年中一定有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和比較激進的共產主義者的區別,而共產主義陣營裡,又一定會有比激進更激進的「毛派」。
「毛派」的特色,是本質性地反對一切權威,通常包括自身所屬的黨或組織的權威。除此之外,「毛派」緊抓「造反有理」的口號,表現出一種強烈青少年式的破壞狂熱,他們對於要改革新造一個什麼樣的新世界沒有什麼興趣,將所有精神投注在如何打倒他們討厭的事物上。
那個時代「毛派」是個世界性的重要現象,也是此起彼落恐怖主義組織,背後共同的信仰。從日本到義大利,從歐洲到南美,到處有「毛派」,到處有「毛派」奉毛澤東之名作出的種種破壞行為。
世界性「毛派」尊崇的,不是長征的毛澤東,不是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更準確些說,是他們想像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毛澤東。那個時代,中國仍然對外封閉,沒有人能進到中國看到「文革」真實的面貌,即使這些「毛派」也都不可能理解「文革」給中國帶來的破壞到達什麼程度,不過,他們對於「文革」精神的掌握,尤其是「造反有理」刺激的青少年情緒,其實掌握得還蠻準確的。
「毛派」心目中的「造反」,和實際的「文革」之間最大差距,在於「造反」的限度。「毛派」真心相信「造反有理」,換句話說,任何既成秩序與權威,都在他們「造反」的範圍內;然而在中國,「文革」再怎麼徹底革命,再怎麼徹底造反,再怎麼炮打司令部,毛澤東卻一直是絕對不能被挑戰的最後權威,造反反到最後,還是要「擁謢毛主席」,彼此對立武鬥的團體,都堅持自己是毛主席的子弟。
依照一個不容許挑戰的權威來進行造反革命,也就是「奉命造反」,正是「文革」最核心也最內在的矛盾落差。
矛盾的,不只是為什麼激動造反的青少年始終不敢挑戰毛的權威,也包括了,掌握那麼大權力的人,為什麼還要命令人家去造反呢?造反不是奪權者才運用的手段嗎?已經擁有權力、尤其是最高權力的人,不是應該反過來成為大保守派,嚴守既成秩序,對鞏固、延續自己的權力最有利嗎?
後面這項常識想法,使得許多想要解釋毛發起「文革」動機的人,都特別強調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地位,以及劉少奇對毛澤東構成的威脅,以鬥爭劉少奇作為「文革」的根本原因。
這樣的解釋,順理成章,卻不完全符合史實。面對毛排山倒海而來的行動,劉少奇根本招架無力,也幾乎不曾真正試圖對抗,很快就被壓伏了,顯示即使「文革」之前,劉少奇都沒有足以跟毛相庭抗禮的實力。黨機器始終掌握在毛的手中,國家行政機器,從基層一路上來,都比黨矮一節的,劉少奇哪有多大本錢可以對抗毛澤東?
然而,劉少奇節節敗退,乃至劉少奇徹底倒台,卻都沒有讓毛澤東停止「文革」的瘋狂舉措,而且「文革」造反破壞的主要對象,不是國家行政機器,而是共產黨黨官僚。
鬥爭劉少奇不足以解釋毛澤東的行為,顯而易見。「文革」陸續出土許多文件資料,讓人們逐漸清楚「文革」帶來的狂亂與悲劇,不過若是要思考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理由,那麼最富參考價值的材料,首推毛身邊醫生李志綏的回憶了。
李志綏近身觀察讓我們看到毛權力慾望真正的極端程度。一九五○年代,當毛澤東自己下令要全中國「向蘇聯老大哥一面倒」,中國上上下下都在努力學俄語,大學英美語文教學全面停擺時,毛澤東最熱衷做的事,竟然就是學英文!
沒有任何合理的原因,讓他在那個時間點上學英文,唯一的解釋──連他自己設下的規定,毛澤東都不願、不能遵守,他的權力滿足來自於他的「例外性」,他不必遵守任何規定。
所以有時候就連最重要的「五一」、「十一」大典,毛澤東都會因為起不了床而缺席。坐在火車上,管它是白天黑夜,毛隨時可能想睡覺,專列火車就必須停下來,連帶地周圍幾十列幾百列火車班次同時停擺,沒人知道什麼時候主席會醒來,也就沒人知道多久以後火車才可以復駛。
毛不只不能忍受聽別人的指使,他甚至無法忍受有規定跟制度限制他,即使那些規定、制度是他自己訂的。他這種空前高漲的權力意識,化成打敗日本人、美國人、蔣介石的強悍革命意志,不過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後,就形成了嚴重的問題。
國家不能沒有體制,執政的政黨也不能沒有固定系統。就算毛自己不服從體制,他自己高於系統、超越系統,他的同志們畢竟要慢慢收拾收束在黨政官僚裡,對官僚規則的看重,逐漸超越過去革命中人與人的流動關係。
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儘管歷經各種運動風波,黨官僚畢竟還是一層層地建起來了,過去的革命夥伴各有各在官僚中的位置,按照體系安排彼此對待,也照著體系規則尋求提高地位、增加權力。
他們並沒有挑戰毛澤東的地位與權威,但是他們的政治權力認同,無可避免越來越傾向於抽象的黨,而不是具體且任性的毛。
這正是毛最厭惡、最不能接受的。世界凝固了,一切都有了秩序有了規矩,毛能夠任性活動的空間越來越小。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決定阻止世界在他周遭進一步凝固,直接實際的做法,就是摧毀黨官僚,他要用個人意志個人力量逆轉黨和國家建制化的歷程。
「文化大革命」在毛心中,不是策略,不是手段,是真正徹底的絕對改造,他要從人的內心、從社會文化上,終止追求建制、追求秩序的衝動。「造反有理」因為造反就是打破建制、打破秩序,所有建制、秩序所成就的,通通被視為「舊」,也就通通都可以消滅。
革命經驗與革命口號長期影響下,毛澤東對於「群眾」的基本認知,就是:群眾不滿現狀,熱終於打破現狀,認為打破現狀有助於改善自己的情況。到了六○年代,共產黨建國、執政的結果,其實大幅減少了潛在的「群眾」,畢竟中國連續動亂了半世紀,誰不想藉著新中國的解放,休息休息喘口氣呢?無法發動原本的「群眾」,毛澤東於是轉而發動學生,後來發現連大學生都不具備那麼強烈的造反「群眾性」,索性再將目標放到高中生身上,因而釋放出了那既驚人又恐怖的童稚、野蠻破壞力量。
短短兩年內,「紅衛兵」的力量就摧毀了毛澤東視為眼中釘的黨官僚,然而從開始「軍管」到「文革」落幕,卻還要再等漫長的八年。至於「文革」留下的後遺症,到今天快半個世紀後,還沒有人敢說已經真正清除了。
「文革」完全毀掉了中國共產黨原來的領導階層。造反派打倒當權派,接著就輪到造反派被看作當權派打倒。一波又一波,再厲害再會鬥爭,誰也防止不了「造反」造到自己頭上。唯一的例外,只有毛澤東。幾年下來,中共所有人都失去了權力正當性,毛澤東死後,「四人幫」維持不住局面,華國鋒也保不住權力,鄧小平勉強登基,接下的畢竟是一個人才嚴重不足,而且官僚秩序蕩然無存的國家。
「文革」不只毀掉當時的建制與秩序,連帶毀掉了建制、秩序在中國的基本合法性。一整代人在童稚、野蠻破壞中生存長大,從來沒學會如何打造制度,更從心底瞧不起秩序,這樣的國家,別說如何在國際間競爭,連要在內部跟自己和平相處都極度困難。
一直到今天,中國都還在「後文革」的階段中持續蛻變。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的書,堆積、鋪陳眾多的細節,讓我們具體走過「文革」的歷史巨變,感受「文革」對中國產生的深遠影響。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真正領受到「文革」中彰顯的人類行為荒謬性,切身感知文明的脆弱。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如實地思考集體行為內在高度的可操控性,以及如何防止群眾被煽動、操控,創造出無可挽救的傷害。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找到衡量中國內在精神扭曲的尺度,進而了解現實中國依舊未能徹底拔除的暴力導火線所在。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評價三十年「改革開放」帶來的治療與進步,並依此投射預見中國未來可能的轉化速度與幅度。細密地凝視「文革」,我們才能看出鄧小平的關鍵歷史地位與發揮的關鍵作用,公平地承認他對拉住沉淪中的中國作出了多大的貢獻。細密地凝視「文革」,同時將「文革」複雜因素放進對中國的圖像裡,我們才有機會擺脫許多來自傳統與古遠歷史的刻板印象,在自己的認知架構中,有效地刻寫現實而不虛幻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