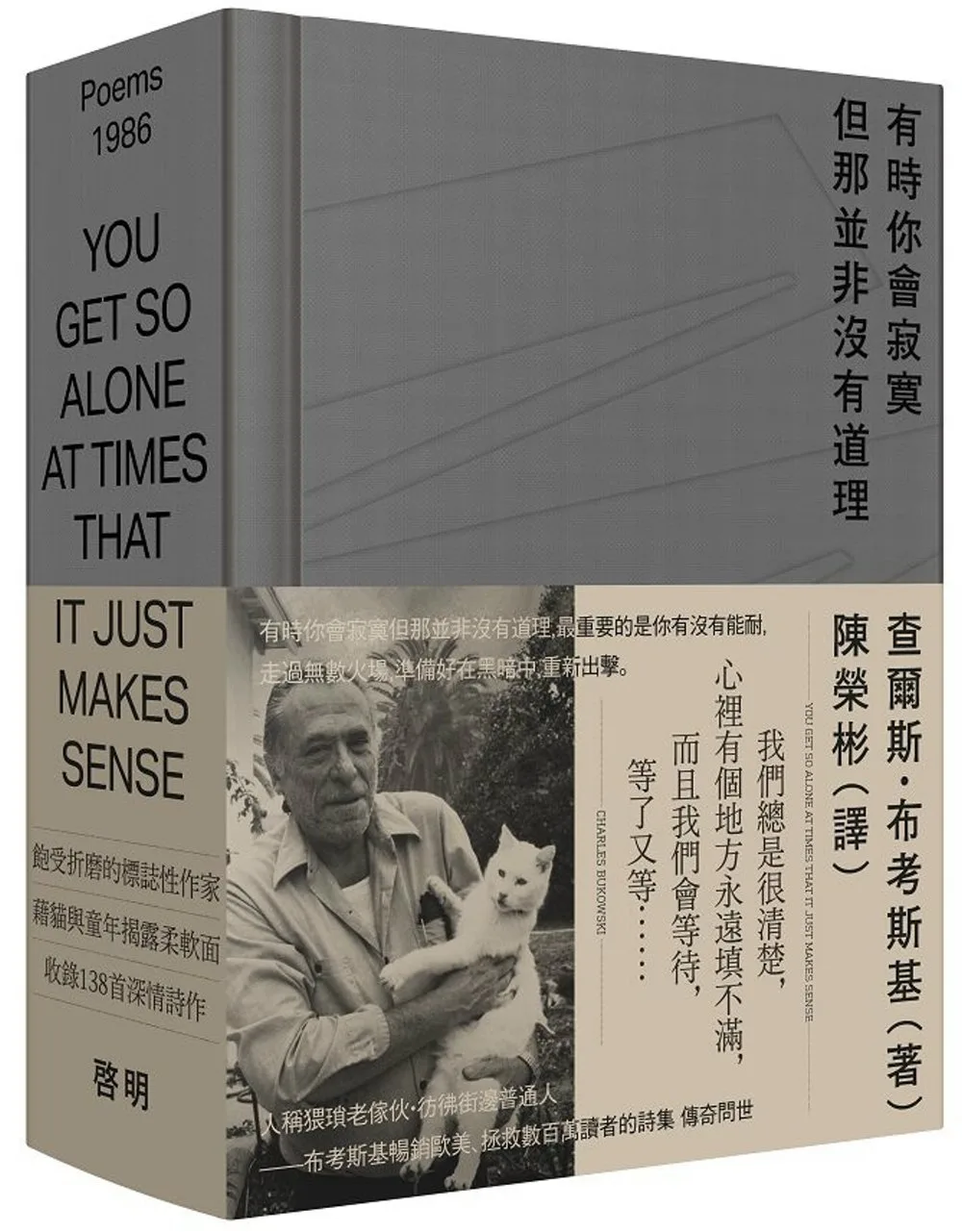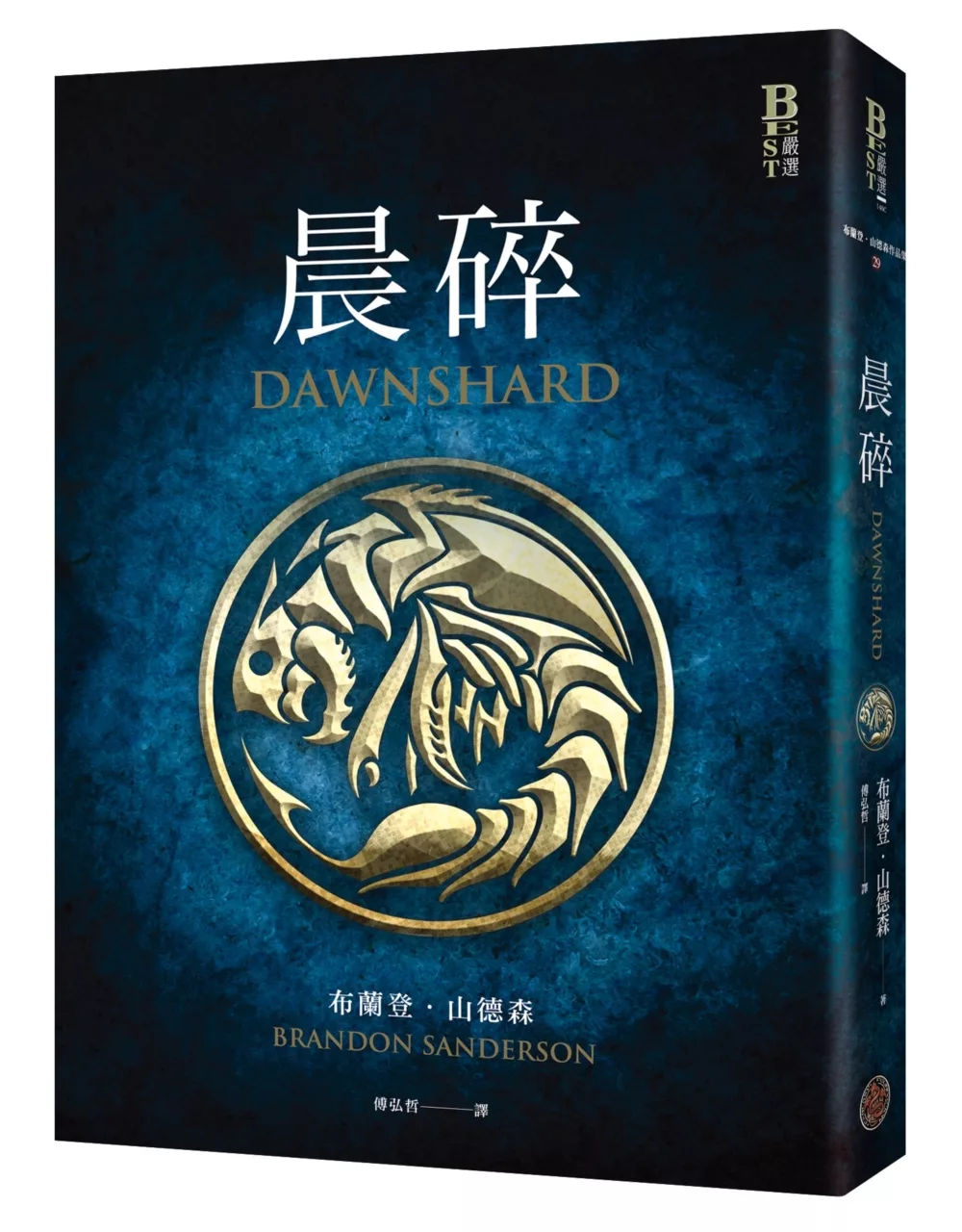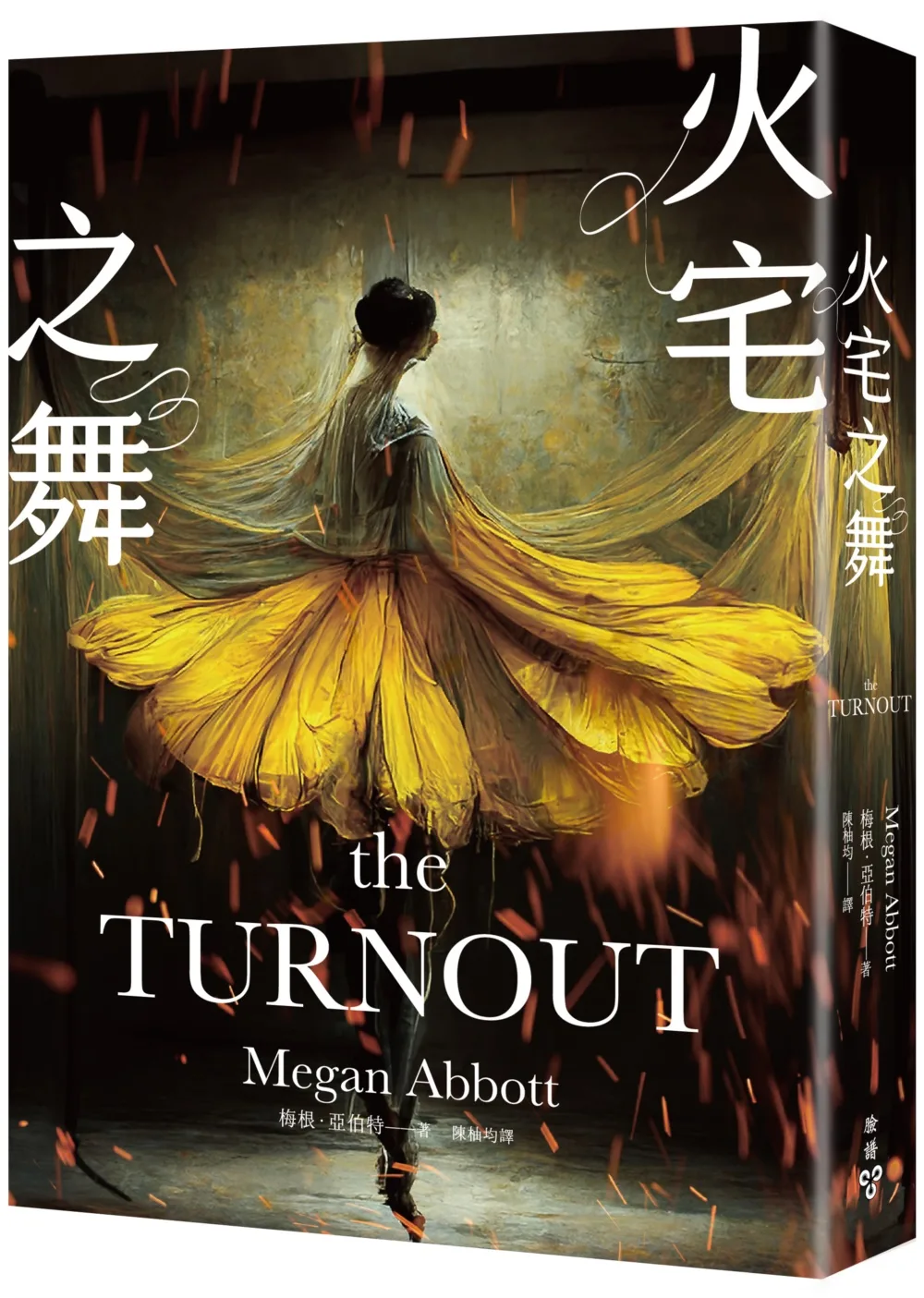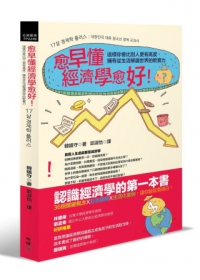推薦序
生命中的小屋
文/彭蕙仙
基督教信仰裡最難過的一關,有人說,就是「苦難神學」。《聖經》裡的每個人物,從〈舊約〉到〈新約〉,大抵都能找到讓人一望可知的意義,唯獨約伯,總是讓人不解,更讓人不忍:《聖經》作者形容約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這樣一個好端媏的人為什麼後來竟碰到家破人亡加上破產的慘事,上帝到到底在幹嘛?
兩千五百年來,已有無數人討論過約伯。不論是否有基督教的信仰,或多或少聽過約伯的故事,即使不從神學的角度,就從人生際遇或者甚至俗話說的「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的觀點,或者也思索過約伯的故事。而他的故事之所以能夠引發人們從未止歇的關切,並且成為基督教信仰裡的一個核心課題,有兩個理由:第一,每一個人的人生總不缺乏受苦/吃苦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或大或小,或漫長或短暫,但不可諱言,「受苦」是許多人生命的共同語言。
曾經看過一個故事,有個婦人因兒子過世悲慟逾恆,向智者求取解痛之道,智者給了他一個小皮袋:「你去收集家裡從來沒有過死人的人的眼淚,裝在皮袋裡,這就是藥方。」婦人走遍千山萬水,卻找不到一個這樣的人,於是領悟到,原來人生裡,「失去」與「死亡」是如此普遍甚至尋常的課題,自己並不是惟一受苦的人;婦人因此走出了悲傷。
約伯的故事之所以充滿張力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們都相信「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至多加上一句安慰,「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這種對善惡與人生境遇之間存在著一種「因果關係」的信仰,是維持人間秩序的重要動力,甚至是維持人對神的信賴的依恃。
也因此,我們相信苦難終有它的意義。美國小說家索頓.懷爾德(ThorntonWilder)在《第八日》(TheEighthDay)描寫了一位好人和他的家庭無端遭害的故事。懷爾德並未對這樣的苦難提供解釋或者解脫之道,但提出了「織錦說」。一幅繡工美麗的藝術品,從正面看來,絲線各安其位、配色鮮豔,但若是翻到了背面,則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番景象,絲線扭曲盤錯,有的長、有的短,顏色錯綜複雜。從背面看,這幅圖像簡直亂的毫無道理;但從正面看,每個打結、剪斷、換色的絲線,原來都有巧妙安排。
受苦使得生命在另外一個層面上,有了更深刻、美麗與動人的可觀之處。這可能是這個故事嘗試要告讀者的事;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本來就如同各條不同的繡線,在我們所不能理解的設計藍圖裡,我們彼此糾結,有時甚至還互相牴觸,但最終是成就了一幅偉大的藝術作品。
然而,大部分的我們畢竟不是那位造物者、設計師,很難從宏觀著想,看的都是小小的局面:碰到這樣的事、吃這種苦頭,對我有什麼意義呢?最普遍的一個觀點就是「受苦使人謙卑,使人心柔軟」。我們不得不承認,一路坐著雲霄飛車往上騰升的人生確實容易使人傲慢並且心思粗糙,但吃過苦的人卻更容易放低姿態,對人生種種也更能包容寬厚。悲劇甚至讓我們體會到生命是多麼地脆弱,由此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有這種認知的人相信,受苦是一種修復,既修復人性中的錯誤,也修復人際關係中的錯誤。
各式各樣不同的解釋,目的都在於幫助人從人生種種苦難中走出一條路來。但是關於苦難,這些解釋還有一個不能處理的部分,就是「受害人」要拿「加害人」怎麼辦呢。即使我們能夠相信上帝充滿了慈愛與憐憫,相信苦難是化了妝的祝福,但是如果苦難有個直接的源頭,也就是造成苦難不幸的那個人,例如《小屋》這本小說中的那個連續殺人「魔」,難道這個人做這些可恨可惡的事也有什麼偉大的動機嗎?
受苦的人或許可以咬切齒地「勉強相信」上帝並未「促成」不幸,祂只是「任憑」人類依自由自意志去做他想做的事,就好像儘管上帝告誡了亞當不可吃分別善惡的果子,但人類選擇要吃,上帝也由著去。這樣看,似乎上帝也沒有那麼可惡,但那個壞蛋傢伙就不同了,他做出這麼傷天害理的事,死有餘辜;他於受害者的受苦受難又有什麼啟發性的意義呢、憑什麼要受害者饒恕他?
饒恕不是把可恨的人與可恨的事藏在閣樓裡,想辦法一輩子不要去碰;饒恕不是讓的確做過錯事的人得以脫罪;饒恕甚至也不是讓加害人與被害人從此可以手拉手、建立信任的關係。饒恕是讓對方可以和你一同站在上帝的面前;其他的,就交在上帝的手裡吧。
當然,這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除非上帝的愛介入再加上聖靈的動工,這樣的事幾乎不能成就,也因此,悲劇並不能提煉救贖,苦難,也往往成為隔離人更隔離神的、厚厚的牆;這牆硬厚堅實到甚至於可能永遠無法超越;牆的這一邊和牆的那一邊,俱是苦情。《小屋》想做的,是化解這堵牆。小說藉著一件凡人難以承受的慘案,和一樁常人難以相信的奇遇,循序漸進地從主角在原生家庭受到的傷害一路舖陳到他後來的悲慘苦難,重點是引導他認識上帝的愛,以及上帝與他親密而獨特的關係。當故事來到了他如何面對兇手的部分,雖僅寥寥數語卻為整部小說帶出了不可思議的高潮,衝擊之大,讓人低迴再三。
儘管這部小說裡的基督教信仰信息很明顯,但是其中對生命種種關係和際遇的深刻省思,卻是跨宗教的,毋寧說,這部小說為人類在苦難中的孤獨、困惑、憤怒與呼求,提供了一個清晰可信、誠懇欣慰的回應。或許每個人的生命裡都有這樣的一個小屋吧。在那裡,曾有無法言說的至大苦楚向我們襲來,然而,就在那裡,我們也將會遇見言語不能形容的至深之愛,上帝的愛。
像神明一樣快樂
——關係與療癒的小屋之旅
文/呂政達
麥肯錫:
好一陣子沒聯絡了,很想念你。
如果你想聚聚,下週末我會去小屋。
老爹
等等,先別管老爹的身分,或者下個週末將要展開的神幻經歷,讀到這個邀請,請你設想成體貼的精神醫師或心靈療癒師,寄邀請給一位當事人或案主:「你最近心情不好喔,來吧,來談談吧。」就這個週末,暫別人間眾事紛擾,來談談困擾糾纏生命甚深的疑義。
《小屋》除了浸潤在《與神對話》、《告別娑婆》的基督教義大眾敘說脈絡外,其實,整個幻現的歷程,就是一場典型的心理治療。許多心療案例裡,案主同樣也因親人遇害的悲傷際遇,開始懷疑自己的信仰,從此不再相信神的存在,從精神分析的鼻祖佛洛伊德以降,對這個議題從不陌生。佛洛伊德終身秉持無神信仰,但他在世最後一本著作《摩西與一神教》,雖仍維持神是神化後的人,卻多少可以讀出猶太教的出身背景對他的影響,佛洛伊德自己就引用了宗教對人的詮釋體系。
去世於一九三九年的佛洛伊德,如果有機會閱讀《小屋》這部小說,肯定會拿著向讀者宣示:「我說的一點也沒錯,神只是神化的人。」在後實證主義氛圍裡,究竟是神照自己的樣子造了人,還是人照完美典範打造出神的樣本,始終是心靈科學與基本宗教教義的根本衝突。
關於這個爭議,這部小說採取了現象學家胡塞爾所說的「擱置」立場,它讓神做人做的事:烘焙、烤餅乾、墾植花園、洗碗盤;同時也展現走在湖面、召喚死者和生者的夢境等神蹟。然而,各有宗教立場的讀者或許也可暫時「擱置」爭議,「還原」到作者要我們真正讀到的:對一位喪失女兒的父親,自我療癒如何成為可能?小說裡,神並沒有採用心智侵入、矯正或用藥,來改變麥肯的痛苦,採取的是傾聽、了解、相信、分享、幫助他辨清問題和建立關係,這都是現代精神醫師經常會使用的進路。讀者一定會感受到,其中,「關係」才是整部小說的精髓核心。正如聖靈沙瑞玉對麥肯所說:「你要尋找關係─—這是與我們同在的方法。」回答麥肯「你們是三個,還是同一個神?」,他們也說,這樣的位格,才能讓神擁有愛與關係。
麥肯當然符合一個精神醫學案主、當事人或直接就稱為病人的標準,然而,我們何能讓全能的神走出天國,充當我們的精神醫師呢?找個線索,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寫道:「神能夠觀得存有全體,能夠包容存有全體,故而也能夠理解存有全體,因此,祂所看到的存有全體必然皆是美善的,是恰當的,是理所當然的:而且祂必定視『惡』為有限的產物,是在自私的觀點、自私的理解下所產生的後果。如果我們能在此意義下肖似於神,我們便也能夠走出一般普遍的理解,而會永遠不再責備、不再詛咒、不再失望、不再震驚。……這也正是所有的心理治療醫師們嘗試對待病人的方式。」人本心理學早就有將神喻比喻成心理治療的傳統,關鍵就在於,我們能不能在此理解下「肖似於神」?這部《小屋》,當然也是這層理解下的註腳。
千萬不要浸潤在基本宗教的描寫裡,將「肖似於神」,當做多麼艱難的修行。馬斯洛用過「像神一樣快樂」的字眼,比如幽默、有趣、大智若愚、傻氣、遊戲、歡笑,皆是凡人所能達到,接近神性的存有價值。我邀請讀者在等一下將閱讀的章節裡,體會出作者在這方面的著墨,在老爹、耶穌、沙瑞玉的對待中察覺「像神一樣快樂」的特質。我們所得到的感想,將不僅是「神原來都在做這些事啊,一點也不稀奇」,而是較接近「神的快樂就藏在凡人的日常瑣事間,我們只從不這樣認為」。
如果你還是以為,凡人的皮囊,皮囊附帶的七情六慾功能,是你最重要也唯一僅有的,請回到黑格爾的話語中歇息:「從永恆的眼光看來,每一件發生在天上和塵世的事,發生在神的生命和時間中所有事蹟,都是靈性認識自己、發現自己、成為自己的奮鬥,最後他要讓自己和自己真正合而為一。」
在自己心靈角落的「小屋」內,請善自歇息。
晚安,祝你好運。
(本文作者為《張老師月刊》編輯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