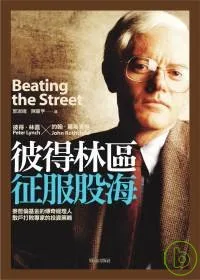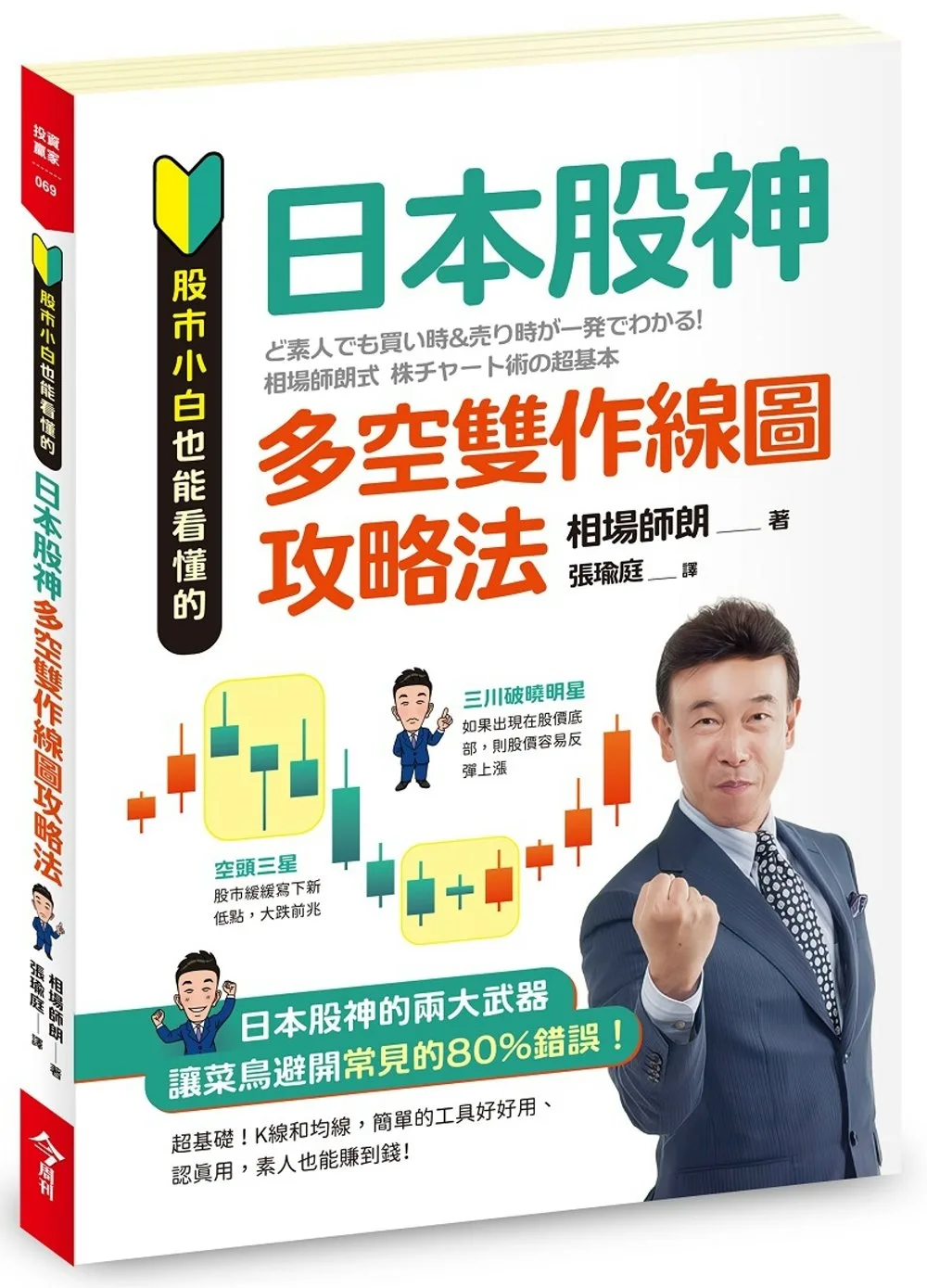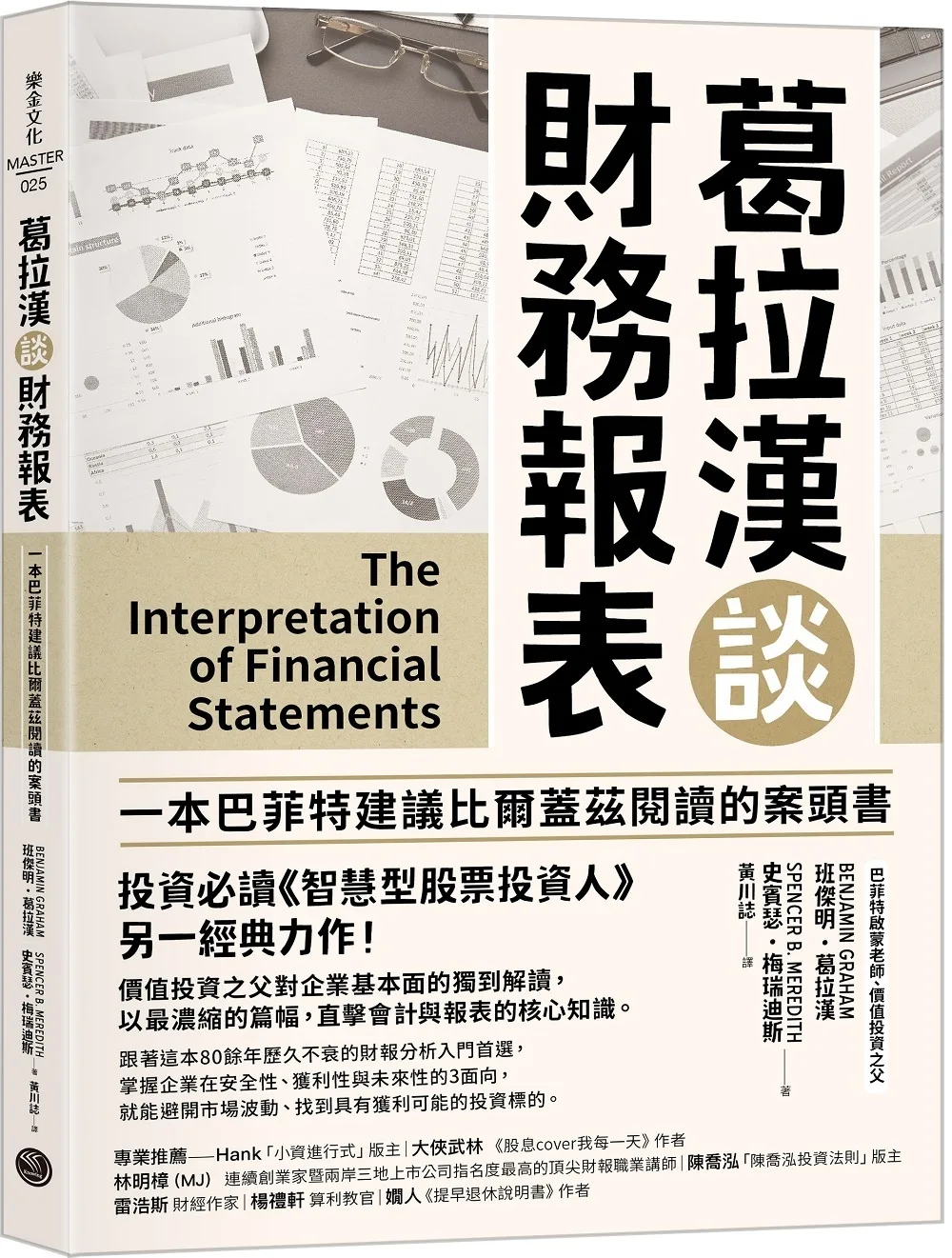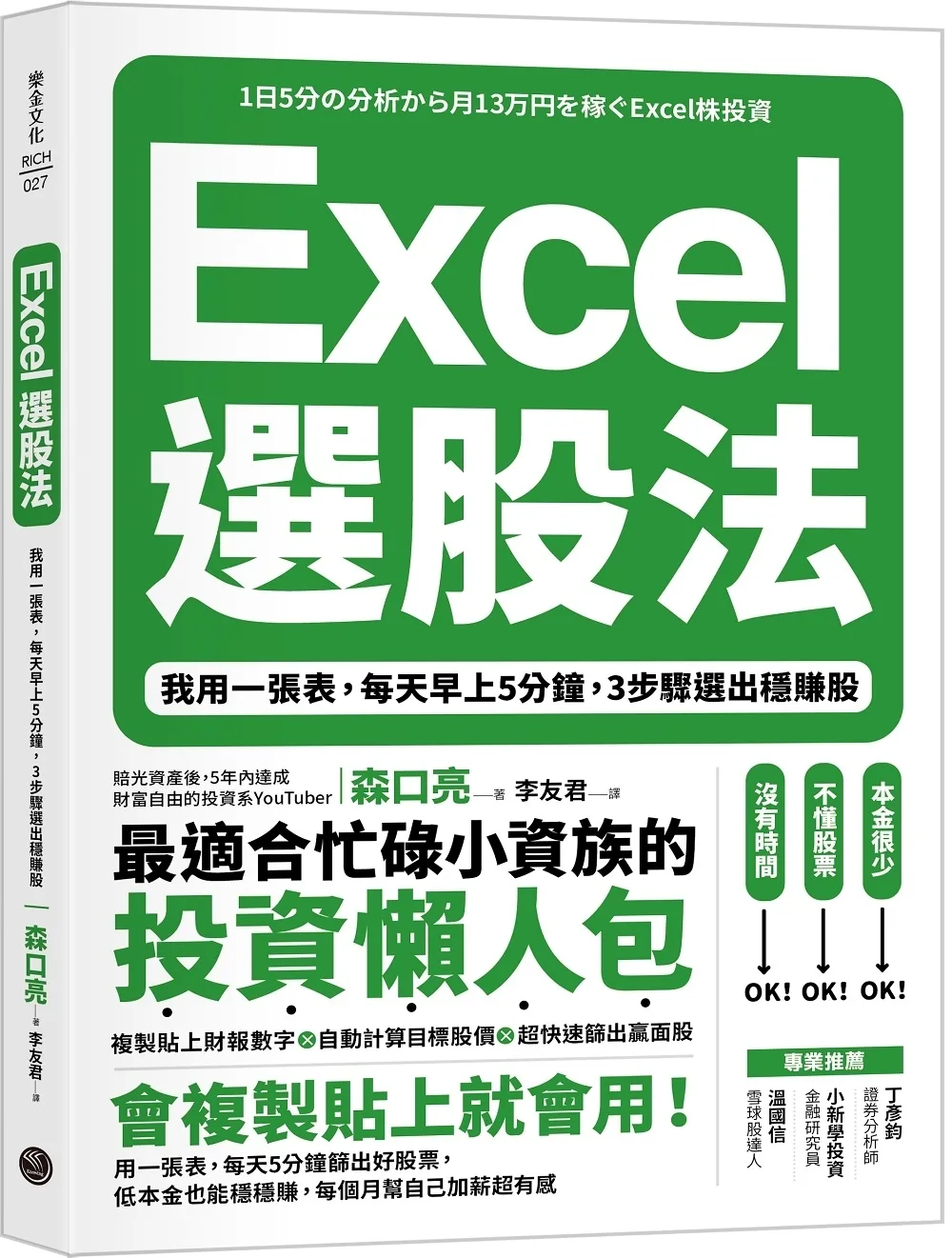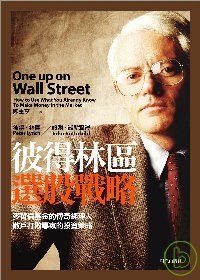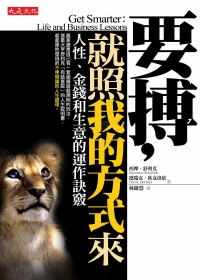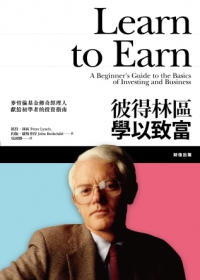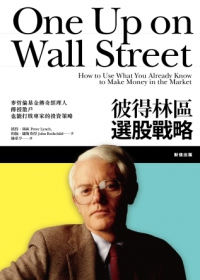自序
1990年5月31日,我正式離開富達麥哲倫基金。到那一天,我接掌麥哲倫剛好13年。當時美國總統是吉米.卡特,他曾對《花花公子》雜誌自承,心裡對女人還是充滿了情欲。我也一樣是春潮欲滿,不過是對股票情有獨鍾。在麥哲倫的13年中,我替客戶操作過的股票超過15,000支,很多股票甚至不止買過一次。難怪人家以為,沒哪支股票是我討厭的。
離開麥哲倫是很突然,但也非一夕之間突發奇想。八○年代中期,道瓊指數衝破2,000大關,我也突破43歲關卡,這時還要緊盯千百支股票,真的是代價不菲。雖然我很喜歡管理一個和厄瓜多爾國民生產毛額一樣大的基金,但是我也錯過陪伴孩子的樂趣。小孩子長得可真快,幾乎每週都要讓他們自我介紹才認得。我實在花太多時間在工作上,比和她們相處的還多。當你開始把家人名字與上市公司名字搞混;記得2,000支股票的簡碼代號,卻記不住孩子生日時,對工作未免陷得太深啦!
1989年股票行情挺順的,1987年股災已成過去,我老婆卡洛珠和瑪麗、安妮、貝絲三個女兒為我慶祝46歲生日。慶生會上我忽然想到:先父就是享壽四十六。當你年紀超過父母壽命時,就開始感受到死亡陰影。不管往後還能活多久,都有餘日無多的感覺。這時只望能看更多戲、滑更多雪、踢更多足球。誰會在臨死前感慨說:「但願能多花點時間在工件上。」
我試著說服自己,孩子大了就不用太費心。但事實正好相反。小孩兩歲剛會走路時,成日橫衝亂撞,父母當然得隨侍在後收捨殘局。但是應付小鬼還好,真正耗時費神的是青少年的孩子,陪他們做西班牙文功課,和那些早就忘光的數學習題,去網球場、購物中心要接要送,有煩惱還得咱們加油打氣,這些可都不輕鬆。
每到週末,為了拉攏小孩,瞭解青少年想些什麼,只好跟著他們聽音樂,生吞硬背搖滾樂團名字,陪他們去看根本沒興趣的電影。這些事我都做過,只是不常。我週六幾乎都在加班,工作多得跟喜馬拉雅山一樣高。偶爾帶孩子看電影、吃披薩,還是滿腦子股票。正是因為帶他們去玩,我才知道披薩時光戲院──真希望從沒有買過這支爛股;還有奇奇餐廳──沒買真讓人扼腕。
到了1990年,瑪麗、安妮、貝絲分別是15歲、11歲和7歲。瑪麗就讀寄宿學校,兩週回家一趟。那年秋天,她參加七場足球賽,我只看到一場;同年,我們家的聖誕卡晚了三個月才寄出去;而我們為孩子作的剪貼簿,集了一堆卻沒空貼!
我當時自願參加一些慈善機構和民間團體,所以平常晚上若不加班,可能就去參加這些機構團體的會議。通常我負責投資事務,為慈善、公益目的選股票,是再好不過的事,但是公益活動需要更多投入,麥哲倫基金讓我愈來愈忙,女兒功課更艱深,需要的接送也愈頻繁。
那段期間忙得晚上睡覺都夢到客戶,可是和老婆的浪漫時刻,竟只剩在自家車道巧遇;每年一次健康檢查時向醫生自首,唯一運動是用牙線剔牙;18個月來沒讀過一本書,兩年來只看了三齣戲:《漂泊荷蘭人》、《波希米亞人》和《浮士德》,足球賽一場也沒看。所以我歸納出彼得定理第1條:
當你看歌劇的場數以三比零領先足球賽時,生活大概哪兒不對勁啦!
1990年年中,我終於明白該離職了。我記得麥哲倫本人也是早早就退休,搬到太平洋偏遠小島。雖然他的悲慘遭遇讓我稍有猶豫(他被當地士人撕成碎片)。為了避免被生氣的股東大卸八塊,我和富達的老板強森以及交易部主管柏克黑,一起討論如何順利卸任。
我們坦誠而友善地溝通。強森要我繼續待在富達,統管所有富達證券基金,自己只操作一個小型基金,例如只有1億美元,這和我正在管理的120億美元相比,是輕鬆很多了。但是對我而言,儘管基金規模少掉幾位數,新基金所需耗費的心力,和經營麥哲倫基金沒兩樣──到時週六又得加班。因此我婉拒強森的好意。
大多數人都不知道,我當時還替柯達、福特和伊頓等大企業管理10億美元的員工退休基金;其中柯達比重最大。操作退休基金比麥哲倫更順手,因為投資限制較少,例如退休基金在個股投資比重上可以超過5%,但是共同基金就不行。
柯達、福特和伊頓公司也希望我繼續操作,不管我是否會離開麥哲倫,但我也沒接受其好意。另外有人慫恿我自立門戶,搞個封閉型基金,就在紐約證交所掛牌交易。那些人告訴我,隨便幾個地方宣揚一下,就能募到幾十億美元。
從基金經理人觀點來看,封閉型基金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不管玩得多爛,都不怕贖回賣壓。因為封閉型基金是在證交所買賣,就像莫克、拍立得,或任何一種股票一樣;想賣掉封閉型基金,市場上就得找到相對買家才行,所以流通憑證數額永遠不會縮水。
但麥哲倫這種開放型基金可不同了。基金持有人要求贖回,基金公司必須依憑證淨值等額付現,而基金規模則相對減少。如果開放型基金操作不佳,投資人紛紛棄船,把錢轉到別的基金或貨幣市場時,基金縮水得很快。這就是為什麼開放型基金的經理人晚上睡覺,通常不像封閉型那麼安穩。
一個20億美元,在紐約證交所掛牌的林區基金,就像一家20億股本的公司(除非我犯了一連串重大錯誤,賠光所有的錢),每年穩拿0.75的管理費(1500萬美元)。
就金錢上而言,這個提議相當吸引人。雇些助理來選股,上班時間可以減到最低,平時打打高爾夫,多陪陪老婆孩子,還可以去看球賽和歌劇。不管操作績效比大盤好或壞,豐厚酬勞照拿。
但還是有兩個問題。第一,我想超越大盤的企圖心,遠遠超過落後大盤的忍受力;第二,我認為基金經理人應該自己選股票。於是又回到原點,週六待在林區基金辦公室,在成堆年報中上窮碧落下黃泉,儘管賺進大把鈔票,卻和過去一樣無福消受。
有錢人會慶幸自己放棄賺更多錢的機會嗎?對此我深感懷疑。能對大筆財富說不,確是凡人難以想像的奢侈。可是你若有幸像我一般身纏萬貫,就得決定是要做個金錢奴隸,一輩子只知聚歛搜括直到老死,還是懂得運用支配辛勤累積的財富。
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寫過一則貪心農夫的故事。有個妖怪對農夫說,一天內只要用腳踏過繞一圈,那些土地都是他的。貪心農夫拼命跑了幾小時,得到幾平方英哩土地,一輩子都種不完,傳子傳孫也夠吃好幾代。這個可憐蟲汗流浹背,氣喘噓噓。他想停下來──地夠大了,幹嘛再跑?但就是停不下來,只想抓緊機會多要點,最後筋疲力竭而死。
這就是我不想要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