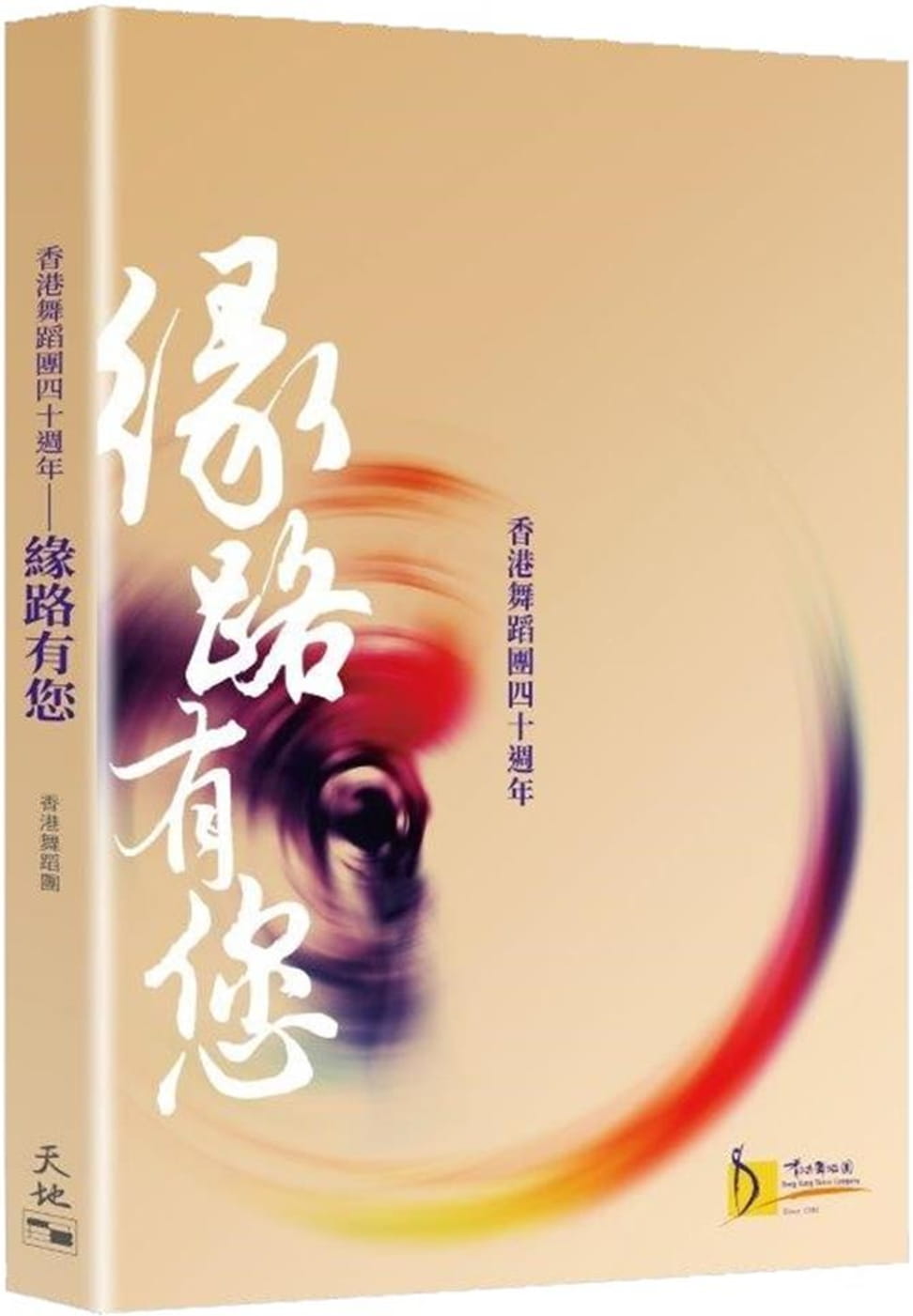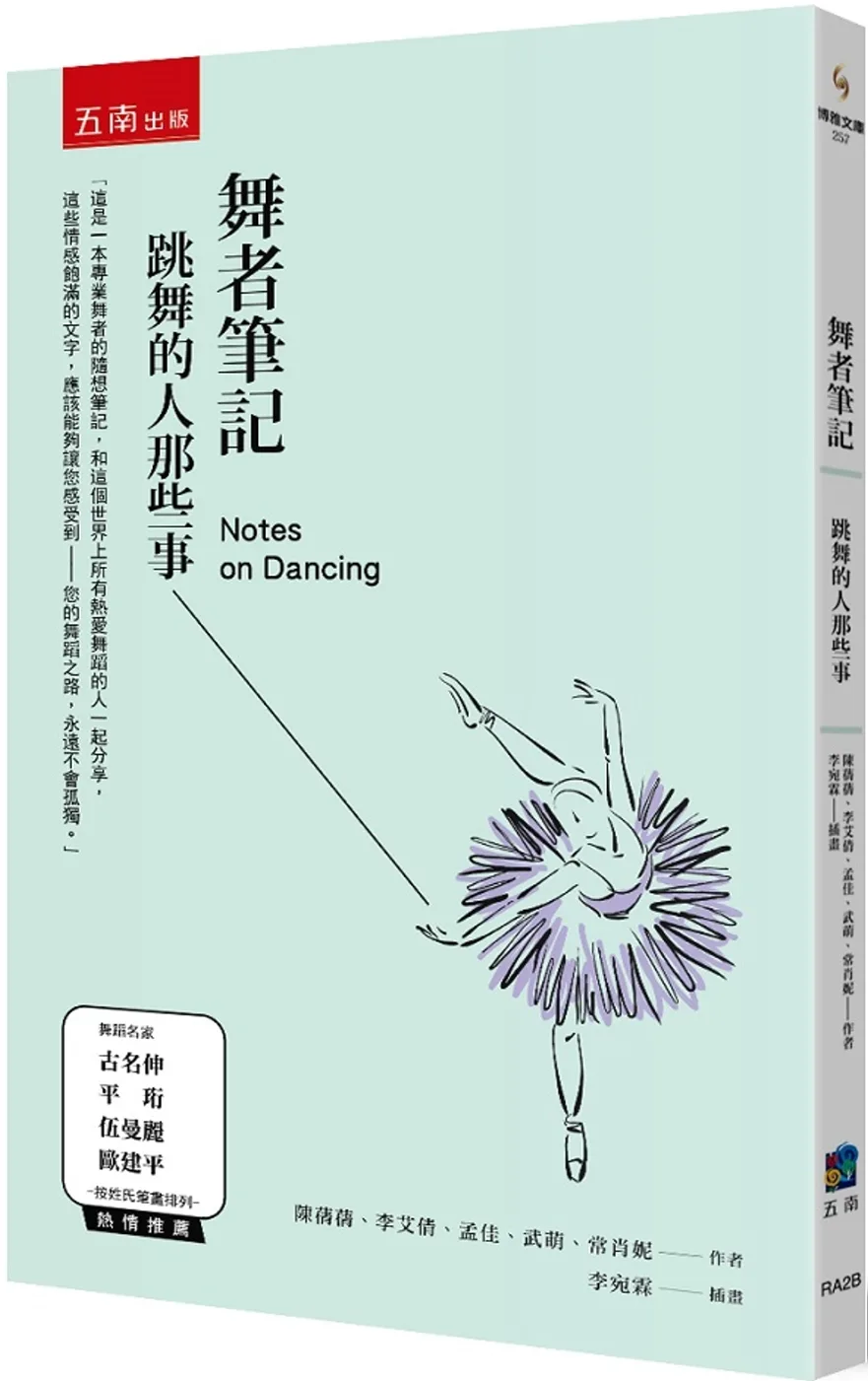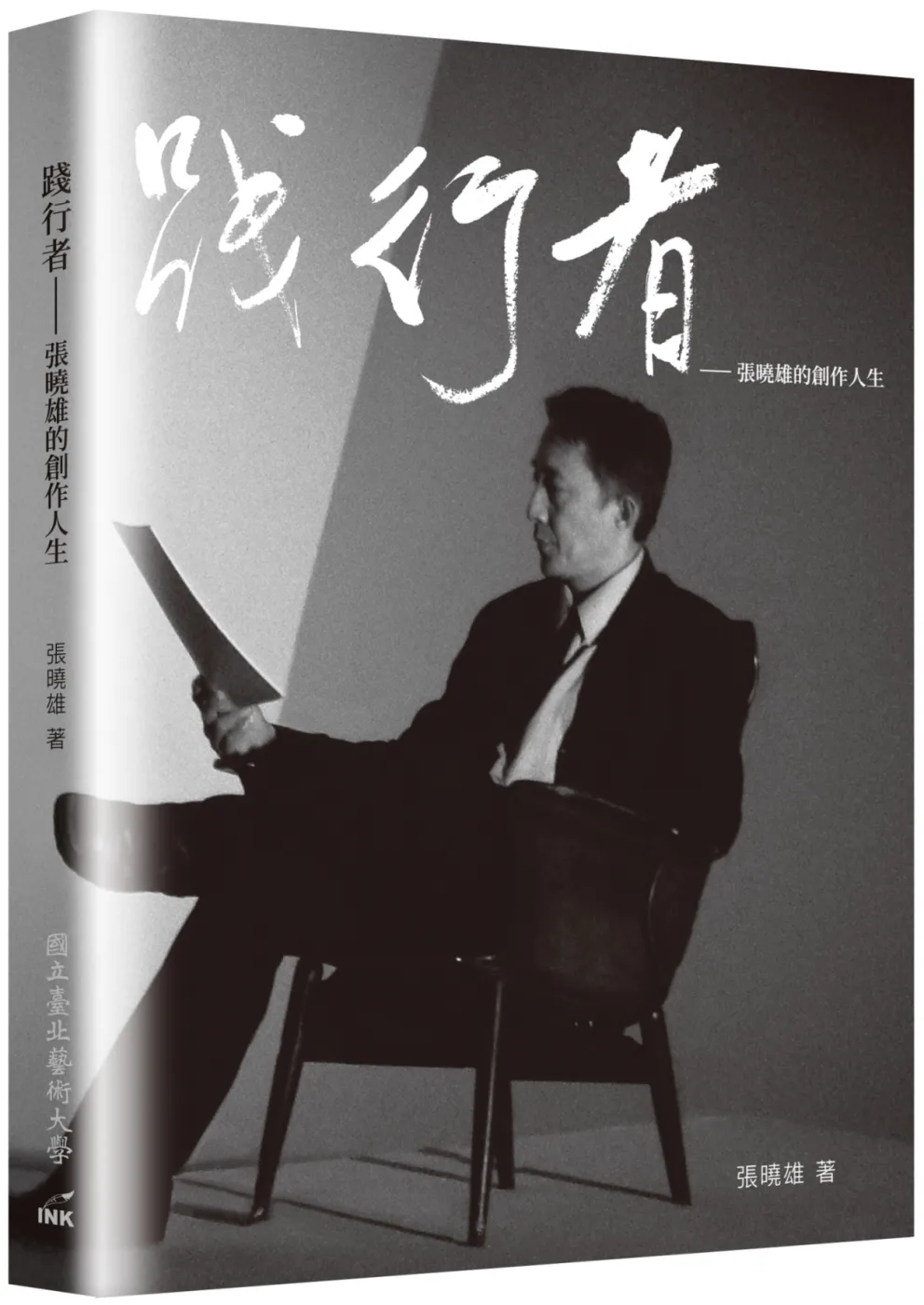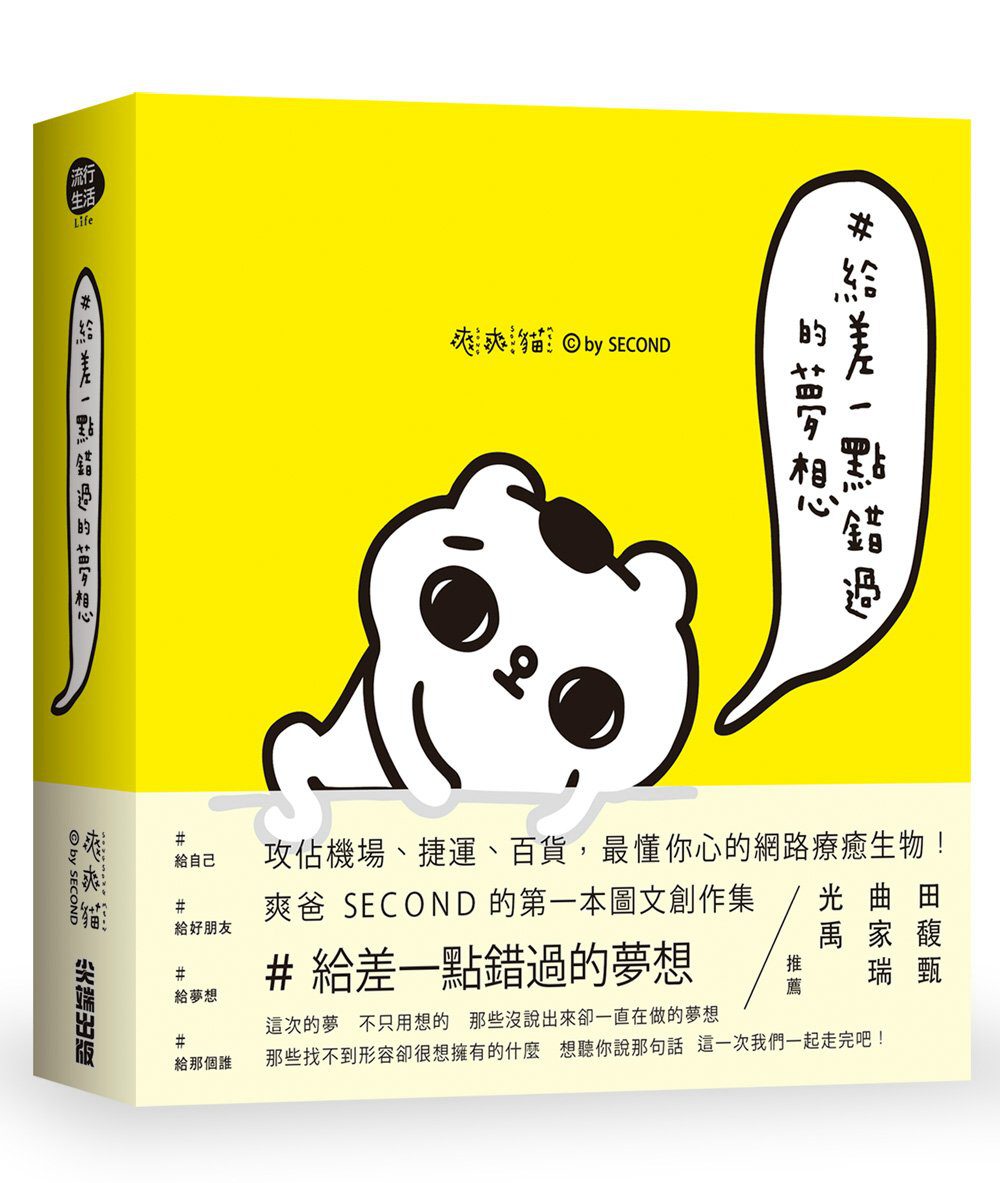誠實面對自己的人生 「金星,你愛舞蹈嗎?」
偶而有人會這麼問我,而我,總是堅決地回答:「不!」
以一個稱為「你」的對象以及稱為「我」的主體間的距離為前提,所產生的即是愛的感覺,然而,我從未想過自己與「舞蹈」之間有那樣的距離及感覺;因為我是舞,舞即是我,我從未想過我的人生中沒有舞蹈,所以不說我愛舞蹈。舞蹈本身就是我的人生,更是我在找尋真實「自我」的漫長旅程中唯一的夥伴。
上帝雖然將我關在男人的身軀中,卻幫我打開了「舞蹈」這個出口。「舞蹈」是讓禁錮在男人體內的我可以表達女性一面的唯一語言,更勝過連筆墨都無法表達的、被壓抑的渴望;雖然我平常生活在禁閉的混亂之中,站在舞台上舞動的瞬間,我就是完整、自由自在的「我」。長久以來,我面對過無數次抉擇,但即使在那些需要下決定的時刻,我也不曾想過要放棄舞蹈;對我而言,我的母語不是中文、不是韓文,而是舞蹈。
我一生的抉擇通常將我引導至人跡杳然的路途,選擇跳舞之初也是如此;在中國,舞蹈家如今依然不是受歡迎的職業之一。九歲那年,我誓言用一輩子的時間來跳舞而決定入伍時,最堅決反對的是母親;她認為男生要讀大學、有高學歷才會有一番成就,因而一直極力阻止我走上這條路。
母親深怕自己唯一的兒子會讓人看不起,更擔心被人嘲笑是少數民族,但我還是說服了母親,接受了舞蹈與我無法須臾分離的命運。
遠走異鄉只為追尋「半個夢」
記憶中,我成長的過程只有充滿痛苦的軍營生活,雖然比大部分小孩早熟,在軍中,我永遠都是那個個頭最小、頭最大的老么,在比我年長的大哥、大姊中,連站上舞台的機會都很渺茫。正因為無法免於長期坐冷板凳的命運,十七歲及十八歲連奪兩屆全國性舞蹈大賽冠軍時,可說完全是由汗與血所匯聚的小小成就。
得獎後,雖然在不知不覺中被認定為中國最優秀的男舞者,我所擁有的那「半個夢想」卻一點兒也沒有實現,甚至可以感覺到,只要留在中國一天,我的夢想將永遠無法落實。
當時也是「現代舞蹈」這個世界深深誘惑著我的時候,然而我一直無法下決定:「究竟要留在中國滿足於目前這小小成就的現況呢?還是應邀前往那人生地不熟但很有魅力的地方呢?」最後,我還是選擇了美國行。我知道我要填滿的夢想實在太多了,希望在「美國」那自由的國度,能實際試探一下自己的可塑性,更重要的是,我想確認我的「性」以及我真正的「性向」。
到美國留學期間,我經常流連同性戀酒吧,與那些同性戀者混在一起,但是,在那個世界中我依然是個異類,他們要的是「男人」的我,而我渴望他們愛的是「女人」的我,因此我可以和他們作朋友,卻無法和他們談戀愛。即使我依然是一個被囚禁在男人身軀中的女人,對他們而言,我仍只是一個漂亮、美麗的男人;對我這種身體與靈魂性向迥異的人來說,愛情不過是存在於小說中的幻想情節罷了。
然而,身處如此徬徨、無助的環境中,我都未曾拋棄過舞蹈,直到二十一歲那年──那是我習舞後第一次離開了舞蹈,因為我認識了一個如同愛女人般愛我的男人。為了跟他在一起,我毫無依戀地放棄了舞蹈,在短暫的過程中,我變成一個只為他而活、只為他呼吸的真女人。但是,一年以後他送走了我,他不希望我只是一隻籠中鳥,他希望我飛向更廣闊的世界,擁有更大、更自由的空間。
失去愛情後的兩年內,我一直在義大利及比利時流浪,在無法靠語言溝通的國度,舞蹈成為我唯一的救星──讓我找到了工作,還認識了許多人;停留在義大利和比利時期間,我愛上了兩個男人,他們也都希望跟我一起生活。
只是,我無法接受他們的求婚,雖然我也愛他們,並給了他們全部的心,但,猶如仲夏夜從夢中驚醒般,深思後,我真誠地問了他們:
「你是如同愛女人般愛著我嗎?」
我比任何人都渴望自己所愛的人是如愛女人般地愛我,可是他們愛的卻是有著男人身體的我。靈魂與肉體的不一致,使我對任何愛情都缺乏信心;我知道,自出生那一刻起,我就是一個女人,因而總是以一個女人的立場去愛著一個男人,不幸的是,我卻借用了一副男人的身軀。
變性是身心靈合一的渴望
我無法再自我欺騙下去了,由於內心的煎熬與忍耐皆已達到極限,二十六歲時我又回到中國,並於第二年決定動手術──變性。
為了尋找身體與靈魂合一的那個完整的我,接受將上帝賜予的肉體性別轉換的手術,對我而言是必要的過程。
嚴格來說,從中國到美國、義大利、比利時,再回到中國,這一段長遠的旅程,只不過是為了找尋「真正的我」的真誠之旅。心中的渴望已無法遏抑,我已無法再以男人的身分繼續活下去。自二十歲起,我就不斷問自己: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嗎?」
我嘲笑自己的心,也聆聽內在誠實的聲音;倘若自己都無法自我理解,更不可能說服任何人。更改自己原有的性別也許是背叛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必須更慎重其事,為了得到上帝的寬恕,心中更應該確認自己所要的是什麼。終於,二十八歲時,我聽到了來自內心深處、充滿信心的回應:
「是的,金星,我準備好了!」
沒有任何猶豫的理由,變性手術只是為了可以誠實面對自己。自初戀起,雖然認識了許多人,也曾相愛又分離,我卻從未想過要為其中任何一個人變成女人。
二十八年來,我以男人的身體活在世上,但靈魂始終是女人。我總希望自己不是家中的獨子而是可愛的次女,並且在我所愛的男人面前,是一個被疼愛的女人。
聽到我要動手術的消息後,不!應該說是我單方面的通知後,家人的確感受到很大的震撼。母親一直感歎,為什麼芸芸眾生中,偏偏是我家的孩子?懷孕七個月的姊姊則因過於震驚導致流產,但兩人最後也只能同意我的選擇;而我以為會堅決反對的父親,反而還幫我去更改戶籍,將男人身分改為女人身分。
我想在中國動手術是因為那裡有父母親,是我出生的地方。就醫術而言,在美國或歐洲等先進國家作手術當然比較妥當,但我仍希望在自己出生、成長的地方,變成一個真正的女人。
手術歷經三次才完成,首先是胸部整形,接著是去除毛囊及磨除喉結,最後則是性器官改造。最重要的性器官改造手術耗時十六個小時,期間還有三個小時發生不明原因的大量出血;通過重重危險與難關,終於成功地完成變性手術。
當時,腦中浮現的是,每逢下雨天總會期盼著「就算被閃電擊中而變成女人也願意」的兒時記憶。
還有那段情願拋棄舞蹈也不後悔的初戀。在他面前,內心總有著「希望自己是一個平凡女人」的傷痛。
拋開所有混亂與絕望,我終於如願地變成了女人,但是,奇怪的事發生了──我的腿無法動彈!原因是手術時應該頂住膝蓋的鐵板搖擺不定且漸漸下滑,結果碰到了左小腿;這搖擺不定的鐵板在我麻痺、僵硬的身體上不停地又刮又碰又磨,折騰了數小時,導致腿部肌肉與神經無法忍受折磨而完全麻痺。這都是護士小姐因為不明原因的大量出血與性器官手術分心,未能察覺鐵板移動所產生的後遺症。
醫師宣布了再也不能跳舞的殘酷事實。我實在無法相信!任誰都不能模仿如此卓越的我,取代站在舞台上躍舞如飛的我,然而,這樣的我再也不能跳舞了。母親及家人因悲傷過度而不能自己,朋友也因過於震驚而啞口無言,而我一心只想跳樓尋短;假若當時我能自由行動,造成自我了斷的事實,今天就無法站在這裡了。
這無異是最糟的情況、最絕望的時刻,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性別,卻成了殘廢,「跳舞」已變成不可想像的奢望;但是,隨著時間不停地流逝,「我不能被擊敗、不可以就這樣放棄」等想法,不斷敲打我的腦海。就在無可奈何且不知所措地躺在病床上的某一天,僵硬的左腳趾竟然稍微移動了。從那一天起,我關在醫院整整三個月,接受重生治療後,麻痺的神經才逐漸恢復正常;不同於心急如焚的我,左腿恢復的速度可說是既遲鈍又緩慢。
我一邊告訴自己不要急躁,一邊想著:違背上帝的旨意而付出這種代價也是應該的;因為背叛了上帝賜予的命運,上帝才會暫時收回舞者所看重的腿。只是,無論出現任何變數,我都無法拋棄跳舞;沒有舞蹈我無法生存,沒有舞蹈的人生對將沒有任何意義。於是我下定決心,哪怕是跛著腳,也要重新站上舞台。
到死都要跳舞的命運
重生治療過程極為痛苦,左腿的腳趾頭、小腿肚、膝蓋無一處倖免,我咬緊牙關忍受著苦楚,不知不覺中便從坐輪椅恢復到可以拄著枴杖慢慢走路;出院後我獨自到西藏旅遊,拖著尚未康復的身軀在西藏巡視了一間又一間寺廟,心中深思了許多事。
眾多的佛像中,唯有觀音像最吸引我心、最引我注目。觀世音菩薩本為男人身軀,其慈悲與優雅的氣質卻非常女性化;望著以長袍遮蔽下半身、以慈母般的眼神看著我的觀音像,腦海中竟浮現同時存在「男」與「女」的我。在西藏度過的一個多月旅程中,我再次思慮了我的人生。
回想過去,總覺得上帝其實已賜予我許多機會,相較於周遭的人,我更是得到比付出多的那一個,那麼,我到底能給別人什麼?我發現,我最擅長的只有舞蹈──那種可撫摸又可安慰他人傷痛的舞,可以洗滌心靈的舞。
上帝並未收回我的舞蹈。自西藏歸來後,我抱著尚未痊癒的腿傷重新站在舞台上,此後長達六年的時間,發生了許多事,也見過許多人。雖說腿傷幾乎痊癒了,如今跳舞時的體力及技術比起鼎盛時期,也只能發揮百分之七十左右,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上帝卻賜予了我最佳的禮物,那就是足以讓我填滿體力缺陷的豐沛情感。
走過從未有過的絕望及無邊的痛苦後,我發現內心世界已變得更深、更廣闊,甚至上帝給了我至死都要跳舞的命運,因為只要稍微怠慢舞蹈,我的腿就會引發無法忍受的疼痛。人生雖美,有時卻也讓人覺得有如走在黑暗深山般無助,但我相信,可以照亮那黑暗的光,只能來自內在的我;我的名字叫「金星」,正與傍晚第一個出現、黎明時最後一個消失的那顆金星同名(註:韓文的「金」為破音字)。傍晚出現的「金星」彷彿在說:「黑夜不見得只有漫長與痛苦。」而黎明時的那顆金星卻似溫暖地拍拍你的肩膀,對你說:「晨曦即將來臨,要忍耐、要加油哦!」
由衷期盼我這一生不算平凡的故事,可以帶給時下對現實生活失望又疲憊的人一些小小的希望,更期望能成為那些被大部分的人排擠、遭受忽略的少數人的力量;我想大聲對他們說:「請從他人的視線與批評中解放自己吧!對自己誠實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名字前面通常會出現一些繁瑣又不切實際的形容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朝鮮族中國人變性舞蹈家」,一般人都會根據自己的利害關係來為我定位:有時是朝鮮族,有時是中國人,當然還有「變性人」及「舞蹈家」。其實那些不過是我變成「一個人」過程中的一部分,而我只不過是一個聆聽內心世界的聲音,隨著那聲音所要求的命運而走的一個平凡人。
手術後,我以女人的身分重新開始了我的人生。三十三歲得子後,我終於成為一個孩子的母親,即使每次都是我在選擇人生,惟獨這一次卻是孩子選擇了我。透過孩子,我終於得到一個原以為一輩子甚至永遠都無法擁有的角色,那就是「母親」;由於這孩子,我真實感受到發揮母愛的滋味。
以前,我一向只為自己而活,如今,我卻為孩子而活。當孩子長大成人,我希望看著他的眼睛對他說:「要誠實面對自己的人生。當命運碰到需要抉擇的瞬間,要回應的不是別人的聲音,而是自己內心深處最誠實的聲音。」
金 星 二○○一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