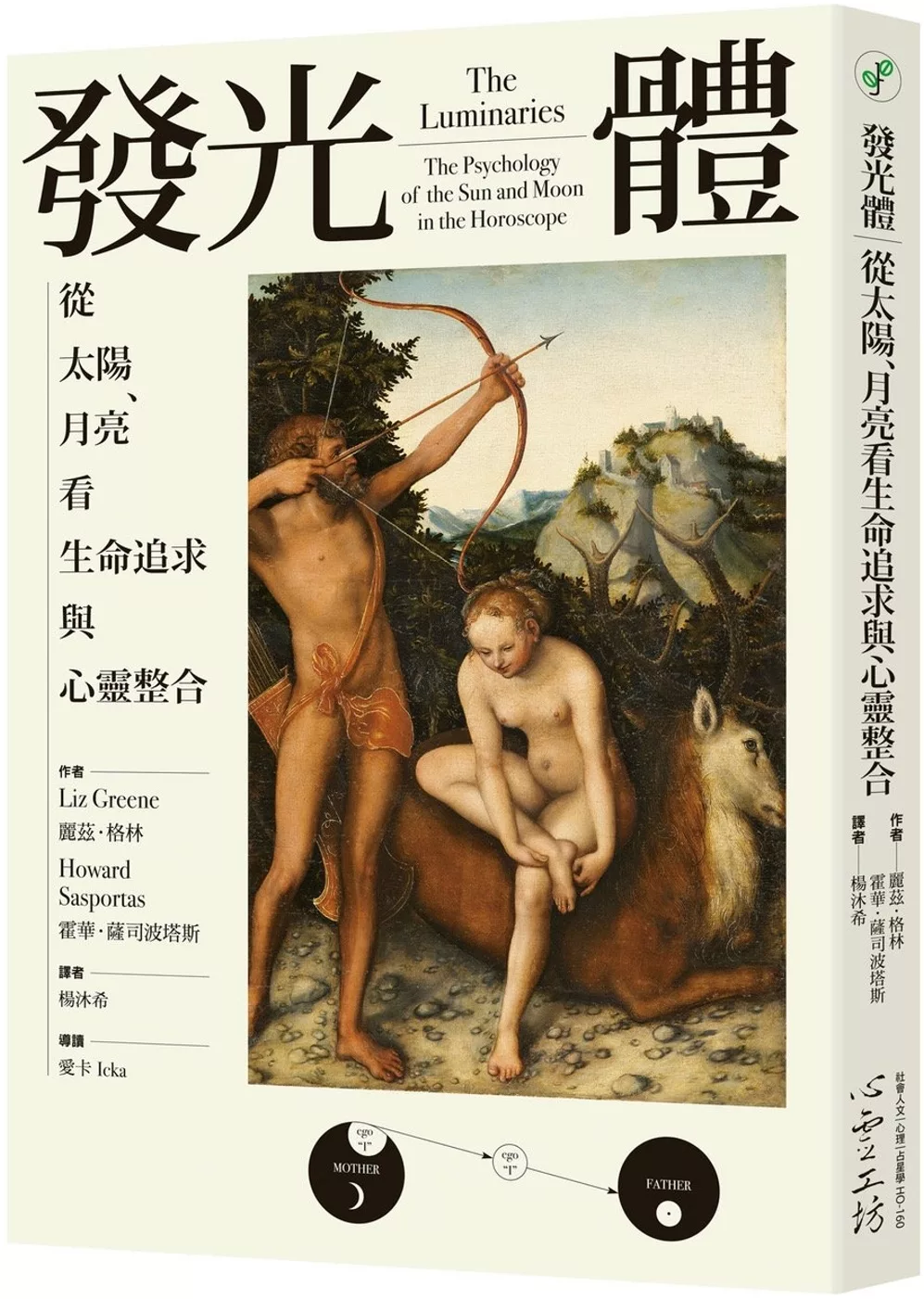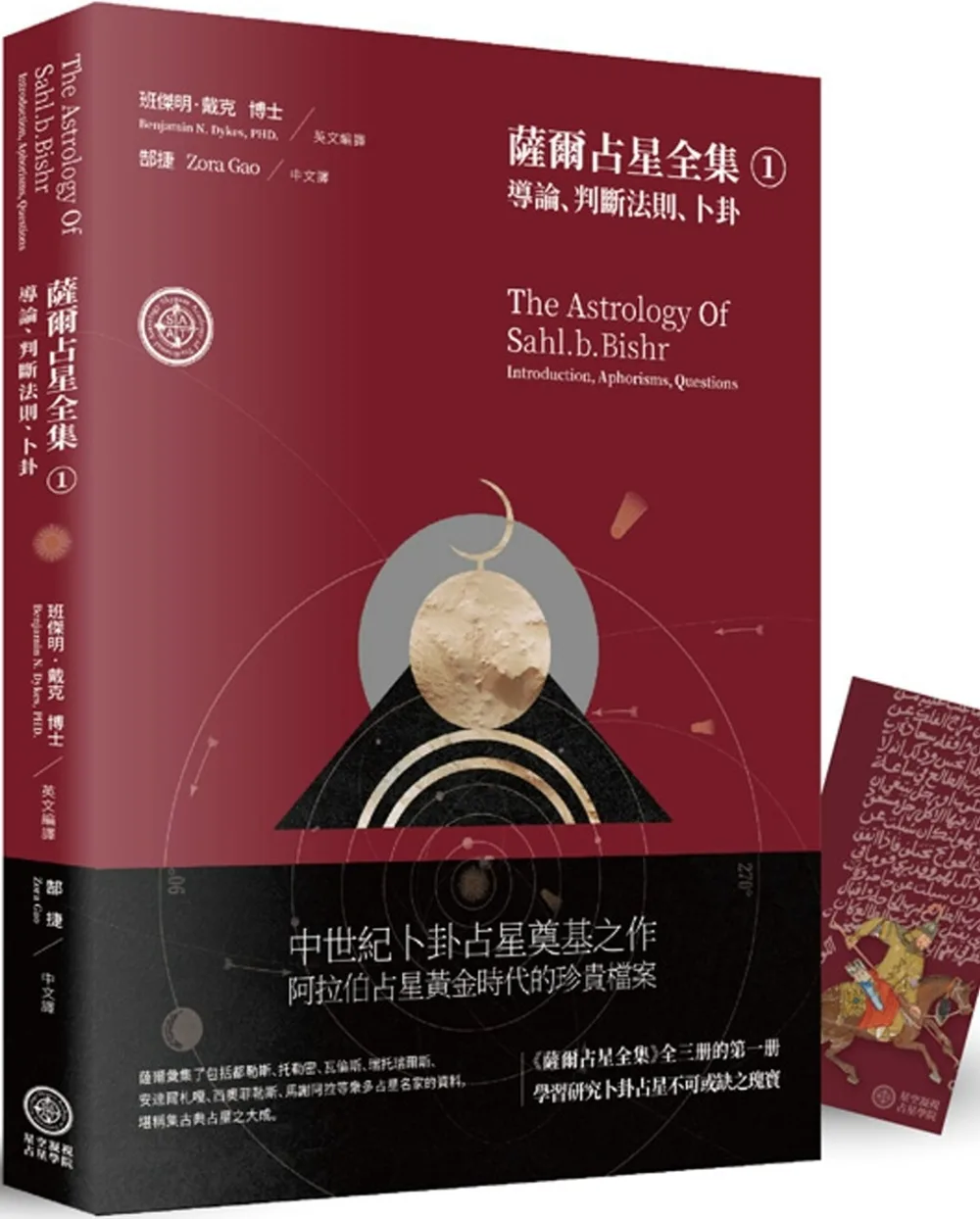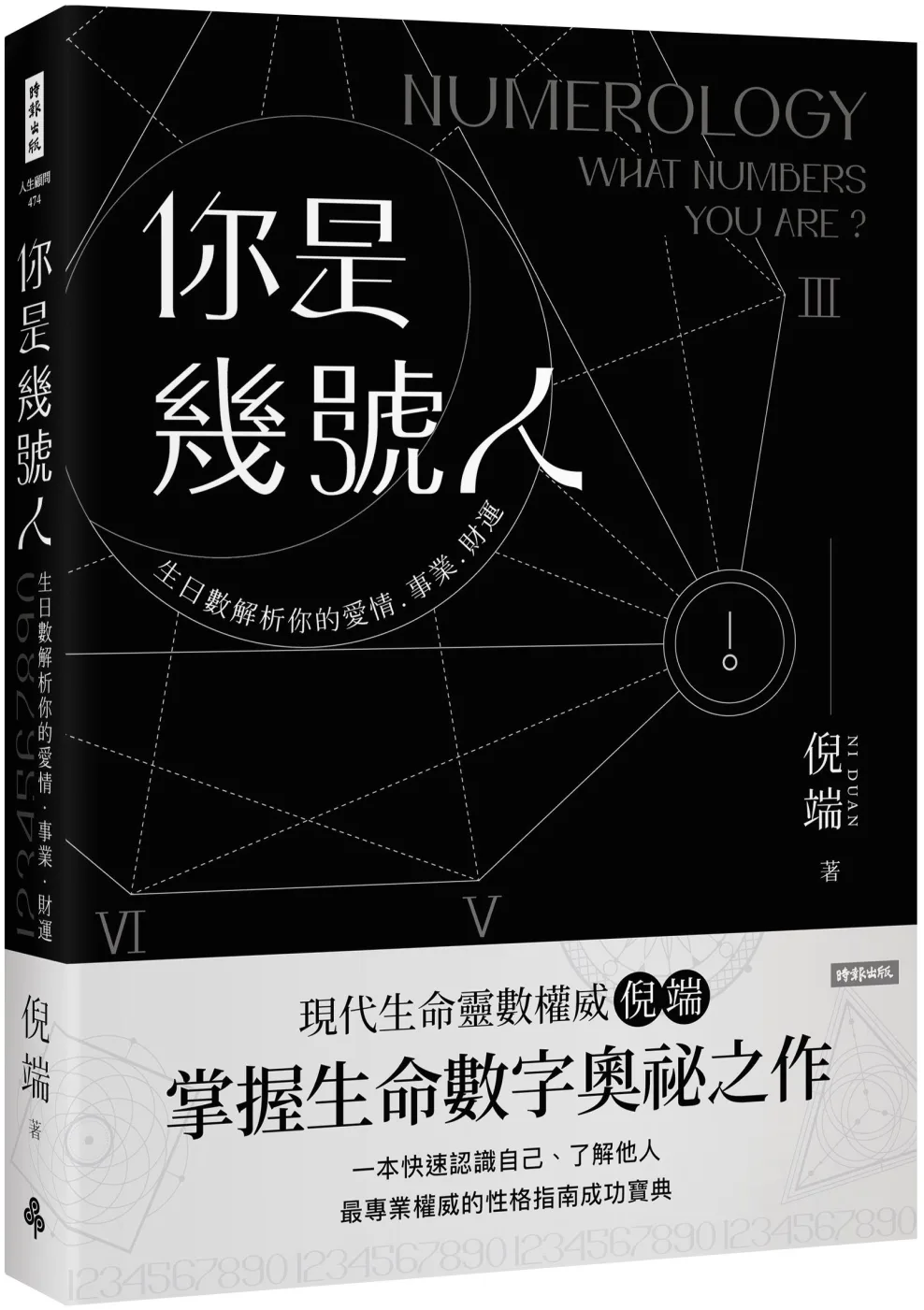推薦序
當你心中的月光隱滅,靈魂的太陽仍在散發光芒
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月亮與太陽是占星學中的兩個發光體,同時也是星盤中最重要的兩顆星。我經常告訴學生,如果在星盤裡迷路,月亮和太陽就是你回家的路標。
本書論及許多太陽與占星的神話,但多數人可能不曉得,圍繞在月亮與太陽神話的其實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信仰。就算它們屬於同一文化,也經常有前後時期之分。即便這些神話的流行時期會有重疊,也反映了很不同的心靈面貌。
月亮每個月都會消失三天(黑月),它的光芒隨著自身的盈虧而產生變化,但它的變化卻遵循固定的週期。與之相對的則是太陽光,它是超越的光、永恆的光,因為太陽本身並沒有陰影,它的光芒也沒有偏私。
月亮光與太陽光相互調節,如神話學大師約瑟夫•坎伯所說,它們的神話組合構成了永生的兩種基本形式。第一種永生是死而復生,人們相信自己死去的祖先會活在月亮上;第二種永生則是靈魂跟隨太陽光而去,自此永不復返,活在太陽的另一邊。
因此輪迴也就有了兩種假設:第一種是人會反覆褪下不同的肉身,如同月亮那樣隱而復現,死而復生;第二種是永不消亡的亮光,它化身為萬物,並隱藏在萬物之中。
讀者只要稍加思考,就可以發現,前者是普遍存在於母神信仰時代,人們對大自然春去秋來永恆循環的嚮往。後者在東方文化中所指的就是涅槃,一種不再輪迴,超脫六道的宗教理想。
以此為基礎,本書所提及的各種神話就有了一個共通的核心,月亮與太陽因此分別代表了:不變與變、精神與物質、獨立與安全。但無論如何,它們都是人類對死亡焦慮的反應,以及對死後世界的猜想。
用神話與心理學的角度來解釋星盤是心理占星學的特色。由於天文學與占星學的分家,加上自然科學的興起與實證主義的抬頭,遂使占星學另闢蹊徑,與心理學產生了合流,它們逐漸採用了人本心理學、精神分析與榮格心理學的觀點,形成了今日心理占星學的樣貌。
在結合榮格心理學與占星學的嘗試中,麗茲•格林是當中的佼佼者。許多市面的占星書也都可以看到對陰影、人格面具、投射、阿尼瑪�阿尼姆斯、共時性等榮格術語的採用。
然而,榮格心理學與占星學的整合企圖迄今仍未完成。榮格心理學擴充了占星師的文字資料庫,但並未根本解決占星學急需面對的問題:它究竟偏向自然科學,還是詮釋學?
有人認為占星是一門古代的統計學,但筆者必須誠實說,這個說法已被許多不同的研究所駁斥。那麼它的效力可以用詮釋學來解釋嗎?亦即它的地位源於它是一門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學科,具有自圓其說的特質,而不是與客觀事實的對應。若如此,占星就無法宣稱它可以透過星體運行來預測吉凶禍福。
既然是心理占星的著作,此處不妨淺聊一下榮格與占星的問題。事實上,榮格很早就對占星學情有獨鍾,這從他與佛洛伊德的通信中可以發現,後來他在煉金術的文獻中也大量引用。他晚年依舊熱衷於占星的科學研究,但結果卻讓他失望。他在進行婚姻合盤的研究時發現,讓星盤準確的不完全是星體的位置與角度,而是占星師本人的主觀參與以及他個人的情緒�心裡狀態。這回到了他對共時性的說法:有意義的巧合。
誰認為有意義?占星師認為它有意義。
這麼說來,真正使命盤產生奧祕性質的並不是許多占星師認為的「時間」,而是「人」。與不少讀者以為的相反,星盤的客觀性不僅未因「共時性」而得到確立,反而受到了顛覆。這樣的矛盾在當前的心理占星書籍中似乎較少提及,卻是榮格與占星兩個學科交會時的深水區,尚待有志者提出理想的解釋。
之所以提及此點,是要表明心理占星學還有許多值得探究的題目可以做,也不應受到心理學知識的挹注而太急著全盤接受。而對喜好榮格的朋友來說,占星學背景中的一體世界(unus mundus)宇宙觀,以及出生盤所揭示的個體化圖像與進程,則高度反應了榮格思想的旨趣。
占星學是傳統命理學之中最突出、最開放接受新知,也最勇於嘗試的學科。相較於東方的命理學,占星學從未停止對新技法的開發,其對深度心理學及神話如海綿般的吸收,也說明了占星師們勇於接受新觀念。
對我而言,學習占星意味著相信個人的命運與宇宙的藍圖相連,對星盤的主動詮釋會使人以更具意義的方式將散亂的生命事件重組,並在回顧過往的同時又對未來展開進一步的推測。它不僅指向了今生,甚至指向了來世。
對在科技與資本面前感到渺小的平凡人來說,心理占星學的魅力相當巨大,撫慰亦相當深厚。所有學習過占星,運用過占星的人都會被它的豐富給吸引。心理占星學的學科跨度相當廣,麗茲•格林與霍華•薩司波塔斯更是當中的佼佼者。
讀者翻開這本書時務必當心,因為你可能會停不下來,從而不小心迷失在各種迷人的故事和心理學浩瀚的概念當中。這個時候請你再次回想月亮與太陽的基本性質:一個自帶陰影,一個永不消失。而我們的心中是否也存在著這兩個相異但互補的面向?是否也有來去無常的思緒,和持續一生的召喚?
我相信,古人仰望天空看到日月時的那份悸動依舊在你胸膛燃燒,提醒你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你應當這麼安慰你的個案�或是激勵你自己:當我們心中的月光隱滅時,靈魂的太陽仍在散發光芒。因此,人應該常保希望。
月光去而復返,而太陽永遠照亮你生命的黑暗。
前言
根據《錢伯斯二十世紀字典》的定義,「發光體」(luminary)一詞的意思相當簡單,就是「光源」,也作「照亮物品或啟發人心之人事物」。因此,在文學或劇場領域,「發光體」指的正是才華洋溢之人,諸如演員勞倫斯.奧立佛*(譯註1)或作家托馬斯.曼*(譯註2),透過他們定義的精湛卓越,讓我們追求的標準更上一層樓。「發光體」樹立典範,呈現出臻至完美的具體成就。
*譯註1
勞倫斯.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英國演員,獲獎無數,被譽為二十世紀最著名、最受崇敬的演員之一,與費雯.麗(Vivien Leigh)是美國影史上第一對奧斯卡影帝影后夫妻檔。奧立佛在舞台與銀幕上詮釋了希臘悲劇、莎士比亞戲劇等各種不同時代的角色。他對莎劇角色的詮釋和對詩意語言的掌握廣受讚譽,且自導自演,改編莎翁的《王子復仇記》(Hamlet),因此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大獎。
*譯註2
托馬斯.曼(Thomas Mann),德國作家,一九二九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一年,首部小說作品《布登勃洛克家族:一個家族的衰落》(Buddenbrooks: Verfall einer Familie)甫一出版就受到讀者與評論的廣大共鳴,之後又出版《魂斷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及《魔山》(Der Zauberberg)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在早期且詩意的占星理論中,太陽與月亮即為發光體,意即「光」。這些發光體、這些啟迪的「引導者」,它們在各自領域裡定義了我們渴望的內在標準為何。過去在解讀行星配置時,會認為這是難以撼動的特質,本該如此。太陽與月亮象徵一個人的本質,定義了當事人的性格,無可辯駁。只不過,占星要素都是過程,因為人類是透過心理學的視角洞悉占星,人非靜止,而是在永無止境的改變與發展過程中推動人生。占星配置描繪起指向某處的箭,用創造力逐漸將層層血肉堆疊在原型模式的枯骨上,隨著光陰前進,以帶有智識的行為,將必要的細膩色彩填進銳利的黑白輪廓之上,而這些斑斕的色彩正是經驗與每個人的抉擇。占星學上的「發光體」的確是指引的明燈,反射出我們終有一天能夠達成的成就,以象徵的形式描繪出我們能夠成為的最佳自我。
人類出生時並未「完成」,相較於其他動物,我們似乎過早降世,無論身心,頭幾年都得仰賴他人才能存活。剛破蛋的小鱷魚就有牙齒能啃,具備能夠行動、可以游水的完整和諧軀體,同時也擁有激烈的攻擊本能,得以獵食、自保。不過,咱們人類這種自然界的偉大奇蹟(magnum miraculum)一出生卻是潛在的受害者,莎士比亞說我們「在奶媽懷裡啜泣嘔吐」,脆弱的無「齒」之徒,無法自行進食,除非有人能夠照料我們,不然我們就死定了。我們遭到子宮伊甸園的驅逐,沒有車、沒有房、沒有信用卡這些不可或缺的東西,我們必須仰賴母親或母親的代理人,這種立即且絕對的依賴會引發我們對最初生命資源提供者的深層緊密依附,這種依附關係之後只能透過掙脫母親來達到平衡。因為,打從一開始,母親就是我們的全世界,我們根據與母親共處的早期經歷來感知世界,之後根據這種「示範」,學習照顧自己(mother ourselves)。如果母親是安全的載具,足以滿足我們的基本需求(溫尼考特所謂之「夠好的母親」),那我們就能成長為信任生命的大人,相信世界基本上是充滿善意與支持的所在,因為我們有榜樣,可以學習善良,且支持我們自己。不過,若我們的需求遭到打壓、扭曲,或直接拒絕,長大成人後,我們就會相信世界充滿掠食者,他們狡猾又有超凡的能力,而且會覺得生命沒有站在我們這一邊,因為我們自己都無法站在自己這一邊。母親是我們首位的實際示範,能夠讓我們看到月亮提供的自我滋養是什麼樣子,具有指導性質,更能讓兒時的我們了解這種滋養可以達到何種程度。不過,月亮,這個能夠教育我們該如何按照個人獨特需求照顧自己的發光體,說到底還是存在於我們內在,(若生命早期的「載具」不夠好)我們可以學習如何療癒傷痛,進一步學習信任生命。
要達成心理上的誕生,我們必須認清自己是完整的個體,與母親有關,卻並非一體。人類內心有一股能量,對抗孩童時期的全然依賴與羈絆,就是這股能量迫使我們憑藉超越生命的力量,走上充滿荊棘的漫長道路,迎向獨立的自我。這不只是長出牙齒,啃咬其他鱷魚這麼簡單。太陽這個發光體在分離的儀式上帶領我們,以「我」這個巨大的謎團引領我們前進,光芒閃爍,承諾起與眾不同的真實自我,掌握的不只是生存的智慧,更是讓生命充滿意義、目的與喜悅的能力。從仰賴母親到獨立存在的道路,無論內在外在,皆如英雄之旅原型所描繪,充斥恐懼與危險。與母親合一的狀態是喜樂的,即天堂花園那永世永恆的繭,沒有衝突,不會寂寞,毫無痛苦,更無遑死亡。不過,自主與真我是孤獨的,要是沒有人愛我們怎麼辦?況且,萬物終有一死,這一切的掙扎與焦慮到頭來又有何意義?指引我們方向的內在明燈似乎永遠困在生死交戰中,如同巴比倫的火神馬爾杜克(Marduk)與他的海洋女神母親提阿瑪特(Tiamat)一樣。或如美國詩人理查.威爾伯(Richard Wilbur)《子葉》(Seed Leaves)一詩所言:「植物想生長�也想保持胚胎狀態�渴望抽高卻也想逃避�成形的宿命??」*(原註)
原註
理查.威爾伯(Richard Wilbur)《子葉》(Seed Leaves)一詩,出自《諾頓詩選》(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第三版,一九八六年由紐約W. W. Norton出版,第一千二百?一至?二頁。
據說,歷史就是意識展開的故事。如同每個人的故事一樣,話說從頭都是嬰兒離開羊水,創世神話也然如此,帶有太陽性質的神祇或英雄脫離原始大母神的軀體。英雄與母龍戰鬥,之後返回神聖父親的懷抱當然不是故事的結局,因為英雄終將必須離開奧林帕斯山,以凡人身分與女伴結合,將英雄與惡龍的爭戰轉化為被愛。不過,正是我們內心一度遭到圍困(有時一輩子都無法脫身)的太陽英雄,這個內在的發光體指引方向,解放自我,從盲目的本能衝動中,走入孤寂卻堅不可摧的「我」之輝光裡。
太陽與月亮象徵著每個人內在兩種相當基本卻截然不同的心理過程。月亮的光會誘惑我們回到與母親融合的狀態,回歸銜尾蛇般的安然容器之中,但也是這道光教導我們如何連結,如何照顧自己與他人,還有歸屬感與同理心。太陽的光會帶領我們走進焦慮、危險與孤獨之中,但這道光也指引我們找到隱藏的神性,如十五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哲學家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所言,我們有權自豪共同創造了上帝的宇宙。為了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意即鍊金術中雙方兼顧的「合體」,則需要一輩子的努力。將自我從母親、自然及集體的融合狀態中分離出來,這樣的行為讓我們能夠發展理性、意志、力量與選擇,以歷史的角度來看,因此造就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在社會與科技上長足的進步。我們也許過分美化了舊時的「自然」母系社會,但只要仔細思考那時的生活條件(人均壽命二十五歲、面對天災疾病徹底束手無策、完全無視個體生命的價值),我們說不定就能以更加欣賞的目光看待太陽帶來的禮物,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讓我們走出母親的洞穴。只是我們似乎太過分了,代價是犧牲了心靈與本能,對地球母親的盲目殘害讓我們來到生態深淵的邊緣。我們著眼太陽的輝光,並非與母親脫離,而是處在解離的狀態,曾幾何時,我們得看「她」的臉色行事,現在是我們說了算,同樣受害的是我們的肉體與星球。我們的個人生命也受到影響,我們似乎還在天上日月的環狀舞步間尋求節奏平衡。榮格說如果社會有問題,那個體也會有問題;如果個體有問題,那我肯定也有問題。「我」是太陽也是月亮,正因這兩座內心明燈在每一張出生盤裡最特別的配置,每個人肉體、心智、心靈的不同,進而產生個體化的卓越標準,同時也在每個人靈魂與精神發展的過程中,展演出狀態最佳的個人典範。無論出生盤裡較為沉重的行星能量多麼強大,最終要匯集、具體化這些能量且將其形塑為個體經驗與表現的還是太陽與月亮。了解日月作為人格特質的描述只是理解占星的起點,發展發光體象徵的能量,讓我們成為自己內在潛力的完美載具也許是最為困難的任務,同時也是我們在個人生活裡能展現的最高成就。
註:本次講座內容擷取一九九?年六月於蘇黎世舉辦之「內行星」單週研討會前半部分。該次研討會其餘的水星、金星、火星講座內容收錄在《內行星:從水星、金星、火星看內在真實》一書中,繁體中文版於二?一九年由心靈工坊出版。
麗茲.格林
霍華.薩司波塔斯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於倫敦